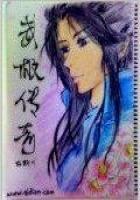不久以前,我读了某位文学家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愤然而起,对叙利亚开往埃及的某一条法国轮船的船长和职员表示抗议。因为当他在餐桌边就座时,这些人曾强迫他或试图强迫他摘下他的红毡帽。众所周知,在天花板下脱帽本是西方人的习惯。
这一抗议令我吃惊,因为它向我表明,东方人对其个人生活中的某种象征是多么执著。
我佩服这位叙利亚人的胆量,就像我有一次曾对一位印度王子表示钦佩一样。那次我邀请他出席观看意大利米兰城的一次歌剧演出,他对我说:“如果你邀请我去访问但丁的地狱,我会随你欣然而往。但我不能在一个禁止我缠头巾和抽烟的地方落座。”
是的,我看到东方人执著于他的某些信条。即使对他的民族习俗的某个影子也紧紧抓住不放,这使我惊讶不已。
不过,我的这一惊诧不会也绝不可能抹掉它后面的那些与东方人的本性、东方的种种嗜好与说法相联系的粗鄙事实。
这位认为在洋人轮船上脱掉红毡帽是件难事的文学家,如果能够想到,这一高贵的红毡帽本是在一家洋人的工厂里造出来的,那么对他来说,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一条洋人船上,脱掉红毡帽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假如我们的文学家想到,在区区小事上的个人独立性,过去和将来都取决于科技独立和工业独立这两大独立的话,那么,他就会顺从地不声不响地摘掉红毡帽。
假如我们的朋友想到,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她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人的。
假如他想到了这些,他就不会写他那篇抗议文章了。
如果我们的文学家想到,他的叙利亚祖父,曾乘着叙利亚船,穿着叙利亚人纺织缝制的衣服,航海到埃及,那我们的自由的英雄,就只能穿着国产的衣服,只能乘着由叙利亚船长和叙利亚海员掌舵航行的叙利亚船去埃及了。
我们勇敢的文学家的不幸,就在于他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故在赢得本质之前已被偶发现象所控制。这是大多数东方人的情形。他们不愿意做东方人——在无聊琐碎的小事上除外,与此同时他们却以他们从西方人那里模仿来的东西为荣,那些东西既不无聊,也不琐屑。
我要对我们的文学家和所有戴红毡帽的人士说:你们何不用自己的手去制作你们的红毡帽,然后在轮船的甲板上,或在高山之巅,或在幽谷深涧,去斟酌如何处置你们的红毡帽呢?
上天有知!这些话不是为红毡帽而写,也不是为红毡帽在天花板下或银河下是脱是戴而写。上天有知!这些话是为一个比所有红毡帽都久远的问题而写;这个问题悬于每个人的头上,悬于每个颤抖的身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