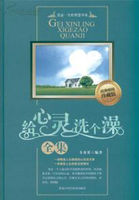当人们险入债务之中时,他们不知道已经为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至于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并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但是债务却真实得像压在人们身上的巨石,直到死亡那一刻才得以解脱。债务就像一个噩梦,影响家庭的幸福,打破家庭的安宁。
即使是那些定期取得高收入的人,如果长期处在债务的噩梦之中,也会感到吃不消的。那么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呢?如何为妻子、儿女的未来生活而节俭地积攒财富呢?一个险入债务纠缠的人无法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他无力保全自己的房屋与财产,并且他不能到银行存钱,因为根本就没有剩余的钱,他也不能购买房屋。他所有的净收入必须用于偿还债务。
哪怕是那些腰缠万贯、大地产商,一旦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也常常会表现得情绪低落、伤心欲绝。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已经养成了挥霍钱财的恶习——好赌、赛马或者享受奢华的生活——以房屋、工厂等不动产作抵押借入大量金钱,挥霍浪费,于是使自己险入无边的债网。除非是法律严格限定的固定资产——因为上层社会的人们早有所图谋:在他们去世后,他们生前欠下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原本富足的基础上更加肆意地挥霍,满足自己奢侈的癖好——法律限定继承人在继承这些不动产的时候可以不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这种特权等级的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继承人继承了不动产也就意味着继承了债务,而且债务往往要比不动产的数额更大一些。因此现在英国很大一部分土地都被当作抵押财产或者是放贷人的财产。
即使是最伟大的人也有债务缠身的时候。曾有人断言:伟大与债务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只有伟大的人才拥有巨额债款;因为他们信用高,放贷人敢于借给他们大量的金钱。伟大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她们受人尊敬,享有信誉。无名小卒没有债务,所以小国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不肯借钱给他们。在欠债上,个人和国家一样,有债务就要支付利息。他们的姓名多次出现在债务薄上,人们据此猜测他们是否已经清偿债务。没有债务的人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那么的无声无息,没有引起社会的一丝波动;而姓名列在债务薄的人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人们关注着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一旦到外国去,就有人焦急地期盼他们归来。
债权人经常被描绘成丑陋、冷酷、面目狰狞、苛刻吝啬的人;而债务人则显得特别慷慨大方,随时都愿意帮助和款待每一个人,他成为普遍同情的对象。当哥尔德密斯不断被催讨牛奶费,而因此交不起房租被捕时,谁又会想到牛奶女工与房东正处于多么可怜的环境中呢?尽管债务缠身,人们也经常对债务人给予同情。彭达戈路尔问巴卢奇有这样一段问答:“如果没有债务你会做什么呢?”巴卢奇回答说:“没有负债的话,一开始我就同上帝站在一边!” “在你看来,借款或者为他人提供信用贷款中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吗?”彭达戈路尔接着问,“显然是没有的!因为欠债是一项真正的英雄之举。”
然而,无论债务人获得了多少赞美的词语,毫无疑问它们都是令人十分难堪的语言,甚至带有讽刺的意味。债务缠身的人为了生活被迫采用难堪的权宜之计。催债人和治安官不断纠缠他,向他讨债。只有少数的债务人能够像谢里丹那样,轻松自如地应对这些催债鬼,谢里丹居然把他们请到马房,在那里招待他们。一般情况下,当债务人听到敲门声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会突然变得煞白。他的朋友也都变得冷漠、麻木,甚至他的亲人也疏远他。出国他会感到厚颜人世,呆在国内则战战兢兢。渐渐地他变得暴躁、忧郁、易怒,甚至失去了生活中的所有快乐。他急切希望获得通向欢乐与自尊的通行证——金钱;但他唯一拥有的只有债务。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招人猜疑、被人蔑视,无处不受冷落的可怜人。他生活在绝望的沼泽之中。他感到在别人——甚至是自己——的眼睛里他都最低等的人。他必须服从其他人的无礼要求,而他只能以伪造的借口推辞这些要求。他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并且失去了作为人来讲最基本的自主性。他乞求人们的怜悯,恳求催债人能够延缓还债的时间。当一位冷酷的律师指控他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的时候,他瞬间感到自己早已落入债务之魔的手掌心。他向友人与亲人乞求帮助,但是得到的只有他们的蔑视和冷漠,而且拒绝他的一切请求。这时他又乞求于债权人的援助;但即使成功,他也只是从一个火坑跌进了另一个火坑。我们很容易看出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无耻地躲避或者不断的采用权宜之计,或许他的余生将会在监狱和囚犯工厂里度过。
有人一生都不借债吗?如果负债,有没有避免因债务引起的道德堕落的可能呢?在确保人们的独立和自尊的同时,难道就不能还清债务了吗?事实上要做到这些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适度借债”。只可惜,现代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借债的时候,总相信自己具备偿债的能力。我们无力抵制挥霍金钱、奢侈享受的诱惑,有一种人想拥有高档的精美家具,并且住在租金相当高的公寓里;第二种人想品尝美酒的滋味,要包下歌剧院里所有的单间;第三种人要举行宴会、音乐会——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并且深深地吸引诱惑着我们,但是倘若我们无力支付这些昂贵的开支的话,我们就不要沉溺于此,要学会放弃。如果宴会是由肉联厂、酿酒商、食品加工商等提供的,你向他们借钱却又无力清偿,那么这场宴会表现出来的实际意义岂不是你穷摆阔气的寒酸相吗?
我们不能用举债度日的方式生活,也不应该为了享受今天的奢侈生活而提前花掉下一周或下一年的收入。债务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错误,通过它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债权人与债务人都会受到谴责的,债权人提供贷款并且鼓励客户或者是那些可怜人贷款,而债务人就是获得贷款,以便满足自己的欲望与要求。如果一个人可以避免借贷,那么他就能够把握住自己的确切状况。因为他的支出是以收入为限,并且恰当地、合理地分配他的收入,将留下来的钱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总是能做到平衡有余。如果他购置任何物品的时候均用现金支付,那么他的家庭账户一定会年年有余的。
但是,当他的账单开始迅速增加的时候——裁缝店欠款单、服装店赊款单、肉食店账单、杂货店账单,等等;纷纷而至的账单让他摸不清头脑,不知该如何承担每一笔费用。渐渐地,他的债务堆积如山。但是这个过程却是在一种无声无息地条件下进行的,他自然是没有察觉,仍然潇洒自如地出入各个消费场所,似乎搬进家里的东西都是不要钱的,可事实上,它们都记在了账单上。年终收账,催款的账单就被送到他的手上,看着这厚厚的一摞账单,他只有无奈,内心充满悔恨与沮丧。这时他才能感悟到:一时的快活要用一生的不幸作代价。
这个道理也适用在穷人身上。许多年前,为了帮助小商贩和贫民筹钱,以保证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国会通过了一项建立小额贷款机构的法律。他们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举债与抵押未来收入的便利条件。但是一部分贪婪的人将这项法律作为攫取金钱的好手段,这些可恶的人组成了贷款俱乐部,公开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利息为5%的贷款,并按周分期偿还。贫穷的劳动人民急于通过这种机构来借款。有人借钱是为了“一次狂欢”,另一些人借钱是为了买一件新衣服,还有人是为了买一台漂亮的时钟,等等。与往日的储蓄相比,这些人更愿意向贷款俱乐部借钱,并且愿意在清偿债务之前长期地险于困境与贫穷的生活处境中。依靠这种借钱的生活方式倒不如赚多少花多少:因为这毕竟是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
至于那些狡猾的贷款俱乐部的合伙人,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怎样榨取人们的钱财的。假设他们借出了10英镑,期限是3个月,利率是5%。如果按周分期偿的话,每周要支付10先令——并且是从贷款的第一周开始支付。虽然10先令是按周偿还的,但是5%的利息却是以贷款的总额作基数的。这样一来,名义利率是5%,但实际利的息率却在不断地增加,到最后一周,负债人偿还的实际利率竟达到100%!这就是所谓的“养鸡吃蛋”。
对来那些能干的人来说,他们更容易借债。能干与节俭或自我克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能干也不会对僵硬而缺少弹性的一般数学算法产生任何影响,能干的人也经常考虑不到培根所谓的“商业智慧”。然而,培根自己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忠告,因为一时的奢侈而最终走向毁灭。培根在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当他成年时,他就险入了更大的经济困境。但是他追求奢华的生活,过度的开销吞噬了他的收入,使他成为一个债务缠身的人。有一天,培根从卧室走到客厅,看到几个债权人正在那里等他,他说:“坐着不要动,我的先生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起身就意味着我的倒下。”为了支付他的所需,偿还债务,他不得不接受了贿赂。就这样,培根被他的对手打败了,并且被判有罪,给予免职并且险于破产。
哪怕是具有卓越的管理宏观财政金融才能的人,在他们私人的经济事物管理方面也可能是完全失败、一塌糊涂的。当皮特先生管理国家财政时,他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虽然他在工作上表现突出,但是他自己总是债务累累。应皮特先生的请求,银行家卡灵顿勋爵曾查看过他家的账目。他惊奇地发现账单上记录着要付给屠夫的肉钱一个星期就要一英镑,付给佣人的工资、家人的伙食费再加上日常开支,全家一年的总消费额竟超过了2300英镑。在皮特逝世的时候,国家拿出了40000英镑来为他清偿债务,但事实上他每年的收入从不低于6000英镑;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五港同盟监督官一职,每年也可以挣到近4000英镑。麦考利说出了其中的原由:“皮特具有像伯里克利与德威特那样的公正无私的美德,但是如果他能像他们那样具有高贵的俭朴精神的话,他的社会地位将会更高。”
当然皮特先生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例如梅尔维尔勋爵,他管理私人事务的方式同他管理公共钱财时一样——挥霍无度。福克斯是一位大债主,他的座右铭是:如果一个人愿意偿还足够多的钱,那么他自己就不必拥有什么钱了。福克斯把阿马克的外厅称作“耶路撒冷大厅”,因为他经常在这个外厅里从犹太放贷商人手里以很高的利息借款。他最大的恶习就是赌博,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赌博而欠了大量债款。据吉本说,有一次,福克斯连续赌了近20个小时,输掉了11000英镑。在当时,像这样的豪赌只是上流社会生活的瑕疵,人们还不知道作弊。塞尔维恩曾提到福克斯赌博的损失,把他称为“殉道的查尔斯”。
谢里丹是一位负债英雄,他是依靠负债生存的。虽然他有一些可得到大笔收入的办法,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他并没有还任何人的钱。到他手里的钱就像落到他手里的雪花一样,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把他第一个妻子的1600英镑花在了一次赴珀斯的为期6周的长途旅行上。因为贫穷,他开始写作,我们或许应该把《情敌》以及他后期的剧本归因于贫穷对于他的激励。他的第二个妻子使他获得了5000英镑的财富。他带着这5000英镑加上卖掉居利·蓝公司的股票所得的15000英镑,在萨里购置了一块地,而这又使他负债累累。他的余生可以说是变化多端的,有时绚烂夺目,但是大多数时间他都处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地举债,又无休止地躲避债权人。歌剧院的泰勒先生经常说:“若在大街上遇见谢里丹,如果他脱帽向我表示致意,我就不得不借给他50英镑;如果他停下和我说了几话,那我就要损失100英镑。”
有一天,谢里丹的一位债权人骑着马来向他讨债。“啊!真是一匹漂亮的田马呀!”谢里丹殷勤地对债主说。“你也这么认为?”债主问,“是呀,跑得怎么样?”谢里丹接着问。债主得意洋洋地说:“你应该亲眼看一下,”话音刚落,债主立刻骑上马全速地跑远了。谢里丹利用这个机会,匆匆地躲进最近的角落里。每天早晨,各个债主都会来找他讨债,想在他出门前找到他。这些人在房间的走廊上等他。当谢里丹吃早饭的时候,他总是要下楼问:“门都关上了吗,约翰?”在确信门都关上了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从中间溜出去。他到处借钱、欠债——欠杂货商的钱、欠面包师的钱、欠牛奶工的钱、欠屠夫的钱。有时谢里丹的夫人还要像一个佣人那样,为了做一顿早餐而向邻居要来咖啡、黄油、鸡蛋和一些钱。而这个乞讨的过程一般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当谢里丹担任海军会计长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屠夫把一大块羊肉送进了厨房。厨师拿起羊肉就放到锅里煮,然后到楼下向谢里丹要钱,但是他没有要到钱。屠夫只有无奈地打开锅盖,取出了那快几乎就要煮熟的羊肉,带走了。然而,即使生活已经十分窘迫了,当谢里丹应邀带儿子去农村的时候,他总要奢侈地雇用两辆双轮马车——他坐一辆,而儿子汤姆坐后面一辆。
奢侈与借债的生活结局是相当悲惨的。在他去世的前几周,他就已经没有赖以为生的食物了。他的那些贵族朋友也彻底地抛弃了他,欠下的债务也需要马上清偿。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是在治安官的监管下度过的。他之所以没有被转移到监狱,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这样的转移会加快他的死亡时间。
拉兹枢机主教为了偿债,卖掉了他的一切财物。但是他仍然无法恢复往日的自由。他甚至为了不再忍受见到债权人时的那种尴尬、难堪,而情愿在维塞尼斯城堡中被监禁。米拉波的一生都是在债务中度过的,因为他养成了致命的挥霍无度的恶习。他的父母能够使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弄来一份逮捕令,然后把他安全地监禁起来。虽然米拉波执掌国家权力,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却是那么的悲惨,或者说他曾经是那么的挥霍无度,以至于他一直欠着裁缝制作结婚礼服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