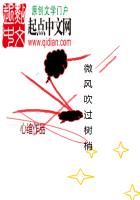那百户倒地,口中鲜血汩汩涌出。方晖踏上一步,问道:“李立虎、欧阳华怎生死的?”百户眼中闪过一丝异色,旋即笑了一声,说道:“你当锦衣卫的百户是什么人,会受你供么?”
欧阳霖此时穴道已解,但手足酸麻,立起身来又坐回椅中,问道:“你们把刘伯伯怎样了?”那百户哼了一声,闭起眼睛,并不理会。方晖知道再他也是无用,缓缓抬起头来,望向一众小旗。
这小旗之职,在锦衣卫中已算得有职司,较之平常的军校、力士,已高出一大截,大多是由颇有武功根底之人担当,此次所出竟全都是小旗,颇见任务算得不同一般。方晖缓缓地问道:“你们怎么说?”余下尚有七人,一言不发。此时听得楼梯声响,想是最初一人破窗飞出,惊动了暗哨。
方晖心知这百户或许知道些什么,这些小旗却并不知情,多问无益。当下扶起欧阳霖,转头向那百户道:“在下也敬佩你是条汉子,便不多折磨你了。”飞起一脚,踢在他背心大椎穴上,将他踢得直飞起来,这一脚看似不重,却脚尖略向上撩,使足了真力,又踢在背心要穴之上,那百户当即毙命。那尸身撞向众人,趁众人一乱,方晖左手长臂收起长剑,右手揽着欧阳霖,撞破长窗,唿哨一声,已自越墙走了。
两人一骑,向南疾驰,方才出得城门,听得远处火流星号炮升起,想是众小旗为方晖神威所摄,怕他见了火流星,盛怒之下去而复返,是以估量他去得稍远,才放火流星示警求救。
两人出了城南,绕过湖州城,折而向北,一路往无锡而去,此时双人一骑,那马负重,速度渐渐慢了下来,欧阳霖的手足酸麻,却也慢慢地解了。
两人离开湖州城五六十里,欧阳霖悄声道:“方大哥,我们下马歇歇吧。”方晖一笑,点头道:“马儿更要歇歇啦。”两人下得马来,牵马缓步而行。方晖见欧阳霖面容憔悴,秀美蹙起,有心想说两句宽慰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犹豫半晌,唯唯诺诺地小心问道:“那刘伯伯”
欧阳霖黯然神伤,说道:“我虽不是锦衣卫的人,锦衣卫行事,也见过不少,刘伯伯曾经言道,自永乐末年,锦衣卫派争愈演愈烈,我适才店中一问,只为情急。刘伯伯刘伯伯他已必然无幸了,否则当年之事,我尚在幼年,又何以来问我。”
方晖见她又是泫然欲泣,忙岔开话头道:“如今你有什么打算么?”
欧阳霖摇摇头,说道:“我自幼是刘伯伯抚养长大,如今可算无家可归了,总须先找到我姐姐再说了。”一言未毕,想起刘伯伯身死,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滴了下来。
方晖默然良久,又问道:“适才我在房顶,听那百户说,你姐姐已入了锦衣卫,此事你可还知晓么?”欧阳霖又复摇摇头,说道:“姐姐长我三岁,十二岁那年,南镇抚司说是缺人,我姐姐人既机灵,武功又高,被南镇抚司借用了去。此后两三年都难得见一面,前年来湖州会过一次,说是又借去了刑部,至于是否真的入了锦衣卫,当时却未曾说起。”
方晖听了“刑部”两个字,不禁心中一动,摸了摸怀中王亦宸所赠的那块令牌,劝道:“我看此番遭难,还是锦衣卫派争,便算你姐姐入了锦衣卫,想来北镇抚司的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向刑部的人为难,我们只须及早寻到了你姐姐,谅来也不致有什么危险。”
欧阳霖心下略宽,此时问道:“方大哥,你怎知我父名叫欧阳华,你问那百户的话是什么意思?”
方晖一愣,心想乃父实是明教旧派之人,此事说来话长,况且牵连甚广,当下便简略地说了嵩山见锦衣卫派争相残,提到欧阳华、李立虎乃是内部倾轧而死,却欺瞒亲眷,因复姓欧阳,是以想到欧阳霖。
欧阳霖低低言道:“我父临终,说这锦衣卫之中,甚于虎狼,只怕便是为此,不对我姐妹明言,想是怕牵连了我们。”方晖点头称是。欧阳霖抬起头来,问道:“方大哥,你适才赤红了双眼,进屋杀人,我当时怕极了你,想不到你武功原来这样地高,那****不知轻重地向你出手,想来后怕。”
方晖听她不追问自己武功来历,倒是松了口气,说道:“当时见你受困,怒气大增,出手忒狠辣了些,也是有的。他们残害同袍,毫无人性,还敢欺负我妹子,却是死有余辜。”最后一句,倒带了三分调笑的语气。
欧阳霖脸上一红,转过身去,低声说道:“没来由地说这些疯话,谁是你的妹子”方晖见她羞红了双颊,脸上兀自挂着泪珠,又爱又怜,心下暗暗感慨:“若不是你这妹子,小房子一条性命,早送在那石洞之中了。”
正说之间,大路上马蹄声响,一骑奔驰而来,马上乘者一提丝缰,那健马立止,端的是骑术了得。来人翻身下马,问道:“欧阳二姑娘哪里去?”
方晖闻言吃了一惊,伸手便去摸剑,需知欧阳霖平日里身份皆是“钟小妍”,那人既知她是欧阳二姑娘,必是锦衣卫有关。
欧阳霖向方晖摇了摇手,示意他不要妄动,说道:“安大哥哪里去?”
那人望了方晖一眼,皱了皱眉,又望向欧阳霖,示意询问。
欧阳霖点点头,说道:“大家自己人,这位是安奇刚安大哥,这位是方晖方公子。安大哥是锦衣卫的人,却在刑部,方公子是我认识的江湖朋友,极谈得来的。”
方晖见着安奇刚二十七八年纪,虽是一身儒雅打扮,但朗眉星目,极是挺拔,勃勃英气之中透露着一丝不惑的沉稳,太阳穴凸起,举手投足之间,显见内外功夫,都是十分了得。
那安奇刚听欧阳霖说“极是谈得来”,不禁皱起眉头,又看了方晖两眼。方晖被他犹如冷电般的双目扫来,感觉极不舒服,心中不喜。心下暗想,欧阳霖与他言语之间极是亲密,想来是旧相识了,刑部有什么了不起,我拿出令牌来,说不定你要向我行礼。
正自胡思乱想之际,那安奇刚言道:“既是好朋友,明说不妨,令姊让我来知会你和刘伯伯,速离了湖州北上,北镇抚司派争之际有人放出风来,要为难你们。”
方晖听到此处,哼了一声,却不接口。
那安奇刚甚感奇怪,问道:“方公子何意?”语气已颇为不满。
欧阳霖急忙言道:“多谢安大哥啦,不过却是迟了一步。”当下详述近日来湖州之事,说道刘伯伯遭难,又是哭了起来,那安奇刚温言劝慰。
方晖知道欧阳霖生来心高气傲,在客栈之中,被那百户欺凌胁迫,尚未有半分退让,此时落泪,倒似见了亲人一般,眼见安奇刚轻抚其背,心中隐隐便生出一丝不快来。
那安奇刚听到方晖闯店救人,使重手顷刻之间,连毙八名锦衣卫,其中尚有一名百户,大感惊诧。抬起头来,向方晖道:“安奇刚深谢方公子援手之德,那北镇抚司卫所现在为所欲为,欺凌孤女,原是该杀,方公子替我杀了他们为我妹子出气,最好不过。”
方晖听到“替我杀了他们”,怒气更增,两眼向天,道:“好说好说。”
安奇刚见他神色无礼,眼中怒气一闪即过,沉声道:“方公子能在锦衣卫中来去有如无物,武功想必是好极了的!”虽是脸上神色不变,但语气之中,剑拔弩张之意,已无半分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