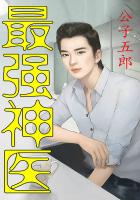入夜,方晖携了长剑,早早来至湖北面的长亭,默运内息。这些天,他一边畅通内息,一边默揣招数正反变化,日间与欧阳霖那一战,于这几天磨练的招数,也进益不少。
少时,一阵凉风拂过,白衣如雪,正是沈双凡到了。
方晖上前施礼已毕,备言日间前事,沈双凡点点头,问道:“小房子,你是怕我仇视锦衣卫,对她不利么?”方晖沉默不答。
沈双凡缓缓道:“是非恩怨二十余年,我虽少与人交往,却也不是祸及人妻女之人,锦衣卫尽忠于朝廷,也只是奉命行事,何况这欧阳姑娘,来历恐怕另有别情。”方晖一惊,他早已想到,锦衣卫围攻南阳侯府之时,调动如此多的人马,可见带头之人的职司不低,而武功却是显然不及欧阳霖。
沈双凡见方晖不言语,便说道:“我看这孩子跟你颇是投缘,想来不会害你,我只告诉你,她那对通点峨嵋刺的功夫,来历久远,她年纪幼小,这功夫显然是从小习练的,若是如此,她的师长辈,可厉害得很那。”方晖不知该如何作答,垂首不语。
沈双凡摆了摆手,说道:“算了,不说这些,各人缘法不同,一秤棋信手置之,哪渠暇分黑白?我自今夜起,将当年他留下的九华功夫传授给你,五天之内,当可传完。九华招数,你本都烂熟于胸,他的功夫,在悟不在练,你能贯通多少,看你自己造化了。”
此后一连五晚,沈双凡将九华派剑法掌法内力,个中精微变化组合,一一传授给方晖。方晖本于此道另开蹊径,悟性奇高,时时发问探讨,沈双凡都觉他奇思妙想,有些招数甚至是自己此前从未想到的。
五天来,方晖日夜用功,白天闲暇时与欧阳霖叙谈风月,只觉自己记事起二十来年,从未有过如此快乐时光。
第五夜,方晖如约来至长亭,沈双凡却已飘然而去,留下一贴,言道方晖心思灵巧,自己已无可授,当年之事心愿已了,愿方晖此后事事小心,好自为之。方晖深叹,心底竟似有所失。
又住两日,方晖起身要往少林去寻温恭,欧阳霖心底不快,却也不言明,双骑并辔,一直送出湖州城数十里,犹是恋恋不舍。
方晖与欧阳霖这十来日的相处,心底也是不愿分离,此时硬下心肠,一提丝缰,说道:“欧阳姑娘,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江湖儿女,山高水长,我们必有再会之期。”
欧阳霖压低声音问:“方大哥,你这一去,可还回湖州来么?”
方晖心中不舍,拨转马头,说道:“欧阳姑娘,在下有一句良言相劝,不知当讲否?”
欧阳霖翻了翻眼睛,如嗔似怪。方晖哈哈一笑,道:“如此我直言了。锦衣卫官场之中,牵涉江湖旧怨,是非对错,原自难说,况且如有魔教之人来寻钟小妍,也是照顾林前辈的义气,肝胆相照,再加捕杀,确是不该。姑娘你蕙质如兰,何苦卷入这名利圈、是非场、恩怨地之中,莫不如与我同行江湖,岂不是好?”
此时方晖之邀,言下之意欧阳霖岂有不懂之理,当下羞得面红过耳,喃喃道:“方大哥,我此时却是不能离了湖州,你的话我记下了,愿你有睱,来,来湖州接我。”调过马头,拍马疾走。
方晖尚待叙言,却听忽地一声,一物劈面掷来,方晖顺手一抄,却是一把长命金锁,做得甚为精巧,红线穿连,尚带微温,想是欧阳霖贴身之物。方晖抬头,欧阳霖那匹马,却已头也不回地去了。
方晖放脱坐骑丝缰,缓缓而行,一时将金锁收进包袱,一时放入怀中,一时缠在腰间,都觉不妥,思来想去,也把了那红绳,穿了金锁系在项下,心中只觉喜乐至极。
不一日进了河南境内,此时河南黄泛甚是厉害,沿途可见灾民三三两两,逃荒而出,衣衫褴褛沿路乞食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时至中午,方晖于路边一家村店打尖,见此处弊旧,粗饼劣茶,也不以为意,打算对付口腹便即上路。
便在此时,一行人等,络绎约有十数人,进得店来,吵吵闹闹地要吃喝。方晖抬眼一看,不禁一惊,见是镖局人众,赫然便是京师人武镖局的字号。方晖眼见此处距嵩山也即不远,当时想起武当山下人武镖局众人横尸大路的情状来,不由得暗暗心惊。
那为头的镖师止住众人吵闹,喝令噤声,众人坐下吃喝,却仍是交头接耳不休。那领头的镖师身材魁梧,劲装结束,见众人扰攘不休,当即大怒,喝道:“你们一个个都闭了嘴,这趟镖,总镖头多给了一倍的脚力,出来之时你们应承好好,一路上嘀咕个不停,哪个兔崽子不愿做了,乘早给我滚了吧!”众人显然是怕了这人,都闭口不言。
半晌,那领头镖师同桌一人悄悄地问道:“朱镖头,这趟镖,笃定无事么?”那朱镖头眼睛一瞪,同桌之人忙道:“朱镖头莫恼,我只这么一问,若是怕了我便不来了。”
朱镖头眼睛横过,低声骂道:“你这混账不怕?哼,不是为了多拿这趟银子,你肯来?说实话,这趟镖,总镖头不仅多加了好手,另有安排。”那被骂之人诺诺连声,说道:“是是,总镖头委派了朱镖头你来,本就是万无一失。”
这两人低声耳语,方晖便在邻桌,近日来内力精进,隐隐听得清楚,便听得那朱镖头道:“哼哼,上次武当山下戚老儿带队,估计也是太过托大,遭了偷袭。我就不信,大路之上,谁有许大胆子,劫夺镖行。若查了出来,将他大卸八块。哼,也不打听打听,人武镖局岂是好欺负的?”
这边嘀咕未完,却听得旁边桌上有人阴阳怪气地说:“人武镖局历来都是横行霸道,欺负别人的,怎么会好欺负?”
众人都是一惊,向那人望去,却见一人,头戴斗笠,伏案而睡,似是吃多了酒,一身粗布衣衫,斗笠遮住了头脸,年纪形貌都瞧不清楚。方晖心中暗自惊讶,这人比自己坐得更远了一个桌子的位置,那朱镖头说话声音已压得极低,自己如若再远一些,便听不清了,此人内力,显然十分了得。
那朱镖头虽是脾气暴躁,但却老于世故,当下走近了道:“阁下想是吃醉了酒,我们出门在外不想惹事生非,你不要胡说八道就好。”
那人缓缓立起身来,斗笠压得极低,仍是看不见面孔,当下大声说道:“我这里专门劫人武镖局的镖,不相干的人都滚得远远的罢,免得伤了无辜。”话音一落,人武镖局的人众都站了起来,虽是进来时候乱哄哄地,此时却无一人出声,都缓缓地抽出了兵刃,足见平时习练有素。
方晖四下一望,见除了镖局和那劫镖之人,闲人便就自己一人,当下拿了包袱,快步往外就走,那人也不拦阻。大道上走出不上十数步,刚牵了马来,听得身后打斗之声大作,方晖心下奇怪:“难道那头戴斗笠之人,便只孤身一人,在这官道之旁,劫夺人武镖局的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