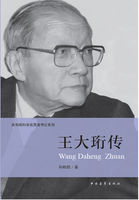此时,章士钊在日本出版一个刊物《甲寅》,梁漱溟与这个刊物从书信上往来,才清楚是章士钊,梁很佩服章的思想,认为他头脑周密、精细,人格又极有独立性。两人多次通信,后来章回北京,住魏家胡同,因与北京政府要一笔款,结束军务院事,梁漱溟来到章士钊家,一见面梁颇感失望。“因为见面时,他是代表南方来北京,北京有许多湖南的乡亲、朋友在他家吃饭,我也参与吃饭……来的客人大谈其书画,拿出一卷一轴的名人长联、对条给大家看,我大失所望。我认为,国家正在一个危难的时候,正是南北政府对峙、要结束未结束之时,北方也还有直系、皖系如此等。国家不统一,人们生活还在苦难的深渊,你怎么搞这些字画,这不对。”
令梁漱溟失望的还有,梁本来极尊敬这位岁数大出自己较多、且很有才干的人,但其“多才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虽然很不喜欢,我还是一直到他90岁的时候我还跟他往来”。
因为蔡元培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教书,梁漱溟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也见过当时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李大钊亦是蔡元培请到北大讲课;陈独秀则是从上海到北京为“亚东图书馆”筹股时,恰好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蔡与陈本来是老朋友,蔡便说:“好啦,你到北京了,不要搞什么图书馆了,不要搞什么出版社了,你就来帮我吧。”据梁漱溟回忆,陈、李、梁是同时进的北大。
三人的第一次见面,缘于李大钊请客人吃饭,请的人里面有陈独秀和梁漱溟。梁和李的交往,显然多于陈,但梁对陈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认为陈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虽然他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学校内外有不少人反对他。
梁漱溟认为:在蔡元培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除了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新派名家,亦有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等旧派学者。新旧派人物之间观点各异,常有论争,但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它们却能各抒己见。“从总体上看,蔡先生是极力扶持新派人物,主张传播新思想,并在实际上酝酿了新潮流的。但更使人赞佩不已的是,他并未因为支持新派而反对旧派,而是也给他们一席之地,发表己见,让新旧学派之思想观点在争论、比较中决胜负,分优劣。其结果尽人皆知,新学说、新思想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波及全中国,终于酿成了五四新潮流”。
梁漱溟与李大钊的交往多于陈独秀,这不仅仅限于文字讨论。1919年夏,李大钊、张申府、雷同伦(国能)和梁漱溟四人同游中山公园,并合影留念。
在北大,两人时有来往,李大钊给梁漱溟的印象:“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头他也是很激烈的。”
梁漱溟每次去北大讲课,在课前或课后,都要去学校图书馆办公室坐一会儿,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经常送些期刊给梁看;有时李有事或梁离去,均不打招呼,彼此很随便。
梁漱溟准备结婚时,到李大钊家拜访并告知。李告诉梁,二十年前李就成家了,由于父母早亡,祖父母年迈,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久,祖父母就过世了,只留下他与妻子,妻子赵氏长他五六岁,但两人感情很好,他外出求学,赵氏鼓励有加。
离开北大后,梁漱溟还常去看望李大钊。最后一次见面是1927年春,梁到李居住的东交民巷旧俄使馆拜访,适逢当天宾客较多,李忙着接待,梁见此便未停留,匆匆道别。
岂料不久即传来李大钊全家被捕的消息。梁闻讯后,急忙赶到章士钊家(李大钊与章士钊亦较熟识,并教过章的子女章可、章因),想和章一同出面保释李的家眷。章以为不妥,便说他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很熟,他去见杨,可保李大钊不死。然而,李大钊还是被杀害了。
李大钊遇害后,棺材停放在下斜街长椿寺。梁漱溟赶到那里,心里很难过,又见棺材菲薄不堪,心情更加凄凉,待守在门外的警察走后,马上打电话给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等吴与其他朋友来后,大家主张另换棺材。梁漱溟回忆:“我和一些朋友在长椿寺开了会,捐了一些钱,把李大钊安葬了,总算安葬得好。大家很悲痛,我和李是好朋友,更是悲痛。”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另一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亦是梁漱溟的朋友,尽管胡适的文化观点、学术思想与梁漱溟的主张是对立的,并时而在刊物上争论。
梁漱溟曾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写道:“我们同胡适之、陈独秀,都是难得遇着的好朋友!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极好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幼声,鼓励你们。”
梁漱溟认为,胡适头脑聪明,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时,与任鸿隽等组织科学社,就出名了。胡晚梁两个月入北京大学,与高一涵共住东城墙眼儿竹竿巷。其最大的贡献和功劳,就是主张用白话文来作诗、作文章、谈学术。诚如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文中所言:“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独秀)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来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
然而,胡适的哲学研究并不深入。他《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了上卷,后来写不出来。梁漱溟认为,胡适的头脑是以浅明取胜,而哲学光有浅明是不够的。哲学要精深、精深而深奥,不精没有多大价值。
北京协和医院董事会开会,医院开办投资方美国的主持者是孟禄博士;中国的主持者有胡适,还有金岳霖。胡、金两人相遇,胡拿来一篇文章(既有英文,也有中文两种文字)给金岳霖看,文章大意是说,哲学是一个没有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够好的科学。金点头说:“很好,很好。”胡很高兴。金又讲了一句:可惜你少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听罢,无话可说了。
对现实问题,胡适所见亦太浅。他反对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话,认为五大魔(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社会的五大病毒。
针对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还有人提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等),胡适认为要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梁漱溟指出,胡适特别害怕共产主义;共产党一来,他就跑了,跑到台湾,人是胆小!
梁漱溟对胡适的总结说:一个人有长有短,胡先生是很有见长的一面的。
自梁漱溟1924年(31岁)离开北京大学至其晚年,他又有很多朋友,与此前不同的是,前一阶段的朋友多为长辈;后一阶段的朋友多为晚辈和学生。而梁漱溟正是依靠这些友人和学生,才得以开展其乡村建设运动,才能够从抗日战争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正规这50年间感受朋友、晚辈的关怀和友情。
如果开列梁漱溟友人的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许多名字,如黄艮庸、朱谦之、陈亚三、王平叔、张俶知、云颂天、叶麟、李渊庭、席朝杰、吕烈卿、徐名鸿等;梁漱溟尊重的陶行知、卫西琴。
如果不单纯算友人、弟子;50年中,梁漱溟还接触过国民党要人蒋介石、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韩复榘等;拜访、认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同为乡村建设运动领导人晏阳初等的交往;与张东荪、张君劢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交往,等等。这些留待各章节中介绍。
黄艮庸原名庆,广东番禺县人。结识梁漱溟缘于梁在北京大学做宗教问题讲演,讲演场在第三院大讲堂,梁讲演长达三四小时之久,内容多涉及人生问题。次日,黄艮庸到缨子胡同梁宅,见到梁漱溟,深鞠一躬,满面涨红,竞因心情激动而语塞,少顷,乃告梁因头一日听梁讲演,深深触动其衷怀。梁漱溟后来对梁培恕言及此事,很动感情地回忆说:“他的痛苦极深沉,当时的神情,味道好极了。”
1924年,黄艮庸与陈亚三、王平叔、张俶知、徐名鸿等,随梁漱溟到曹州办学,年末梁离曹州回北京,留一信表示愧悔,说自己“昏妄不自揣量……半生盖未有无一毫自信力如今日者”。
王平叔写信批评梁漱溟做事轻忽,指出“藉来曹之种种扑倒观之,不实心踏地重新死炼苦修一番,将何以哉?吾师病实不轻,有转机否在真能一下回头不耳”。
黄艮庸亦写信批评梁漱溟:“吾人思之,一日之行,终身之志,终身之志,其确定否乎?如志已坚定,则日常生活有道可循,断不致凌乱也。如其不然,日云奋发,何所奋发?……每为浮气所隔,真心不见,反末为本,几希狂矣!所幸经此失败,尚有回头之一日。”
1925年末,梁漱溟派黄艮庸、王平叔、徐名鸿去广州,三人便随陈铭枢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1926年,黄艮庸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秘书;1927年任广东军事厅政治部主任。1934年黄艮庸随梁漱溟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班主任、训练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黄随梁漱溟赴山东敌后巡视。
梁漱溟与朱谦之在北大曾有师生之谊。朱藏书颇丰,梁得其助益较多。朱谦之逝世后,朱夫人何绛云还借给过梁漱溟朱遗留下的书籍。
陈亚三、张俶知等与梁漱溟关系很深的朋友,梁没有什么文字资料。陈亚三,山东郓城人。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追随梁漱溟左右: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后,陈先后任训练部主任、菏泽乡建分院副院长;1935年,陈任菏泽乡建实验县县长;1940年任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校长(四川重庆北碚);1948年又任教于勉仁文学院;全国解放后随梁漱溟来北京。陈亚三对先秦哲学、宋明理学颇有研究,在易经研究方面造诣颇深,深有道家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