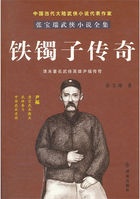自从几年前在钟陵踏歌会上见了这丑书生,玉娘一颗心就被他深深吸引。他的多才多艺、孤傲高洁,他的刚直忠诚、恬淡潇洒,无一不使玉娘魂梦长萦。她丝毫不在意他相貌丑陋和口吃缺陷,也不在乎他多次躲闪拒绝,竟如飞蛾扑火一般,义无反顾扑向自己炽烈真纯的初恋!
此刻她已将内心深处的情爱表白无遗,身为女儿家,还能怎样?
漫长的静默中,仿佛听得见两颗心激烈地怦怦大跳。陆羽几番张嘴,总是欲言又止。
慌乱中,他的手忽然触着一只碗边,那是刚才玉娘烹煮的醉莲茶,陆羽那碗已经饮完。这一碗,玉娘一直没喝,此刻早已凉了。
陆羽端起茶汤,仰脖狂饮,清凉的茶液立时沁透五脏六腑。他犹豫一下,把剩下的半碗茶举到玉娘唇边。
玉娘抬起眼睛疑问地望着陆羽。他一双明眸燃烧着激情,默默迎向她。
玉娘明白了,不由娇媚一笑,无限喜悦。
她勾下粉颈,就着陆羽手中碗啜一口。醉莲茶包含着莲花的神韵和茶叶的精髓,也渗融着他二人的情意,再无须语言。
玉娘一口一口啜饮,香茶如美酒一般令她如醉如痴!她情不自禁闭上两眼,仰起脸庞,湿润的红唇微微颤抖。
陆羽与她咫尺相对,耳鬓厮磨,如何能自持?只听叮当一响,茶碗滚落在地,他张开双臂把心爱的人拥抱入怀……和风轻拂,旭日升起,阳光照着一望无边的绿叶粉荷,照着碧纱窗内那一双紧紧依偎的人影……颜颇和石扇并肩北上,沿途难民忽如潮涌。原来仆固怀恩率领回纥大军,与各路节度使形成钳夹之势,将史朝义叛军从东京洛阳撵出。仆固怀恩乘胜追击,一直把史贼赶过黄河。叛贼大势已去,据守在滑州魏州一带顽抗,当地百姓只得纷纷南逃。
颜颇和石扇又是高兴,又是惋惜,只恨自己未能赶上这场空前激战。他们打听得回纥大营驻扎在东京附近,料想仆固琪和忆儿一定也在那里,赶紧转往洛阳方向。
行了十余天,路上逃难的百姓渐渐稀少,有人见两个少年往北而行,好心劝说:“快回头吧,回纥兵杀人如麻,洛阳去不得!”
两位少年如闻惊雷,急问:“回纥不是来帮忙打叛军的么?”难民大骂:“回纥兵赶走叛军,在洛阳城烧杀抢掠,比叛军史贼还狠!”
两少年面面相觑,心里想要不信,眼见难民悲愤之色,又由不得不相信,脚下急忙加紧赶路,又跋涉了数日,终于来到洛阳附近。
极目四望,田野里到处是尸首和丢弃的兵戈甲盾。远处浓烟翻滚,直冲天穹,凝结成望不到边的浓重黑云,遮蔽了太阳和蓝天。
颜颇惊道:“那冒烟的是洛阳城,咱们快去瞧瞧!”
两个少年逮了匹走散的战马,骑着赶往洛阳城,只见城门大敞,洛阳城中尸积如山,竟全是妇孺老幼!城内房屋大部分焚毁坍塌,残垣仍在熊熊燃烧,烈焰逼得人无法靠近。兄弟俩虽久历江湖,毕竟只见过小打小闹的杀人放火,如今突然置身如此惨烈的人间地狱,不由心如刀绞,呆若木鸡!
一阵寒风吹过,卷起大团大团的灰烬,在荒凉的田野间旋滚。
颜颇咬牙恨道:“好你个仆固琪!”
石扇怒道:“咱们在林邑拼命救了这假小爷,是叫她这么和亲的吗?走!咱们去找她问个明白!”
他俩早已打听到回纥大军驻扎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城外,当下急忙赶去。
河阳城紧挨大河,南北两城左右拱卫,河滩上布满帐篷,回纥兵有的在河边涮马,有的兴高采烈摔跤角力。颜颇和石扇伏在长草中远远眺望,不敢贸然上前。
颜颇小声说:“哥哥,你瞧大河中央那座石城。”
石扇一看,滔滔的黄水中央有片沙洲隆起,洲上果然有座小石头城,齐肩高的矮墙将它团团围着,一架大桥穿过小石城,贯通南北两岸。
他好奇地问:“那小城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建在河中央?”
颜颇道:“那叫中氵单城,围着城的矮墙叫羊马城。河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石头城建在河中央,是保护大桥的堡垒。”
石扇盯着看了一阵,发现河中小城有回纥兵把守,不由猜测:“回纥兵抢了洛阳百姓的金银珠宝,大概全藏在石头城里吧?等夜深了,咱们摸进去瞧瞧。”
颜颇道:“哥哥,金银珠宝算什么?找仆固琪要紧!”石扇忙说:“不碍事,咱们找仆固琪,顺带着找找珠宝。”
红日西下,夜幕降临。帐篷外燃烧起篝火,回纥兵围火烤肉喝酒,有人唱起悠长的情歌。熬到三更时候,回纥兵俱入帐睡了,只有几个游动哨来往逡巡。两位少年悄悄潜入营中,仔细查找一番,却没有一顶帐篷像是王后住的。二人正欲离开,颜颇忽地压低声道:“哥哥看那边!”
石扇凝睛望去,只见一团黑影闪过,鬼鬼祟祟奔大桥而去。两位少年心生疑惑,连忙拔腿跟踪。
黑影到了桥下,悄悄潜伏不动,待守卫的哨兵踱到桥头,突然从背后暗袭,哨兵一声不吭倒下,黑影窜过大桥,消失在小石城的阴影里。
两位少年随后飞奔过桥,钻进大河中央的石头城。城里四处寂无声息,淡淡月光照着城池中央一座小楼,楼上窗口透出淡淡灯光。石扇左右张望,道:“奇怪,那厮怎么不见了?”
话音刚落,突闻唿地轻响,小楼窗口跳下一团黑影,紧接着又有一道人影飞掠下楼,狂追前面黑影!
借着窗口灯光,两位少年看到前面黑影圆滚矮胖,正是刚才偷袭桥头哨兵的那厮。后头追赶的人不甚雄伟,身手却十分矫健。
两道人影一前一后疾奔而出,颜颇轻声叫道:“前面那圆滚滚的矮胖家伙,不是黄瓢是谁?”
石扇说:“怪不得瞧着眼熟,果然是黄瓢!”
颜颇道:“不知黄瓢在小楼里做了啥勾当,引得后头那人跳窗追赶?走,咱们进去瞧瞧。”
两少年溜进小楼,颜颇脚下踩着个软绵绵的东西,伸手一摸,却是具尚有余温的尸体。他暗想:“这准是看守小楼的哨兵,叫黄瓢杀死在这里。”
小楼共两层,下层房间里熟睡着一位白发婆婆和一位胖妇人,二人不敢惊动,蹑足上了二楼。楼上房门虚掩,二人探头一瞅,见室内点着琉璃灯,照着桌上明晃晃一堆金珠玉翠。靠墙有张大床,床上被褥凌乱,却并未睡人。
颜颇刚欲退出,眼角瞥见有东西晃动,忙看时,见床柱上扎着一把雪亮匕首,匕首尖上插着一张纸。夜风吹拂,那纸像活物一样迎风摆动。
石扇笑道:“这是飞刀传信,江湖惯用的手段。”
颜颇道:“黄瓢正是从这个窗口跳下去的!他飞了这刀,把床上睡觉的人惊动了,也从窗口追了下去。”
他拔下匕首,把信纸展开看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石扇问:“写的什么?”
颜颇道:“哥哥你瞧,是首反诗呢。”
石扇笑道:“哥哥识不得几个汉字,你且念来听听。”
颜颇瞅着信纸小声念道:
“‘蚌鹬从来苦空忙,吮痈舐痔实堪怜。唇亡齿寒今古事,何不回头看高昌!’”
石扇惊笑:“叽里咕噜,说的都是些什么?”
颜颇解释:“这首诗前三句都用的典故:蚌鹬相争,渔人得利;吮痈舐痔,卖身权势;唇亡齿寒是指虢国借道给晋国灭虞,自己终受其害的事儿。第四句——”
石扇忙道:“第四句我懂!高昌国帮汉天子打突厥,突厥灭后,汉天子就顺手收拾了高昌。”
颜颇说:“这首诗分明是警告回纥不要帮朝廷打史贼,用心十分险恶!黄瓢向来以皇帝世亲自居,为什么会送这种反诗给回纥呢?”
他疑惑地扫视室内,指着桌上的珠宝说:“这些珠宝丝毫未动,十分奇怪。”
石扇笑道:“有什么奇怪?黄瓢往床头飞那一刀,把睡觉的人惊醒了,他慌着逃命,哪里还顾得上珠宝?”
颜颇说:“这就是奇怪之处!黄瓢为什么不先拿上珠宝,再飞那一刀呢?其实他可以把反诗留在桌上,用不着飞刀扎床头柱,惊醒梦中人。”
石扇不觉惊心,忙问:“兄弟,你怀疑黄瓢故意惊醒床上的人吗?”
颜颇轻声答道:“我在摩牙岭住过两年,熟知强盗们的手段。黄瓢今夜不像来偷珠宝,也不像只为送这首反诗……”
石扇急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颜颇沉吟片刻,摇头说:“实在猜不出其中缘故。”
两位少年琢磨一会,都觉得这件事十分蹊跷,心想等那追赶黄瓢的人回来,或许能找到答案。然而等了又等,眼看东边天际已泛出鱼肚白,追赶之人却始终不见返回,他们只得悄悄离开。
第二天夜里兄弟俩仍旧潜入回纥营寻找仆固琪,发现回纥兵十分慌乱,河阳桥上布满岗哨,河滩边到处是巡逻的兵士。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桥上用回纥话破口大骂。有位回纥武将躬身站在老太太面前,满面惶恐听着。
老太太骂完,武将气急败坏转身,对守桥的武士们厉声吆喝,不知说的什么,只听出不时嚷嚷“可敦”二字。
石扇拖着颜颇一溜烟跑出营地,哈哈笑道:“他们丢宝贝啦。小回纥,着急去吧!”
颜颇不解,问:“哥哥怎知他们丢了宝贝?”
石扇从怀里摸出一堆珠翠,道:“瞧!那小回纥说的‘可敦’,意思就是宝贝。”
颜颇笑道:“原来昨夜哥哥拿了他们的宝贝……”
石扇脸色激变,怒问:“宝贝是他们的吗?都是抢洛阳百姓的!老爷要有本事,把回纥一个个全杀了!”
颜颇暗赞:“好个嫉恶如仇的胡人哥哥!”
又候了几日,不见仆固琪露面,那回纥大营却戒备森严,再也无法潜入。两少年眼见回纥兵个个如狼似虎,不敢再逗留,只得怏怏离开河阳,向西京方向而去。
晓行夜宿,这日已近潼关。石扇替颜颇高兴,道:“你流浪了这些年,总算可以回家了!我听说你爹保家卫国有功,升了刑部尚书,官儿大着哩。”
颜颇怔了半晌,摇头说:“哥哥的消息早已过时了。他老人家痛恨宦官弄权,率百官向老皇帝请安,得罪了宦官李辅国,被贬为蓬州长史。关山万里,竟不知何日才得再见他老人家!”
说罢悲从心起,潸然泪下。石扇连忙安慰他一番,把该死的宦官骂了个遍。
天色已晚,二人在路边人家借了一宿,次日动身来到潼关。
潼关离长安仅三百余里,潼关一失,京城便无险可守。此刻正是混战之际,潼关把守极严。田野中道路边到处是胡乱搭建的小窝棚,守关兵丁不时吆喝着,把聚在城门边的难民赶开。
颜颇二人直奔城门,守门兵爷喝道:“站住!拿路牒来!”
颜颇道:“兵爷,请行个方便……”那兵爷高声吆喝:“滚!没路牒,你就是菩萨他亲儿也不许进!”
说话间一队回纥兵打马东来,像阵狂风穿关而过。石扇怒问守关兵爷:“喂,他们怎么过得?他们有路牒吗?”
兵爷被马蹄踢起的灰尘迷糊了眼睛,满肚皮没好气,破口骂道:“小子瞎了眼?他们是胡人!”
石扇冷笑一声,说:“小子,你瞧瞧老爷是谁?”
那兵爷停下揉眼的手瞪着他。石扇拍胸笑道:“老爷也是胡人!快放我们进关吧。”
兵爷大怒,抢上两步,唰地就是一刀砍下。石扇闪身急避,顺势还他一掌。那兵爷没见过敢跟他交手的百姓,气急败坏大叫:“这里有贼党!”
城门洞里呼啦奔出十来位兵爷,把颜颇石扇围个严实。一位小头目模样的汉子喝道:“哪来的贼党?给我拿下!”
乱世中最怕的就是借贼党二字胡乱杀人,颜颇忙施一礼,赔笑说:“大人,我们不是——”
小头目懒得听,一迭连声下令:“拿下,砍了!”
突然一阵爽朗笑声从两位少年身后扬起,有人喝道:“谁敢拿我的人?好大胆子!”
颜颇急忙扭头,只见三骑人马立在身后,说话的是位英气勃勃的年轻公子,穿一身耀眼衣裳,挎一柄花里胡哨宝剑,一边笑,一边冲颜颇使了个眼色。
小头目慌忙施礼:“辛爷,您回啦?”
纨绔公子漫不经心挥挥手,道:“这是我的两位小兄弟,怎么?不让过关吗?”
小头目忙道:“不敢不敢!小的不知道是辛爷的人,多有得罪,嘿嘿。”
颜颇松口气,暗道侥幸。辛爷拉长声说:“我这两位兄弟把坐骑弄丢了,借两匹好马使使,行不行啊?”
小头目慌不迭答应,亲自去牵了两匹高头大马来,赔笑说:“辛爷要马牵去就是,说什么借?冷了兄弟们的情谊。”
辛公子哈哈大笑,打马扬鞭穿过城门洞。颜颇和石扇骑马傍着他一同入了潼关,众人这才缓辔施礼见过。
原来纨绔公子大名辛谠,乃当朝赫赫有名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之孙。另二人,一位五短身材老者,是江南蓑笠堂二当家金怀义;一位长身冷脸不苟言笑的,是辛谠的结拜兄弟范无心。
石扇听见“范无心”三字,不由一怔,凝神苦想着什么,只是想不出来。
颜颇报上姓名,辛谠惊道:“原来是颜公子?久闻令尊颜大人侠义舍亲,将公子作人质以图救国!今日得识公子,幸何如之!”
石扇刚欲报出名号,辛谠和范无心相视一笑,道:“你不是写‘王八’的扬州好汉吗?你那王八朋友正在洛阳同回纥干架呢。回纥近日丢了可敦,吵闹得紧。”
石扇又惊又喜,忙说:“原来哥哥们认得我?难怪,我也觉着范大哥有些耳熟。回纥丢的可敦,是小弟偷了。”
辛谠三人大惊失色,急问:“你偷了回纥的可敦?不是说笑吧?”
石扇从怀里摸出玉翠,得意洋洋笑道:“哥哥们请看。”
三人愕然瞪着玉翠,忍不住放声狂笑。颜颇见三人笑得蹊跷,连忙请教。辛谠忍笑答说:“回纥话‘可敦’,意思是王后。”
石扇哎呀一声,慌忙把玉翠塞进怀里。颜颇问:“回纥的王后不是仆固琪吗?她是个大活人,怎么会丢了?”
辛公子道:“登里可汗追杀史贼去了河东,登里可敦陪娘家人留在河阳中单城里,有天半夜来了刺客,把两个哨兵杀死,可敦也在那夜忽然失踪。刚才过去的那些回纥兵,就是寻找可敦的。”
颜颇和石扇恍然大悟——原来中单城楼上那只被褥凌乱的大床睡的就是仆固琪!大桥上骂人的白发老太太,一定是她的祖母了。
颜颇把那张写着反诗的纸拿出来,将当夜看到的情况一一说了,辛谠三人都十分诧异。金怀义对黄瓢十分熟悉,当即断言:“黄瓢大字不识,决计写不出这诗!我看他是受人指使,送反诗挑拨回纥与朝廷的关系。”
辛谠怒道:“上月怀恩将军与登里可汗在太原见面,家祖也收到匿名警告信,说怀恩与回纥勾结,要突袭太原。当时祖父难辨真假,不敢开城门犒军,怀恩将军愤恨不已,由此与家祖结了仇呢。”
颜颇急问:“究竟是谁搞这种挑拨离间的勾当?”
金怀义与范无心对视一眼,都沉着脸不吭声,仍是辛谠答道:“这正是哥哥们要追查的事情!”
一行人来到三岔路口。辛谠三人欲转道西南,石扇两眼瞅着范无心,嘴里说:“哥哥们去西南,我们也去。只要跟着你们,随便去哪里都行……”
颜颇忙道:“石哥哥,咱们必须去西京!”
石扇问:“为什么?”
颜颇道:“方才那些回纥兵匆忙赶往西京,或许已得着了什么消息。咱们跟在他们身后打听,说不定能找到仆固琪和忆儿。”
辛谠忙道:“有道理!你们见到登里可敦,千万要问问黄瓢的下落,查一查是谁指使他送那反诗!”
他略一踌躇,取下腰带上的玉环交给颜颇,嘱咐说:“若需要帮手,或是缺了什么,只管把东西给寒舍的管家们瞧瞧,他们定会认真去办的。”
大家一揖别过。颜颇满怀敬慕目送三人,感叹说:“范大哥不怒自威,令人且敬且畏;辛大哥貌似纨绔公子,实在是古道热肠,豪气贯胆。”
石扇闷不作声挠头苦想,忽然哇呀叫道:“范无心不是玎零的大哥吗?”急欲回头打听玎零的消息,哪里还追得上?只恼得捶胸叹气,沮丧不已。
兄弟俩扬鞭策马赶到西京长安,问明了大宁郡王仆固怀恩的王府所在,无奈侯门深似海,竟不得其门而入。他俩只得在附近找小客栈住下,每日到王府门外守候,等待机会打听仆固琪的消息。
一晃过了数日,几乎日日都有捷报飞传京城,报告仆固怀恩率兵追击史朝义的进展。东西两市张贴露布的牌坊下,从早到晚聚集着热泪横流的老少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