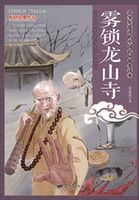陆羽见她突然支吾起来,不禁好奇,追问:“何况怎样?”
那婆子左右为难,叹道:“不能说!说出来得罪狐仙。唉,总之千万莫去……”
看到她欲言又止的样子,陆羽心里一震,忽然想起张婆说起李八叔时,也是同样的神情。
张婆究竟想说什么?她为何故意问起季兰,又吞吞吐吐?莫非她知道那李八爷有些不妥,怕得罪人不敢说?
屈指算来离开季兰已近半月,她若出了麻烦,却是向谁求助?转念至此,陆羽顿时心乱如麻,恨不得插翅飞回季兰身边。
一夜无眠,好容易捱到破晓,陆羽撇了近在咫尺的顾渚山,返身赶回乌程。
近百里路程,陆羽紧赶慢赶走了两日,这天入夜时走近李八爷家,只见院门大敞,院里聚着一些人,不知为什么事吵闹正酣。
一个听来有些熟悉的声气怒冲冲说道:“我不过想借二百两银子,你们推三阻四说了一箩筐废话,可恶!”
陆羽挤进人群一看,骂人的正是那日想接季兰回家的李二叔。
八婶发怒反问:“姪女儿空着两手走来,人人都看见了,二哥凭什么说她有钱?凭什么开口就要二百两?”
李二叔顿着手里的拐杖嚷道:“就凭着她是花魁红妓!就凭她进过皇宫!皇上的女人没钱,骗谁呢?”
李八叔冷冷反唇相讥:“长辈有这么说话的吗?季兰是清白女儿,卖艺不卖身的,二哥这么糟践她,真叫人寒心哪。”
李二叔一愣,站在他旁边的老妇冷笑一声,说道:“二弟,你该学学人家八弟,甜言蜜语笼络人心,不怕姪女儿不孝敬。”
八婶气得一蹦老高,大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大姐早就是刘家媳妇了,跑到李家搅什么劲?”
那老妇不甘示弱,揪着八婶喝道:“睁开你的狗眼瞧瞧——我是你丈夫的大姐,季兰的亲姑姑!你们夫妇想独霸她的钱财,呸,办不到!”
八婶愤怒推搡大姐,八叔上前劝架,李二叔的拐杖却招呼过来,几个人纠缠一团,顿时闹得不可开交。
陆羽看清人群中没有李季兰,赶紧扔了行李,奔向后院寻找。季兰躲在自己的卧房里,正抽抽噎噎,哭得伤心欲绝。
陆羽不及多言,拉起她边往外走,边说:“咱们离开这儿!”
季兰泣问:“离开这里,何处是归宿?”
陆羽怒道:“瞧他们一个个都打的什么主意?这儿不能呆了!”
季兰挣开他的手,哽咽道:“我不能再漂泊流浪,更不能回翠香楼……八叔八婶待我不错,这几日族里人轮流来借钱,都是他们替我挡驾。”
陆羽低声说:“我瞧八叔和八婶未必对你真好,只怕他们另有所图。”
季兰不信,急忙反驳:“我孑然一身无产无业,他们能图我什么?两位长辈都是亲情入骨,你别疑心。”
陆羽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模样,长叹一声,暗想:“她渴望有个家,竟不惜如此委屈自己!陆鸿渐呀陆鸿渐,你没能耐让她安居享福,真是惭愧啊。”
前院闹了半个时辰,总算曲终人散,季兰也噙着忧伤沉沉睡去。陆羽在月下徘徊,想着自己与季兰心心相印,却无处可以安身,实是愁绪满怀。
直到东方微露曙色,身心不堪疲乏,他才回房休息。刚要朦胧入睡,一声惊叫突然入耳,似乎是季兰的声音!
陆羽翻身跃起,急忙奔向季兰的卧室,只见房门仍紧闭着,窗户却开了半扇,窗内传出异样声响!
陆羽使劲敲门,室内的声响骤然加大,忽地有人痛叫一声,压低嗓音呵斥:“你敢咬人?你是婊子,装什么假正经?”
季兰发出唔唔求救声,陆羽不顾一切撞开门冲进屋里。清冷的月光映照着床上两个激烈搏斗的人影,陆羽愤怒若狂,上前一把抓住压在季兰身上的人,拼全身之力掼在地下。
那人痛得哎哟大叫,慌忙爬起逃跑。陆羽追出门外,飞腿踢去,那人向前踉跄几步,扑通跌倒在地。
此时李家人都已惊醒,纷纷赶往后院。那人正巧跌倒在提着灯笼的仆人面前,灯光下大家看得明白,被陆羽拿获的不是外人,正是李家的少主人阿贵!
季兰哭着追出门,看见倒地之人竟然是堂弟阿贵,不由目瞪口呆愣住了。
李八婶扑到阿贵跟前,想将他扶起。阿贵痛叫道:“我的骨头断了!哎哟……”
八婶见儿子受伤,心疼不已,指着陆羽大骂:“丑书生竟敢踢伤我儿,吃了豹子胆么?来人哪,把这穷鬼赶出去!”
仆人吆喝一声,上前来拖陆羽,陆羽喝道:“夜袭闺房,欲行不轨,这种衣冠禽兽律当处死,踢伤他算什么?走,咱们去见官辩个分晓!”
他拖起阿贵,怒冲冲大步走向院门。
八婶听说“律当处死”,顿时慌了神,连忙上前拦住,转怒为笑说道:“哟,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哪能欲行不轨?八成是起床撒尿认错了门儿。”
陆羽冷笑一声,刚要反问:“有从窗户误入的道理么?”那阿贵倒抢先叫道:“妈,我要讨花魁姐姐做老婆!”
八婶跺脚骂道:“糊涂孩子,那怎么使得?娶妓女做老婆,祖宗八代的脸面都要丢尽的!”
此言一出,季兰脸色刷地变得煞白,捂着眼睛摇摇晃晃连退两步。陆羽怒道:“季兰休听她胡说,咱们去官府告他!”
李八叔一直站在人群中没吱声,此时见陆羽执意要告官,冷冷问他:“你打算告什么?季兰本是青楼卖笑的粉头,难道官府还能判一个逼良为娼的罪名不成?”
这话说着了季兰心底痛处,当真恶毒至极!季兰羞恨堵胸,顿时昏晕过去!
陆羽心急如焚,大声呼唤:“季兰!季兰!你你你怎样了?”
李八叔冷笑道:“一个穷书生,又丑又结巴,为何粘着季兰不放?还不是图谋她的钱财吗?来人哪,把这位‘贵客’撵出去,永不许进我李家门!”
陆羽只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李八叔结结巴巴喝道:“你你、你好无耻……”
季兰悠悠醒转,只觉心灰意冷,泣道:“鸿渐,不用多说了,咱们走。”
陆羽情知再闹无益,就是告到官府问阿贵的罪,终归也会让季兰受伤害,只得强忍一腔怒火,搀扶季兰离开李家。
刚走到大门口,忽听脑后一声断喝:“姪女哪里去?”
季兰回头一看,八叔八婶都瞪着大眼。她向二位拜了一拜,道:“今日之事,季兰不再追究,请二位长辈对阿贵晓明利害,以免日后惹祸。”
李八叔笑道:“到底是至亲骨肉,姪女很明白事理,八叔一定好好教训那混小子。姪女受委屈了,快回房歇息吧。”说罢朝八婶使个眼色,八婶嘻嬉笑着,上前来拉季兰。
季兰一愣,不知他夫妇为何转眼便若无其事。她恭敬再施一礼,说道:“承蒙叔叔婶婶垂怜,恩情永铭在心。八叔,八婶,季兰这就告辞了。”
八婶顿时脸色一变,跳脚嚷道:“咦,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今日说走就走,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你要走,拿钱来!”
季兰吃惊地看着她,张嘴欲言又止,将自己腕上戴的两只玉镯取下,抖着嗓音问:“这对玉镯是皇上恩赐的,不知能否抵得叔叔婶婶的饭钱?”
八婶听说是皇上赏的东西,急忙一把夺过。李八叔尴尬地笑了两声,道:“都是至亲骨肉,叔叔哪能收姪女的饭钱呢?姪女无家可归,不如仍住在八叔家……”
季兰毫不迟疑,毅然说道:“姪女已将终生幸福托付给这位陆鸿渐,他在哪里,季兰就以哪里为家。”
陆羽心中又感动又痛苦,紧紧握住心上人的手,向大门走去。
突然人影一闪,八婶拦住了去路。陆羽怒问:“你还想怎样?”
八婶指着他骂道:“丑小子手段了得,竟迷住李家姪女,独吞百万钱财!哼,你就不怕李氏家族找你算账吗?”
季兰惊问:“婶婶说的什么?我哪有百万钱财?”
八婶冷笑道:“别装蒜了,你是当朝红妓,老皇帝的情人,不要说百万钱财,只怕千万都有!”
季兰气得发抖,急切间竟无从辩解。陆羽瞪着八婶怒问:“季兰就有千百万钱财,与你何干?”
李八叔缓步上前,笑道:“这话问得奇怪,李季兰是我李家的人,她的事怎么与李家无关?季兰是最懂亲情的,八叔说得对吧?”
见季兰沉默不语,他趁势又规劝:“姪女呀,八叔知道你把钱财都藏在苏州了,不过妓院那种地方,鱼龙混杂,十分靠不住,不如拿回来,让长辈们替你照应着,才好安安心心过日子。”
季兰心中雪亮,对这份亲情已不存幻想,然而看眼前阵势,不把钱财之事交待清楚是决计出不了门的。只得说道:“当年苏州太守帮我脱籍,鸨婆搜去了我所有的积蓄。在皇宫时,皇上虽多有赏赐,奈何安禄山叛军突然兵临城下,姪女仓促出逃,哪里顾得上其他?姪女的全部钱财,就剩了身上衣裳和这对玉镯,请叔叔明鉴。”
她言语诚恳神情哀婉,李八叔察言观色,情知她所言不虚,不由得发阵呆,眼看着一张黄脸渐渐变成了铁青色。
这阵吵闹早惊动四邻八舍,男女老少挤了满院看热闹。大家见李八叔尴尬,都笑起来,七嘴八舌议论不休。
八婶十分恼火,指着丈夫气鼓鼓骂道:“瞎了眼的,抢着把穷鬼接来当金枝玉叶伺候,这下亏大了!”
有人接口讽刺:“老八认准她是摇钱树,哪里知道千里眼也有看错的时候呢?哈哈!”
人群乱声哄笑,八婶扭头找这可恶之人,原来又是李二爷。她刚要跳脚大骂,眼光忽然瞥见二爷身后的人,急忙转移敌手,指着那人埋怨:“七哥,都怪你,害得我们好苦哟。”
那人斥道:“勾心斗角谋人钱财,你该知道羞愧,还胡唚什么?”说罢走出人群,抱拳朝季兰一揖,道:“妹妹受委屈了。”
季兰定睛打量这人,见他四十出头,身着青布长衫,容貌清瘦文质彬彬,看去有些眼熟。
她正在疑惑,此人又笑道:“刚才我听老八叫你姪女,那却大谬不然!咱们的曾祖是同一支脉的堂兄弟,论辈分该是兄妹。”
人群爆发出大笑声,李八爷脸上挂不住,悻悻甩袖钻进屋内。八婶气急败坏嚷道:“七哥早先为什么不说清楚?光说咱们家族出了个才女,连皇帝都慕名召见,在京城大为风光……”
李七哥不理她,俯身问季兰:“妹妹想去哪里?我已备了车在门外,即刻就可动身。”
季兰踌躇望着陆羽,陆羽暗想:“天可怜见,李家居然还有这么一位恭谦知礼的正人君子!”
陆羽忙跟季兰商量:“咱们先找皎然,再想别的办法,行么?”
季兰想想也只有如此,对李七爷说:“有劳七兄,小妹要去杼山妙喜寺。”
李七爷点点头,引着二人走向大门。村民们似乎对他很是恭敬,纷纷躬身让路,连蛮横的李八婶也不敢再多嘴,噘着嘴让过一边。
门外果然停着一辆马车,篷盖流苏十分讲究,却并非寻常乡下百姓用的家什。季兰更加疑惑李七爷是与自己有过交往的,只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踌躇片刻,施礼问道:“不知七兄……”
李七爷知道她要问什么,笑道:“愚兄在京城做校书郎,昨日回乡省亲。妹妹当年奉旨进京,曾前往芸阁借书,见过愚兄的。”
季兰哎呀一声,恍然大悟。李七爷又笑道:“那时妹妹身边人多,愚兄没有说话的机会,咱们兄妹竟是相见不相识了。”
遥想起当年情景,季兰只觉无限伤感,含泪拜别七兄,与陆羽乘车往西南而去,半日便到了杼山。
杼山妙喜寺是江南著名的古刹,坐落在一片修竹茂林中,东南紧傍悬崖,西北有避它城,寺前一座飞檐翘角的黄浦亭,亭旁小桥横跨碧流,青石路蜿蜒通向庄严宝殿,景致美不胜收。
皎然听小沙弥报二人来访,急忙迎出山门,一见季兰不由惊问:“分手不过月余,怎么憔悴至此?”
季兰压抑许久的悲愤顷刻爆发,只哭得气噎声咽,说不出话来。
陆羽亦是满腔愤怒,把寻亲所遇一一告诉皎然,皎然叹道:“阿弥陀佛,红尘世态炎凉,这也不足为奇!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陆羽踌躇难答,只把眼睛望着季兰。
季兰回想李八兄嫂所说那些刺心的话,又想吴婆婆对自己的蔑视,心中有如刀绞,暗想:“像我这种女子,断断不能与俗人同住一块天空之下,以免平白受辱!唉,鸿渐空有爱我之心,却无助我出苦海之力,奈何?”
左思右想实不知该向何处,她心酸难忍,赌气问皎然:“这附近可有道观?”
皎然不知她想什么,老实答说:“有啊。太湖有个开元观,最是幽静。”
季兰心一横,道:“好,我这就去开元观出家当道姑,万千烦恼,一了百了。”
陆羽大惊失色,急说:“不不不可!季兰,你你……”
皎然也吃了惊,道:“阿弥陀佛,你这么年轻,岂能青灯黄卷陪伴终身?贫僧出个主意吧——妙喜寺后有幢小屋,以前住过香客,现在空闲着。季兰可暂借此屋安身,鸿渐在寺里住着,大家来往都方便,如何?”
陆羽大喜,忙说:“如此甚好!”
二人跟皎然来到寺后,果然绿茵中有座小茅屋,屋里床铺桌凳齐备,连灶具都有。皎然从寺里拿来干净被褥,陆羽动手将灰尘扫去,向季兰深深一揖,道:“从此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执帚事炊,晨汲暮织,你可应付得了?”
季兰早把一腔幽怨抛开,高兴地打量小屋,道:“哎呀,终于有自己的家了……你要答应我,不许嫌我做的茶饭难吃!”
陆羽笑道:“鸿渐岂敢!只怕你嫌我食量太大哩。”
三友哈哈大笑,俱觉前景喜人。
自此季兰就在这屋里当起主人来,陆羽皎然陪伴着她,或谈诗论道,或烹茶弹琴,过了一段安闲宁静的日子。
季兰学问才艺出类拔萃,执帚事炊却毫无天分,虽勉力学做,烧出的饭菜总是非咸即淡。好在陆羽“吃”的心思全部凝结于茶,对饭菜根本不在意。
看看惊蛰已过,春分将近,又是采摘新茶的好时节。陆羽心里记挂顾渚山,有些坐卧不宁起来。季兰觉察到他的异样,旁敲侧击盘问。陆羽叹说:“顾渚山地势凶险,你是万万去不得的。我不忍撇下你,又放不下那明月峡里的好茶……”
季兰打断他的话笑道:“这有什么难的?我陪你到顾渚山,你自去探险,我自去踏青,各寻各的乐趣就是了。”
陆羽还待犹豫,皎然说道:“久闻顾渚山风景奇妙,却是一直无暇瞻仰。趁春光大好,咱们这就去吧。”
陆羽大喜,急忙收拾家什,仔细备齐要用的东西。第二天天刚亮,三友离开杼山,雇车往顾渚山而去。
一路翻山越岭,不几日已到顾渚。季兰看那顾渚山形态秀美,翠峰笼罩在洁白的雨雾中,显得十分娴静。她笑对陆羽打趣:“明明是仙境福地,你为啥不许我来?哎哟,不要是有位狐狸精在这儿等着你吧?”
陆羽见皎然微笑,有些发窘,忙指着前方说:“咱们且在那户人家暂歇两日,待天放晴了,才能上山采茶。”
陆羽走向村舍求宿,这家的婆子却还记得他前阵子来过,笑嘻嘻迎上前刚要打招呼,突然看见紧跟在后的季兰,张大嘴巴一愣,问:“处士刚从明月峡来吗?”
陆羽见她神态惊慌,十分不解,笑道:“我还没去明月峡哩,婆婆怎么料定我从明月峡来?”
婆婆两眼盯着季兰仔细看看,嘴里说:“处士不要诓人,明明你已经去过明月峡了!”
说罢恼火地瞪陆羽一眼,掉转头往屋里走。
陆羽追上前问:“婆婆,我们想借宿几天,行么?”
老婆子两手乱摇,一迭连声回绝:“使不得!使不得,处士去别家吧!”头也不回钻进屋,哗啦把大门关上,竟是再不理睬。
皎然提着行李过来,见二友在门外发呆。陆羽道:“好奇怪!上回我在这家借宿,老婆婆十分殷勤好客,怎么今日突然变了?”
皎然笑道:“游方之人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换一家试试,说不定就碰着好客的了。”
这顾渚山下只有寥落十来家住户,三人连找几家,竟然都被拒之门外。季兰心下忐忑,问:“我脸上有何异样?他们个个盯着我呆看,叫人毛骨悚然!”
陆羽认真瞧着她,笑道:“山里人定是没有见过你这样美如天仙的人,所以情不自禁发呆。”
季兰啐他一口,娇羞笑嗔:“你几时也学会了花言巧语?讨厌!”
陆羽和皎然相视一笑,走向前面村舍。这家人只有位鳏夫带着儿子过活,他把季兰瞅一眼,没说二话,爽快收留了借宿之人。
一连几天阴雨绵绵,三友困在农家无法出门,心情很是烦闷。季兰道:“哎呀,顾渚山就在眼前,咱们赶紧把茶叶摘了,去湖州城玩玩不好么?”
陆羽摇头说道:“采茶岂能随心所欲?雨天不能采,晴天有云亦不能采,咱们还是耐心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