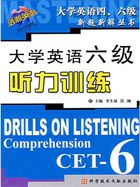只是一个过程
付坤很少跟人谈起童年时的往事,就像把岁月留下的记忆积淀成琥珀埋藏心底。偶而朋友相聚掇上一顿,借着酒劲乱侃一通,更多的时候是回忆童年经历过的事情。当有人追问付坤你咋不说呢,付坤喃呢地轻叹:“往事留下的心痛,似伤口不想去抚摸。”听着付坤悄声低语,朋友们都说他玩深沉,不就是在挨饿那年出生,经历过的事情也不会太离奇,毕竟是远离,战争,远离水深火热,也没经历政治牵连,因为出生在历史苦大仇深的清白家庭。
朋友们的再三追问下才知道付坤跟死亡有过几次接吻。
在出生后的那几年,因为营养不良,导致付坤体弱多病,经常住进医院。在六岁那年,父亲去上班,母亲跟其他的家庭妇女去革命委员会的那间屋跳当时流行的忠字舞,每天必去,这是当时的政治任务。
付坤家住在万新的矿俱乐部不远三层楼,前楼依山搭设维修楼顶的脚手架和跳板,几个十多岁的孩童爬到楼顶去玩,付坤觉得好奇也随着爬上了三层楼顶,天真的孩子不懂啥叫危险,也无大人照看。嬉闹一会儿那几个孩子顺原道跑了下去。付坤瞧着三层高的楼下,腿有些发软害怕,觉得天旋地转就闭上眼睛退着往回爬。悬空一落没等感觉到什么就摔落下来,母亲知道后哭着抱付坤就往医院跑(矿医院离事故发生地不远)不幸中的万幸仅是跟死亡亲了个吻,没有留下残疾,只是擦破了点外皮,医生直称是奇迹。
父亲为这事跟母亲大吵一架,觉得母亲没有尽到职责呵护好孩子,过了几天就领着付坤去上班。付坤跟父亲到了班上后,感到什么都是新奇,在厂里大院玩耍,有一只蜻蜓落在离付坤不远的厂内专用铁道旁的草丛的枝条上,付坤觉得好玩就去捉,追呀撵呀开心极了。就在横跨专用铁路道岔时左脚被卡塞上了,抬不起脚来急得他直流眼泪,偏巧远处驶来辆电车,哎呀越着急越拔不出脚危险就要发生了,吓得蹲了下来闭上眼睛不知所措……
“谁家的孩子——危险!”有位伯伯看到了付坤正在危险之间,急忙跑了过来,顾不上说什么,帮付坤拔腿。电车越来越近鸣笛声一声急过一声,在电车距三十米时总算把脚拽了出来而鞋挤卡住没能及时拿出,伯伯抱起付坤闪到一旁,电车就急驶过来……一双小鞋被车轮碾得有些变形了。
“伯伯你别去告诉我爸好吗?”付坤害怕父亲知道会揍自己,仰起小脸,泪眼吧擦地求伯伯。伯伯把付坤抱进休息室没说什么。后来听说父亲因这事挨了批评。从那以后很少领付坤去班上了。
经历过这二次对生命有危险的事情,母亲对付坤呵护有加,真担心再出现什么闪失。整日的留在家中不让出屋。
有一次,母亲要拆洗旧床被,那时付坤才只有七岁,就跟妹妹抢着帮忙干活,母亲就给了付坤和妹妹各一根针。也许应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妹妹手中的针挑被线时无意的刮扎到付坤左眼睛,当时觉得痒痛没当回事。父亲下班得知后,领着付坤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眼睛能保住,手术后视力也只能达到瞧什么东西模糊……
这次的伤害改变了付坤一生的经历,因为付坤心理知道自己从此成了残废,只有一只眼睛好使。
这一切能怪命运吗?谁又说这不是命运捉弄人。童年不幸的经历,就如那时的疯狂的年代。当这一切随时间远离我们,酸甜苦辣封冻了一个季节很长的季节。而朋友让付坤侃谈他能说什么呢?
生命像小溪般的流淌,人活着只是一个过程……
你的明眸里,荡漾着春风和秋雨,蕴含着隽永的诗意和优美的韵律。
为你击掌
就这样的坐在桌旁,什么也不用去想,被浓浓的夜色沐浴,让疲倦的心灵去拥抱寂静,仿佛在异域的我倾听到你的心跳,你的私语。这时你在干什么呢?是沿着铅字的小巷寻找埋在深层的矿藏,是用笔倾述世间给你的感悟,或是把有哲理的诗文包容着禅机著进书里,又仿佛你在与仙逝的哲人对话交流……此时夜色更浓,形成夜的汪洋,你能感到你是个很出色的水手,在波涛骇浪中搏击,不,你是遇惊事而不怯,遇险事不慌指挥若定的船长,让生命之船迎风破浪。
就这样总想找机会与你交谈,吸吮你那坚韧求索的精神,你是寒冻给人温暖的小屋,把朋友渐寒的心意烘暖,谁又能知道呵你所承受的痛苦是文字所无法描述的,就向翅膀受伤的海燕,挣扎着搏击着风浪,你默默的在书海中耕耘,种植明天。受你精神感动的不仅是我,就像干旱的季节所洒落的雨珠滋润着求索的人们。我在心里无数次祈祷,祈祷,祝你一生平安。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在寂静的夜晚,浓浓的夜色淹没着一切,我有些困倦有些孤独,被无数栅栏围绕着心灵承受着孤单与寂寞,这时我想起了你,纤弱的手指弹奏着命运的交响曲,激昂的旋律倾述着与命运的搏击……震撼着我的心灵。
好样的朋友!我诚挚的为你击掌。
你的生命是一团火,发着光和热,你的生命是常流的水,奔流不息……
二十三岁的你(外一篇)
被梦覆盖着的向往,稚嫩欲滴的年龄,如桃花般艳丽。这一切从你的指缝间滑走,可你甜润的声音仍似童年的画笔书写着人生。二十三岁的你,依然如故纯洁如水,袒露着充满柔情的真挚。
二十三岁的你是绽放的花朵。你已真的懂得了忧郁与困惑,沉思中感悟出影集里褪色的身影。你留恋逝去的一切,不再是无忧无虑,尽情享受阳光沐浴的苞蕾。
二十三岁的你面临着选择,这是一个故事的延续。你不再从书中寻找自己的偶像,懂得了面对现实,时间尽情地吸吮着生命,而你寻找着的是一次机遇撞击出的火花。你把情感大块地种植在日记中,锁进隐秘的心里。
你喜欢荷花的品行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爱。岁月匆匆,世界依然,凋谢与繁衍循环着是一种规律。二十三岁的你懂得珍惜抓不住的时间。
二十三岁是一道题,既简单又复杂。
无烛的夜
是谁掩上门窗遮上帘,留下漆黑的夜晚。烛光,伴我悠悠无眠。星星补缀的夜,是求索的眼,“蜡炬成灰泪始干哟,那是无可奈何”,有位诗人这样写过。
飘忽中越过山峦,在唐诗宋词的小巷里品味甘甜,醒来才知这是梦幻。今夜无烛,灯光璀璨,在稿纸上撒下的是心潮波澜。
给我一道闪电,我是惊雷掠过布满乌云的天空:
给我一声扬鞭,我是骏马奔驰在草原。
我是瀑布,我是山川,我是大鹏,也是无烛之夜求索的眼。
思绪奔驰着似脱缰的烈马,奔驰在岁道的空间。要穿越空幻呻吟的日子,也要跨过平庸的风景线……
你说,你爱天空的宽阔,大海的伟岸;我说,你就有天空的神魄、大海的气概。
把握人生
我参加市里的一个会,会间发现一个女同志,不时地在看着我。我在脑海中迅速搜索记忆,啊!是她!王晓辉。她长大了,亭亭玉立,比以前受看了,漂亮了。
会散了,她匆匆地走到我的身边,试探地问我:“你是三哥吗?”我说:“我已经看出你来了。”她高兴的像个孩子。她是我的邻居,又在一个小学读书,只是我比她高四年级。她一直叫我三哥,那时在学校里有一个“大哥哥”,自然会得到同学们的关照。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却逐渐地疏远了;学校的变更、家庭的搬迁,竟使我们不相往来了。
我们一起走出会场,走了不知有多远,互通了各自家庭和个人的情况。她问我:“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我屈指一算:“五六年,今年是七零年,哎呀!整整十四年了。”我惊讶的是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结婚。我问她有没有心上人,她深沉的看着我、摇着头。
自那次见面后,第二天就收到她的一封信,这封信足足使我几夜没有睡好。她在信中说:以为今生再也不能见到你,但总是不相信,还是老天有眼——你不是问我可有心上人吗,你是我心目中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播下了情苗——这件事家里的人都知道,父亲临终前,还嘱咐家人设法找到你。
收到她的信后,为使她冷却一点,没有急于回信,不曾想到,又接到她的第二封信。大致内容是:“你真该死,是信收到不愿回,还是落到别人手里?害得我几夜难眠——”我冷静地想,这事已经是不可回避了。就这样,我不得不给她写了回信:“我们在一起的美好的童年是难忘的,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而我已经是孩子的父亲。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切要面对现实,要冷静的处理好事情——”
情感的纠葛不是短时间所能奏效的;她在我心中,也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在一起时,她还小,似乎没有长开,而现在,她成熟起来,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动人,竟使我感情翻滚,难以自制。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在南昌参加同一个会议,暇时,我们信步来到赣江边,漫天的大雪,把这座英雄城市打扮得分外妖娆。我说:“晓辉,你还记得我们过去读过的《滕王阁序》吗?”“怎么不记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说:“可是王勃做《滕王阁序》时却是‘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色紫’而现在——”还没等我说完,她立即接着说:“而现在是:‘时维腊月,序属岁末,赣不清而白云遏;气象新而漫天白”“晓辉,你的素养真有长进了。”“这都是跟你学的。”她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跟过去一样,像个顽皮的孩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童年。
她挽着我的手臂,宛如一对恋人。我信口说出:“飞雪迎春到!”她接着说:“犹有花枝俏!三哥,你是我心中的花——我爱你!”“竟说傻话,我是你的哥哥呀!”“不是,不是亲的——”停了一会,又自语的说:“嗯!比亲的还亲。”
为了不刺激她,常常通信、也打个电话、偶尔出去转转,吃顿饭。话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你已经快三十了,个人的问题该处理了。”她总是深沉的看着我。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在北京办完事,同乘一个车回沈。在车上,她说:“我妈听说你在沈阳,总想见你。”啊!是我的不对,十五年了,从小疼我的母亲,该是什么样子?真是有点想她。我说:“好,下车先到你家。”到了家,母亲留下一个字条,说到本溪大女儿家去了。
她忙着做点方便食品。坐了一夜的车,真有点累了,饭后,她说,我也有点累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躺在沙发上打盹,不知何时,她却半躺在我的身上,我实在不忍心推开她,我悄悄地抱着她,她把脸贴到我的脸上,凑到我的嘴边,我第一次吻了她。我用微细的声音说:“晓辉,你还是处女,而我——”“我不管!”我看着她那胸脯一起一伏,理智让我不能非分,只是一动不动地抱着她。她说:“你真坏,这么多年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却这样痴情。”我说:“我心里始终有你,只是在外地读书,又在外地工作——”不等我说完,“借口借口!你不懂得一个女孩,第一次纯真的爱!”
我回到家里,在一个轻松的晚上,我很认真地,和她——我爱人,述说了和晓辉交往的全过程(应该说还稍稍的留了一点)爱人是我的大学同学,通情达理,彼此很信任,我们商定如何处理好这件事。
一个星期天,我们把晓辉请到家里做客。我们无拘无束的谈着童年时的友情,时时发出发自肺腑的笑声,吃饭时我们都喝了不少酒。
后来,我们为晓辉介绍了几个对象;她自己也找了一个,让我去看。最后选中了一个司机,人品很好,待人诚恳。结婚时,我作为娘家客人,讲了一些祝福的话。
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每逢过年过节,她们全家一定到我家来。孩子们给我拜年,亲切的叫我“老舅”,我每个人都给“红包”。我们是真正的亲人、真正的兄妹。
你像出水的芙蓉、傲雪的红梅、凌寒的青松;你坚强、果敢,让生命在困境中开出最美的花,结出最甜的果。
钓鱼
稿子不发就没有劲头儿,将笔一投,不干了。上午悠悠荡荡,下午昏昏沉沉,到晚上再爬格子,可看见沉沉夜色就发困。一天无所事事,悠闲也好,无聊也罢,给自己一句安慰——来日方长。
也不能白坐部队的办公室,终要拿出一点东西出来的,下基层连队搜寻点儿新闻苗头去。叫车那是摆谱,五里的路,走。别只捧本书,给舞文弄墨挂一个招牌。路过一池边,见一白发老人正在闭目悠然垂钓,就上前搭话:“老大爷,修炼啊!”
老人头也不抬就甩给身后一句话:“老和尚修,小和尚练,不修不练是混蛋。”
我不由得心里一惊,说谁呢?这时鱼漂儿一沉,显然一条大鱼上钩了。老人挥力一甩,鱼飞出水面稳稳地落到老人的手中。老人小心翼翼地摘下鱼看了看,顺手又扔回渔塘。再看看老人的鱼桶,一条都没有。我疑惑不解,忙问道:“那你在钓什么?”
“笨蛋,钓那些没有钓到的。”
我不敢再吱声,静静地看着这位“仙人”,想从他身上悟出点儿什么来。这时,夕阳已渐渐落下,老人收拾起工具,准备往家走。我抓住时机又上前问道:“明天打算怎么钓?”
“先把今天的事干好再说吧!”
“你也没干好啊,一条鱼都没钓到。”
“小伙子,你还不知道这‘钓’胜于‘鱼’的道理吧!”老人头也不回径直向前走,消失在夕阳里。
归来一夜没睡,伏案暝想,就写这个小品,供大家来嚼。
我十分欣赏你的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快乐心灵
在街上无意中听见两个人聊天,一个说:“活着真累。”另一个说:“是呀,活着没意思。”不知从何时开始,烦恼和悲观成了都市人的通病,我不禁在想快乐真的离我们那么远吗?
记得在山城工作的时候我主持一档晚间谈心类节目,由于节目的定位是“倾诉心事”,所以参与节目的人多是些“失恋、失意、失业”的朋友,但有一个叫格格的听众很特别,她每次参与节目都会说一些快乐的事情,还会讲些哲理性的小故事,声音甜甜的,很容易让人记住。每当我接过她的电话心情也为之振奋起来。她告诉我她在学计算机,她要把考级证书作为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她会把祝福毫不吝啬地送给那些参与节目的不快乐的人,时间久了,许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她,我想,这样的女孩一定生活的很幸福,她长的大概很漂亮吧!
一天,有几位听众朋友到办公室来看我,说是只闻其声,想见见其人,其中一个女孩吸引了我的注意,二十多岁的样子,大大眼睛,长发垂过肩膀,甜甜的笑容挂在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打扮也十分洋气,穿着休闲的淡粉色长裙,当我顺着裙角往下看时惊讶的发现,这么美丽的女孩竟坐在轮椅上,这时候有人介绍她就是格格,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曾带给我们那么多快乐的女孩竟会是身体有残疾的人,但更多的是让我觉得感动,真正的快乐就是不论自己如何的不幸也拥有一颗快乐的心,用一种快乐的心态去感染那些不快乐的人。
快乐隐藏在琐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更多的时候她不是财富,不是权势,而是一颗积极向上的健康的心灵。
你像一块白玉,毫不掩饰,那么纯朴自然,高兴时大笑,悲痛时恸哭,活得那么坦率。
茶情
我不怎么喝咖啡,不是说咖啡不好,主要是因为喝茶太久的缘故。喝茶是从父亲那继承的。那时候喝茶很简单,无须讲什么,当时也不知道喝茶还有那么多讲究。那时候条件很差,家里只能喝到最便宜的花茶。就是这样的茶,我仍可品出一份清香,这或许就是给喝茶人的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