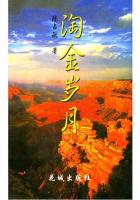自此,天鉴就注意起自己的衣着行头,每日洗脸漱口,衣帽穿戴得整整齐齐。夫人没在,又无双亲,饭食即便是糙米捞饭加一碗白菜豆腐汤,也要坐在那四方桌上用膳,尽量细嚼慢咽,不弄出些响声来。衙里衙外一班公干见知县庄重严肃,也不敢随便懈怠,天鉴便信服县丞老家伙是个油子,大凡一般出门应酬一事都要请教一番。但是,县丞几次暗示他去看看托病在家的巡检,天鉴不去,推不过了,骑驴子去走动一回。巡检家是县城的大户,后背街的一条巷子全是他家字号,看望完毕出来,天鉴只觉得自己瘦,毛驴也瘦。想,一顿饭,端菜上果的就十个丫环,席间那老太太过目一份收租清单,说西王寨某家怎么少交两担谷子,发话让去清查,厅外伺立的家丁竟应声如雷,少则也是七个八个的。巡检家这等威风,倒胜过县衙了!哼,我要是不当这个官,你巡检家的金条今晚就没了!巡检在招待天鉴的时候,用的是客厅里的一方嵌包了玉石的八仙大桌,那玉石并不甚大,但挪动时两个粗笨的丫环竟未能抬起。天鉴立即知道这桌子里的机关了:玉石下边必凿了槽子,藏匿了金条的。走在街上,当然有人就认出知县老爷,胆小的赶忙要跑进门面里去,跑进去了又隔了门道和窗缝往出瞧看。胆壮的便立定,给老爷笑,笑很长时间,直候到他的驴子噗嗒噗嗒擦身而过。或是拦道跪倒在驴头前,呼声:“给老爷请安了!”天鉴只是拂拂手往前踅行。便见一人箭一般从横巷窜出,后边紧迫的只是一女人。逃跑的人蓬头垢面,因被追的急了,一只鞋已经没有,双手却捂着一个馒头吞咬,险些撞到驴头,就站住了,转身面对追来的人,一口唾沫吐在馒头上。追赶的女人也就止步,骂道:“你这强盗不得好死!上山砍柴你滚个血头羊,下河挑水你溺长江,挨砍刀的,得传症的,生娃娃没个屁眼!”天鉴在驴背上喝道:“哪里泼妇,骂得这么难听?!”那男女这才发现驴背上坐的什么人。女人就跪下了,说:“禀告老爷,他是强盗,我才买了一个馒头,还未吃上一口,就被他抢去了。这些下河人满城都是,东关化觉寺门口舍饭棚拥了几百号的,个个不是贼就是盗!”天鉴说:“这些我知道了。好了,这个馒头老爷断定让他吃吧,一个铜子够价吗?”从怀里摸出一枚硬的丢过去,对那男的说:“这馒头是你的了,吃吧。”男的狼吞虎咽,直吃得梗脖儿,吃完了,睁着白多黑少的眼珠子看天鉴。天鉴说:“饱了吗?”男的说:“没饱。”天鉴说:“跟我来吧。”骑了驴子就走,拿眼看街两旁的铺子,就于一家店门口下得驴来,先看了看门板上红亮亮一副对联没有写字,却只用碗按在纸上画得的十四个圆圈,笑笑,喊道:“掌柜的,有馒头拿出五个来吃!”
这是一间门面并不大的店铺,四张桌上有五个人正在用饭,见知县进来,慌忙抹了嘴就出去了,街上的人却围在台阶下往里看稀罕。正厅间有个偏门到后院,后院有一等人横七竖八地在草铺上闷睡,瞧见街上人往店里探头,也好奇从偏门往厅间看。天鉴不理会这些,见掌柜还没踪影,又叫了一声:“掌柜的,怎不快些拿出馒头来!”柜台里的帘子闪动,便有女人一边在头上挽头发出来,一边不耐烦地说:“谁呀谁呀,紧天火爆的,馒头总得蒸得熟呀!要吃五个,什么样的大肚汉?”一举头,却呀地尖叫了,手一松,挽成团饼状的乌发瀑布一般泻在后背:“天呀,河水往西流,太阳也从西边出,知县老爷要吃我的饭了!”
天鉴看时,女人竟是雾晨里见过的王娘,浑身有些不自在了,起身要走,又觉不妥。正在尴尬处,女人已侧身揖手问安了。咫尺之间,尤物一腿微屈,一腿提起,弓弓窄窄的一只小脚恰恰点地,将印花围裙系着的一件桃红旗袍裹弄得了美美妙妙的弯曲。王娘说:“老爷能到小店来,王娘的脸有盆子大了!”
天鉴听跛腿的衙役说,王娘开的是香茶店,现在却卖起饭菜来了?就说:“王娘在这店里打工了?”
王娘说:“王娘现在还打什么工?!亏得老爷废了禁令,我买了这一间两层的门面,先是卖茶,茶又不赚钱的,便兼着又卖饭又洗浆衣服了。活路多是多,店是收拾不过来,地方肮脏辱没老爷哩!”
天鉴倒高兴起来,遂问这门面房买价多少,下河人能这样办饭店客栈的有多少。王娘一一作答,从街东头到西头,说了店的字号也说了店家名姓,连谁家有一只狗三只鸡,鸡公鸡母,都清清楚楚。突然叫道:“只图说话,馒头也忘取了,老爷在衙里吃人参燕窝,倒要尝尝百姓家的馒头,换个口味吗?”
天鉴说:“不是我吃,给他吃。”
待吃者给王娘嗤嗤啦啦笑。
王娘疑惑了:“这二流子给下河人好丢了脸面!前几日在这里白吃了一天,我让他没事干了,进山砍柴来卖,他砍是砍了,卖也是卖了。几个钱在身上就要喝酒,喝得半死不活趴在门外台阶上醉卧一晚一早,还是我用擀杖打醒来的。”说着就扯那人裤子,一扯露出一个透肉的破洞,“瞧瞧,有那一串钱置一条裤子也够了,可他只是灌黄汤,灌不死!这馒头还给他吃?”
天鉴说:“让他吃吧,吃死了拉倒,吃不死我让他去砍柴,一天一趟,攒了钱买田置房安顿个家业,若我再在城里碰着喝酒抢人,我就把他下到牢里去死!”
待吃者浑身哆嗦起来,王娘按了他的头说:“还不谢老爷!”头在地上响了三下,王娘将五个馒头全塞给他了。王娘说:“老爷既然不吃饭,喝口淡茶吧。”便拿手巾拂桌面,返身进内双手捧一碗酽茶过来,天鉴接过茶碗,却看见窗外一只小小的飞虫落在了女人发髻的梳子上。女人刚才是乌云扑散,什么时候却又盘在头顶,插着了一把绿色的木梳呢?
天鉴品一口茶,味道自好。看女人时,那梳子上的飞虫翅已闭合,是小小的瓢虫,一个红色的上有七粒黑点的半圆硬壳。天鉴觉得这飞虫落的是地方,发上不落,衣上不落,偏在木梳上,装扮的是绿叶上的一朵妖妖的花了。
这么思想,一时心旌摇荡,似觉迷迷糊糊如在梦境。天鉴的经验里,倒是见过些女人,有丑的也有美的,但这般明艳女人还是第一回。王娘是什么原因而有了这明艳的感觉呢?偏这时,瓢虫又起飞了,小翅闪得极快,在空中盘旋了三个圈子如一个幻影,竟最后站在天鉴的鼻尖上了。一时间天鉴通身酥麻,他想伸出舌头舔了它来,但没有动,王娘却格格格地甜笑了。
这一笑,天鉴的感觉里,后偏门的人和前门口的人却无声地微笑了,猛然冷静,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就掩饰窘态地咳嗽一声。那瓢虫竟抖掉进了茶碗,忙用手去救,瓢虫已烫死了。
天鉴暗暗叹息了。王娘重换了茶碗,天鉴没有喝下去,看着已吃下三个馒头的那汉子,问这是哪里茶?
王娘说:“下河人在芦子沟垴植的茶,并没什么名声的。”
天鉴说:“喝起来好。”
王娘说:“老爷不嫌弃,就常来喝喝。”
天鉴笑笑,说五个馒头的账你记在水牌子上吧,随后来衙里讨钱是了,起身要走。王娘说:“五个馒头钱值得向老爷讨?说老爷常来,那是一句话,小店哪有福分老能承接老爷呢?你今日来了,只企望老爷能补补我门口的对联吧,王娘咬不了字,画碗圈替字了。”
天鉴虽识得一些字,提笔书写却是不行,说:“画碗圈好呀,开饭店就是用碗的地方,只要来竺阳的下河人都有一碗饭吃,我这知县就不枉当了!”
王娘就朝偏门口喊道:“五升,高运,三柱子,听见老爷的话了吗?老爷会让你们有饭吃的,还不出来见见老爷!”偏门口探头探脑的人一听招呼,头却一下子缩了回去。但立即更多人挤在那里,有三四人前脚已踏出门栏,后边的一推,脚又收回去。
天鉴问:“这是住店的吗?”
王娘说:“我哪里有了客房?都是些没事干的下河人,没处去,腾了这后院让他们夜里存个身,白天就出去混口。这几个是要饭都要不来的,躲在这里发迷瞪哩!进来呀,进来,老爷是官又不是老虎,怕吃了你们?饿肚子不寻父母官,我可没多余一口饭再养你们了!”
还是没人敢出来,天鉴便走到偏门口,站在后檐根下的人就全跪下来磕头。天鉴没有说话,转身到柜台前卸下水牌,用笔写了:“知县,四十个馒头。”说:“王娘,七个人三十五个馒头够吗?四十个馒头钱你一定到衙里来取!这样的人别处还有吗?”王娘说:“多哩。”天鉴说:“你要了解,你寻个人把这样的人名字、年龄列个单儿来县衙给我,总得要想法都活下去。”
王娘锐声说:“行得行得,人都说老爷是支厅的盐包老爷,果然盐青天!”就送天鉴到街上,天鉴并不回头也不回应,一脸正经骑了驴子就走。
走了,还听见王娘在和人说话。
“这就是知县老爷?老爷到你店里了?”
“你是说这老爷是假的?”
“王娘你刀子嘴!老爷到你店里了,你怎不让我见见?”
“你要给老爷磕头吗?老爷刚才在这条椅子上坐的,你先给椅子磕个头吧!”
“我向老爷告状呀,我家的三只鸡都被偷了,还不是你们那些下河人干的!”
“别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下河人屙的!哪面坡上没有弯弯树?昨日逢集,我从十字街口人窝里过,人挤人地迈不开脚,我觉得有只手在我心口处揣。我以为哪个骚小伙在拾我便宜,想,小伙家没见过,揣就揣去吧,寡妇家又不是黄花闺女!可挤出人窝去买熏肉的香料,一掏怀里钱袋,没有了,狗日的人家不是在揣心口,贼,是偷了我的钱袋哩!”
天鉴统计了大约六百余名的流浪下河人,就正式发了修建平川道水渠的布告。不出所料,平川道的许多人家缺乏劳力愿意割地雇人,天鉴便亲自走村过寨,强令得到割地的下河人就地落籍,然后统一组织分段修渠。各段由各村社推举渠长,全渠总负责人为渠督,择了吉日,天鉴在衙门口摆了酒桌,亲自为渠督敬酒。渠督原是衙里的一名粮长,当下激奋,立了军令状:三个月渠修不通以脑袋抵押。天鉴说:要修通了,我赏银三百两,为你竖一块碑子。这粮长到了工地,人虽善良卖力,但乏于威严。刁野浪荡惯了的下河人因粮食不足,偷工减料,三个月后,渠里修通,而一通水则一半渠堤塌陷。天鉴得到消息,传令粮长来见,粮长是来了,却是一颗血淋淋的脑袋装在口袋里着人提来。天鉴见不得血脑袋,想起西流河畔的兄弟,于是放声大哭。巡检抱怨用人不当,下河人刁野,能震住的只能是巡检署的人。便让县西峰镇的一名心腹头目出任渠督。又是三个月,北渠还是没有修通,且修渠民工三分之一的人拉痢疾。一调查,各村庄筹集起来的银款被渠督贪污十分之三,且将所拨的麦子全倒换了玉米,还有一部分已经霉变。天鉴勃然大怒,断了渠督死罪,仍不解恨,着令将皮剥了,蒙鼓挂在城门口示众。人鼓挂在那里,刮了七天七夜风,起风鼓就响,满城公干和百姓都害怕了,说知县平日文文斯斯,下手竟如此狠毒。渠还是要修的,谁来劝说,天鉴就骂,但没人敢再出任渠督,张榜招贤,也是无人来揭。
天鉴也就浮躁了,夜里睡在床上,似睡非睡,眼前总是出现白的光团,又看见白毛狼的眼睛了。燃灯坐起,四堵黑墙惟一一扇窗口,用被单蒙了窗口又睡,还是在梦中见到静卧的白狼。天鉴想,是我做得太狠了,还是这渠本不该修?不修渠竺阳怎么富?下河人如何生活?知县的政绩还有什么?天鉴做得是狠了些,天鉴要不做县令,巡检也一刀砍了,荐举的什么货色,这不是成心坏我的事吗?天鉴如此想着,就每日夜半起来,可一穿上官服,浑身就发痒,这痒越来越厉害;脱了官服看时,褶缝里果然竟有许多虱子。天鉴就奇怪了,当年在山林吃的什么,睡的什么,一件不得换洗的蓝衫也不见生虱子。如今经常在瓮里沐浴热汤,穿了华美的官服倒生虱子?!天鉴就着人常洗官服,但只要一穿在身上就奇痒起来了。这一日又喊跛腿的衙役拿了官服去洗,跛腿的衙役说:“这才怪了,老爷的便服上怎不生虱子?莫非虱子也要沾老爷的官气?”天鉴笑了说:“它是要吸老爷的血哩!”衙役说:“老爷,王娘店里也承接洗衣的,她是用苦楝木籽汤泡过,又用米汤浆的,那法子或许就灭了虱子,怎不把官服交她洗一洗试试?”天鉴说:“那好,我让她来衙里取四十个馒头的钱款,她倒一直没来,你捎了钱去,把这官服也让她洗了。”衙役去后,第二日送来官服,洗浆得十分整洁,天鉴十天里不觉发痒。但十天后虱子又生了出来,衙役就让王娘定期来自取官服。
又是一日,天已转冷,天鉴在堂上断了一桩讼案,又与县丞议了一阵无人揭榜的事,就闷闷不乐回到后院卧房,才点了灯,生了一盆旺炭来烤,跛腿衙役进来说王娘来送官服了。天鉴说人呢?衙役说在门外边。天鉴低头瞧见门帘下露了一点红的鞋尖,立即正襟危坐,对衙役说:“让她进来。”王娘进来了,拿了一脸平静,给老爷请安。天鉴让坐。落坐椅上,腿合交一起,眼就瞥了四壁,耳里逮住了一声嘤嘤清音,知道蛐蛐就在椅后墙角,没有跺脚,也口里不弄声响来。衙役说:“王娘还会拘束呀?”王娘说:“老伯去化觉寺烧香敢指手画脚吗?”衙役就笑笑,退出去了。衙役一走,天鉴和王娘都更不自在,王娘又听见嘤嘤清音,说:“衙里还有蛐蛐?”天鉴说:“衙里有蛐蚰。”说罢觉得好笑,就笑了。王娘很窘的,起身到灯檠前拔了头钗把灯捻拨亮来,说:“天晚了来,老爷不怪罪王娘吧?白日吃饭喝茶的人多,王娘抽不脱手脚,寻思明日送来,又担心明日老爷或许坐堂。”天鉴说:“劳动王娘了!”便将王娘进来时提着的竹笼盖揭了,取了折叠整齐、浆得硬平的官衣,又看见了竹笼底放有一包茶叶。天鉴说:“还带茶了吗?”王娘说:“随便捎一包的。”天鉴说:“那好,送了我就是我的,我也沏一壶茶待客王娘了!”天鉴取了壶喊衙役灌水,王娘说她去,天鉴不允,还是跑来的衙役接了壶,王娘就叮咛一定去井里取活水。取水在火盆上煮,王娘要招呼水壶,就移椅坐近火盆了。两人又没了话。王娘偶尔一举头,瞧见天鉴看她,脸上现一个无声的笑。天鉴以前见过王娘大笑,格格嘿嘿地摇荡人,但还没见过王娘这般无声地笑。她颧骨不高而大,脸丰满如盘,无声笑时嘴角便有微微细痕显出颧部,略小点的眼睛搭配着,是一副佛样的慈眉善眼。天鉴说:“王娘是用苦楝木籽汤浆的官服吗?穿着十天不痒的。”说过了,脸红起来,想王娘洗涤时一定发现官服里的褶缝有虱子了。王娘说:“是用苦楝木籽汤,虱子一闻到那味就死了。”天鉴脸更烧,用手去揭壶盖看水开了没,水还在响,响水不开。王娘忙去调火,不想壶竟灼了,水倾在火炭上,“噗”地腾一片水汽和灰。天鉴说没事没事,身子一扬,一只脚退了鞋屈踏在床沿上,脸上很硬地笑笑,说:“官服上倒生虱子,王娘觉得知县不像个知县了吧?”王娘说:“怎么不是个知县了呢?”天鉴嘲讽地说:“坐在衙堂上的才是知县,而官服里却有虱子,现在不穿官服了,这个样子坐在床沿,王娘眼里见着的就不是知县了。”王娘说:“那知县眼里看见王娘不叩头下跪,又弄倒了水,迷了老爷一脸灰,也就不是百姓了吧。”天鉴就笑起,王娘看见天鉴笑,自己也笑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