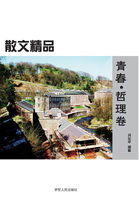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行了,狗婆娘,真想缝住你那讨人厌的嘴,敲烂那嘴里的伶牙俐齿!我这就下来!”我的朋友,请你千万别以为我们的梵能有如此大的勇气说出这样的话。那些话都是我说的,只是自言自语罢了!不过,请别嘲笑我,我们的梵连自言自语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为了捍卫自己卑微的形象在羞辱他的女人面前显露出男子气概了!听听他怎么应答吧!“麻烦您啦,我马上下来。”这苍白无力的声音,怎么听都不像是一只雄性狮子发出的怒吼,倒像从一只马戏团里的狮子口中传出!这倒霉的人那时正在脱自己湿透的裤子,听到了咒骂,他就急匆匆地拉起已经掉至脚边的裤子,胡乱束上了皮带,冲下楼去。下去时,他甚至连门都没带上。我想这应该算作一个地地道道不修边幅的单身汉模样,也只有爱情和婚姻的旁敲侧击才能解救这可悲的人,可是,说实在的,每当我们祈求老天赐福,为我们降下一段美好姻缘的时候,我们的恋人却总是迟迟不肯露面。而当我们苦于等待,发觉自己所爱的另有其人时,上帝又会收回成命。自此,我们眼看就要实现的新生活又成为了泡影,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啊!于是,趁着梵下去的空当,我从黑暗钻入了光明。还好,我的肢体还懂得如何在阳光下呼吸。面对黑暗,我还不至于像一只患上禽流感的公鸡,满脑子都是任人宰割的场景。当我站在光线汇聚的窗玻璃下,发现那七零八落的邋遢场面已将我三面包围,我的天!桌面上,脏衣服覆盖在书本上,使得书香和体臭交流着各自的遭遇;被弃置在床沿的玻璃勺柄,插在了一个圆筒形的糖果盒中,充满喜悦地交媾着;还有一只开了叉的拖鞋孤零零地挂在热水壶的壶口上,就像一艘刚刚经历了风暴的船上悬挂着的破烂不堪的帆。还有那些疏于打理、落满灰尘的海报,求职杂志、报刊,在夹缝中甚至还幸存了一张有关慈善捐赠活动的宣传单,从它那满是褶皱的表面上可以看出梵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中而缺乏爱心。够啦!这哪像一个家啊!这倒更像一个巢穴,一个聚集着世界上所有肮脏与无序的集合。刚刚消失的怜悯又从我心中悄悄掠过,与此同时,我也从对梵的刻薄转向对他的慈悲。可是,我此时的情感却异常复杂。比如说,除此之外,我还对他的生活感到了深深的悲哀,怎么说呢?我之所以对他存在这种情绪,倒并不是因为,梵那乱成一锅粥的室内和他那不修边幅的坏习惯。而是——可以说大概有七成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面临烦恼和羞辱时的怯懦与顺从。就好像他始终安于现状,而且将错就错。我想:在这样一个杂乱无章的室内寻找藏身之处将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我不需要强迫自己躲在一处自己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太多地方供我选择,以至于将我弄得头昏眼花。还好,我并不挑剔,钻入了衣服、被单堆背后的一扇壁橱门里。稍稍拨开眼前的衣服,我就可以从壁橱的缝隙中看到主人公的私密生活!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吧,梵才心事重重地走入我的视线。这二十分钟,我都想些什么呢?我的思想自然会提及我对梵的印象,我曾清楚地记得,我在信中幻想出他的模样。也不一定单单只是借助想象力吧,同时,我还借助他包含于我脑海中的那部分记忆用以依稀判断他的容貌,不过,我的逻辑未免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忽略了变化的细枝末节,以致使我的设想并非无懈可击。还记得,我称他是纯洁的化身,被遗弃在一堆破铜烂铁之中,赋予着拯救无序的责任!但,实际上,现在的他却失去了纯情,变得复杂忧郁,他没有拯救无序,反而正在沦为无序的一部分。或者对于无序混乱,他只是视而不见,独守自己那几乎只有拳头大的精神空间。
谈到他的精神空间!上帝,它空虚且极重。我猜想,夜深人静之时,为了替自己的空虚找到休憩之床,为了把臃肿的负担暂时遗忘,他可能还会同街边游荡的淫妇假情假意地寻求肉欲。不过,那脆弱的床也许难以承重,也许他们根本不需要床,就地解决!随后,我认定了对于梵的情感,我相信,不久以后,我会像喜欢噩梦一样迷恋一个自己了如指掌的人,我深知自己心中会注满对他的崇拜——这个被我占据着一部分过去和隐私的可怜男人——请先不要这么先入为主的妄下定论。
我们往往以现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一个我们认为非常成功的人,可殊不知若干年后我们将会被更多人(包括我们先前崇拜过的人)崇拜,其中除了情感的狂热付出和释放无法弥补之外,我们会发现崇拜只是一场简单的弹珠游戏而已,永远是那样的得不偿失、耗费精力。那么,从现在开始,我需要努力保持一个独立人格,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无数个重合,可是我们的观点却应该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请问,我又是如何站在他之外如此客观地审时度势呢?
除此之外,在这二十分钟内,我还想到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比如说有关自己记忆的事,还有对于这个城市的印象等等。最后,在考虑到如何索要我的记忆时,我自言自语:“应该像个聪明人那样,耍耍手段!”
正当我将注意力转移到运用何种“手段”上来时,他的现身使我的思考戛然而止。好在我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马上警惕异常,仿佛在夜间听见了陌生的脚步似的。回到屋内,梵开始了他刚刚半途而废的事业——脱裤子能算成是一项事业吗?当然,我亲爱的朋友,这倒不是因为裤子里面藏着的东西,而是由于羞耻心。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脱裤子前都应该确保自己处于一个绝对隐形的状态(除了情侣之间以外),由此,他们正如梵一样,需要耐心地寻找一个合适的场所,然后,出其不意地脱下内裤,换上一条新的!——可是,非常抱歉,自以为无人知晓的梵,却始终在我的视野中,而我的视野又始终捕捉那一处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敏感地带。我的天,一丝不挂的梵被我有幸识见,但是,千万别把我同那些娼妓们相提并论!因为,我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梵,擦完身子、换完衣服,感觉焕然一新,他开始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回想着什么。如果他有烟瘾的话,我想,此时污浊的室内会因为烟雾缭绕而变得乌烟瘴气!他缄默地躺在那儿,安分得像只树獭。他的脑海里都回荡着些什么呢?聪明人当然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梵的头脑里,满满当当地装着我对他说过的话,以及我可能具备的身份。还有房东太太突然发作的性情以及她可当真也可当作是一时兴起所下定的搬家期限。或者,他还想着刚才电话里的一些事情,虽然,我现在对于电话里的谈话内容还不得而知。不过,简而言之,他是彻彻底底地把自我放逐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荆棘丛中,他的肉体被毒刺缠绕,已经完全失去了脱身的可能!
我开始觉得单调乏味了,随即,我感到疲惫困乏。你知道,如果人希望好好睡上一觉,他是极其厌烦任何约束的。由此,这狭小的空间又令我焦躁、局促不安。虽然我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我说蓝,既然选择去做有违道德的活计,你当然得付出代价!”或者“这可不是你们家的阳台,你得将就将就,谁叫你自寻烦恼的呢?”但是,我却不能戒骄戒躁,真希望舞台上能发生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以便分散我的注意力!
半晌,梵坐了起来,他迟缓的动作告诉我他并没有灵机一动,或者兴冲冲地想要干某件事。他翻下床,光着脚走向写字台。他打开了台灯,室内顿时镀上了一层蜡黄。梵小心翼翼地打开抽屉,翻出一本笔记簿,准备记录些什么。他摆着一副漫画家的严肃姿态——漫画家的作品,似乎不是严肃和理性的结晶,相反它们好像是随性把玩的结果,仔细地勾勒中隐藏着奇妙的幽默——梵,进入了记录状态。虽然,我的角度不能允许我窥探他的全貌,但这也足够让我把握他的面部变化。首先,他好像遇到了什么磕磕绊绊,像个小学生一样愁眉不展,同文字较上了劲儿;然后,他似乎享受到瞬间的灵感喷发,得以文思泉涌、奋笔疾书;接着,他的叙事又因为某种原因而停滞不前了,不过,此时的他不再像先前那样光顾着盘算文词句读,而是更进一步,仿佛正在同思想较真儿,与故事本身发生冲撞!其间,梵的眉毛还时常略微翘起,它们时聚时散,神似一只扑腾翅膀的大雁。最后,他丢下了笔,把脖子倚在了靠背上,猛伸了一个懒腰。我也多么希望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肢体尽情的舒展一番。可是,我又不愿舍弃因自我囚禁而带来的五彩斑斓的乐趣!梵的笔在本子上到底留下什么内容,日记还是随笔?或者根本就是些有关烦恼的闲言碎语,或者他及时地记录下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信息。难道,他在回忆过去,以便还给我那些丢失的东西?我的心不禁激动起来,如若他真是在为我而付出努力,我将不自觉地充满感激,我的兄弟,他确实是一个守信用的好人!不过,另一种可能是,他早把我的事给忘了。说实话,我更相信后者!
正当我满目狐疑、胡乱猜测的时候,灯熄灭了。梵在笔记簿上撕下了一张纸,匆忙出门了!我的天,这混蛋竟把我反锁在屋内,我真想说:“你这蠢货,屋里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