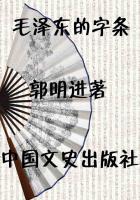我的父亲因为经营私人煤窑,成为一个大亨。他非常喜欢生活的广告词:苦难,应该由那些注定现世悲惨的人去承受,我们积累财富,靠的是他们的卖力劳作。他的煤窑设立在一座四面被乱石岗和黑色的尘埃围着的光秃秃的山脚下。在我的记忆中,山脚下的那一个深深的洞穴就像一张饥不择食的大嘴,从里面不断地吐出一车车的黑色煤炭,当这些车顺着两条寒光闪闪的轨道原路返回的时候,我真有一种想跳入空的车皮,钻入巨大的口里看个究竟的冲动。可是,我没法满足自己的愿望,向父亲提出的类似要求,都被他简单地回绝了。我只能坐在一个空地上,一个看不见父亲的地方摊开手上的书,等待那些从煤窑里走出来的“幸存者”们(小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们是虎口脱险的幸存者)的身影。他们不会轻而易举的现身,每天,他们都会规律性地出现两次,一次是在中午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傍晚。这些浑身脏兮兮的人穿着破烂,满脸倦容。他们在出来的时候大多互不言语,相互间只用眼神来传递思想。就像是被时光机器从另一个世界传送过来的邮差,他们似乎完全与这个世界失去了某种在我们看来相当正常的对称。我始终不敢接近他们,我怕打搅他们因为服从疲倦而遵循的某种特殊的井然有序。因此,我只能从原地站起来,装作是在活动手脚,而害怕同他们的目光有任何长时间的接触。煤窑周围是一堆堆的煤,它们将红砖瓦房衬托得异常艳丽,也就是在这些红砖瓦房边,倦怠、满脸漆黑的“幸存者”们得以蹲在一旁,享受一下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空气。他们摘掉了头上安装了电筒的安全帽,两手交叉,搭在膝盖上。此时,这些沉默不语的人会进行短暂的交流,不过这些交流仅仅只发生在,例如抽烟时找旁边人借火这样实用性强的情境之中。从他们一直到再度进入煤窑之前,都显得僵硬的面部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或者没有幽默感,或者根本是陷入到自己的生存状态里,也许他们就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鸫一样,多数时候只以沉默交流。
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类似父亲煤窑的场景:凌乱的布局、破败的厂房以及随意可见的煤渣。我似乎特别喜欢联想,我情不自禁的将这一幅幅画拼接起来,组成一幅类似于父亲煤窑的活动的生活场景,并将那些文字还原成为一些视觉效果极强的图像符号。此后,我会轻易地走入自己联想的一组关于煤窑的生活里,然后从想象之中狂妄地生出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你知道,当你发现在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生活却于你近在咫尺的时候,你就越发想将这种生活看个透,把一切发现占为己有。我具备这种天赋,因为我占有这种生活。
随后,我成为了父亲身边的一个窥视者,我时刻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偷看他摆在办公室的物件,父亲放在书柜间的排污许可证、像模像样的陈列在橱窗里的,市里颁发的荣誉单位证书以及若干年后即将变成通缉令的营业许可证。而父亲的办公桌也经常空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认为,他钻入了那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然而,若干年以后,当我听着叔父在一次酒醉后的胡言乱语时,才知道,父亲的工作实际上是周旋在一场又一场奢华的宴请上的。
于是,这令我想到了十几年前的一幕,那时,我被母亲带着参加了一个宴席,这场宴席别开生面地发生在父亲新购置的庄园的西餐厅中,虽然,我并不情愿随着他们进入一个满是陌生人和烟酒的世界,可是,冲着晚宴上的美食,我还是穿着一套绅士服参与了进来。那天晚上,似乎整个地区的政治要人、巨贾富商都集中到了一处,可是屋里的空间却不显狭窄。晚宴上不乏作秀的场景,人们弓着腰,互相寒暄着,眼睛中却放射出一种试探和怀疑的神情。他们开着并没有什么新意的玩笑,谈论着属于上流社会的公共话题,但是,这一切都显得极其不自然,就像一些曾经共事、事隔多年后再度邂逅的朋友们,一时找不到话题。
整场晚宴拥有着自己的节奏,听起来非常像一曲由恩里克·格拉纳多斯演奏的慢板华尔兹。分布于10张桌子上的人们,享用着一道又一道可口的饭菜,谈论声、刀叉的撞击声此起彼伏。我和父亲、母亲所坐的那张桌子上的客人们,无疑是经过父亲深思熟虑后的贵宾中的贵宾。他们表现出了对于父亲异常的尊敬,当然,这是出于这场宴会的缘故。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将思考聚集在这次宴会中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场宴会只是一个外壳,是为父亲接下来的行动所作的庞大的投资。当上到最后一道菜的时候,灯光渐渐黯淡了下来。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配合着灯光成为了主调。餐桌上的人开始接二连三的离座,宽阔的大厅瞬间成了华丽的舞厅,优雅的舞步随之迈开,就像水中的卵石一样富有韵律和呼吸。父亲没有去跳舞,并不是因为母亲被一个瘦高的绅士邀请共舞使他失去了舞伴的最佳人选,而是因为他在同一位先生谈论着什么,他并不在意我在他的身边,可是,我却仍然能够从他们的谈话中捕捉到一两个我刚刚在学校语文课上学过的词汇,比如说,他们似乎经常提到矿上、安全、照应、查封、利润什么的,也就是这些频频出现的词汇,在不久以后的将来,成为了我揣摩这一天的对话内容的有力线索。透过这些频频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词组,我会认为不久以后产生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好了一样,就像这样的生词最初为我熟悉一样,它们也似乎将注定成为我生命中的深深遗憾。
宴会后不久,父亲的煤窑就发生了坍塌,那天下午,矿场的地面发生了强烈的震动,黑暗的洞口塌了一半。我顺着第二天的报纸往下读着:矿井中无人幸存,他们基本上都是窒息而死,有几个矿工被塌下的泥砖砸中了头部,失血过多而死……我看到了一些被亲属允许公开的矿工的照片,他们出现在文字的旁边,多半都绷紧着脸,正如同我曾经在煤窑看到的情景。我想:他们之所以始终僵硬着面容,是因为他们无法占卜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他们签订了一份“卖身契”。是因为那些年轻的矿工永远同象征死亡的黑,打着交道——他们处在远离光明世界的黑暗洞穴中,挖掘着黑色的煤矿,然后带着黑暗的心灵去承受疲倦与诅咒。请听我说,当一切美好的希望以黑暗作为底色的时候,每一个拥有希望的人都在劫难逃!
当然,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可是,他竟然先一步找到了退路,应该说,他早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意外而为自己随后的着落安排停当了。他在那次宴请后,就将我交给了叔父,然后同母亲去了国外,当初,在母亲含泪告诉我她很快会回来、去国外只是为了养病这些事情以后,我并没有像离不开家的婴儿一样,疯狂地痛哭流涕。因为我相信: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故事埋好的伏笔……
黑和那些矿工的希望被埋在了更加幽深的黑暗中。几天后,也是在报纸上,我看到了那次宴会上同我父亲进行密谈的中年人被警方拘捕时的狼狈样子,报纸的标题,让我在多年后仍旧记忆犹新:贪市长作茧自缚,请法庭再做申辩。
意料之中,父亲的煤窑被查封了,可是很长时间那里都保持着原样,应该是政府为了纪念或者警示什么而刻意搁置在那的。要不就是,没有地产投资商愿意在那个晦气的地方(按照当时的一种说法),进行任何产业的投资。不过,事发后的第三年,这里被政府建立成为一个国营的煤矿生产基地,至今都没有再度发生矿难……
事情好像告一段落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在西半球的某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安全的避难所。可是,我总有一种掀开过去的冲动,这不是反叛我的父亲,反叛我的家庭,而是在激烈地反叛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那些“幸存者”们,是否拥有再度生存的信心和能力。同时,我还一直深深地坚信,在某个正午,他们仍会从黑暗的洞口无精打采地,几乎是爬着出来,好像刚刚经历了命运的挣扎一般。或许,当我曾经看到这一幕时,他们早已经死了……
现在,我痛恨父亲,我需要在无可对证的时候证明他的罪行!因此,我有必要将自己的发现转告给我亲爱的读者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正是那次宴会上,我父亲和市长阁下的亲密对话:
“您玩得尽兴吗?”
“这可真是一次盛大的宴会啊,非常感谢您能邀请我参与进来,确实,晚会内容很丰富,特别是这些地道的西餐,真是太可口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矿上的那么多事也多亏了您的照应。您看现在矿难频发,国家开始摊派技术人员和纪检部门的官员进入我们这些煤矿生产地区抽查,像我所办的这样的小型煤窑,万一成为他们抽查的目标,会不会有查封的风险哪?您说,我一个老实人,只希望我的生意能够保持现在的状况就足够了,儿子也还小……”
“您上个季度获得的利润是多少?因为那些钦差大臣们只会关注利润高的大中型煤窑,或者,他们会根据媒体的新闻调查和民众的举报去核实审查一些像你这样运作的私人煤窑。”
“上一季度每吨煤的利润大约在100元左右,可是您知道,因为省去了办证费用(这多亏了您),节约了成本,利润应该是每吨200元。乘上交易额,总共应该是1500万吧。”
“……数额还是有些大的……这样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应该避避风头,停工几天。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他们这次是冲着安全问题来的,煤窑坍塌接二连三地发生,暂时歇业我想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我会帮他们确定一条线路,然后把他们带到同你的煤窑反方向的西区矿厂,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抽查到您的煤窑了。媒体这一边,我会跟商业报主编说的,您看,他在和您妻子跳舞呢!请您相信我。”
“真是太感谢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一定会重重答谢您的!”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是老相识了,呵呵……哦,对了,您矿上的安全状况怎么样?我是说,一定要保证矿上的安全,您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否则,到时,我们可是会被……”
“这次就要请您放心了,我们已经发现了煤窑技术设施老化,管道有裂痕这些亟待解决的隐患,现在正好可以利用歇业的几天请地区技术人员过来更新一下。请放心,这一点,我比对任何细节都在意!”
“这就对了,一定要保障矿工的人生安全,还真是件麻烦事啊……”
请告诉我,那黑色的口中到底藏着什么?
迷失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当时的美国青年对于美国战后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时迫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因而取道极端的反叛。他们以“脱俗”的方式表示对于政府的抗议(诸如厌弃学业和工作,穿着奇装异服,蔑视传统文化)。这似乎成为一场对于政治的讥讽,青年作为政策的直接受用者应该承担更多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可是,在他们看来政治好像成为了某种令人生厌的玩物,于是,他们希望落空的政治心态转而成为了一种对抗政治、逃脱生活束缚的伺机。最终,凝聚成这个国家特殊阶段的时代背景!
我们的这个时代,政治不再甚嚣尘上。相反,它已经开始逐渐趋于缓和。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不需要因为受到政治的限定而穿着统一的服装、喊出某些夸张的口号了;我们不需要隐藏自己的资产阶级子女身份,同一个工人家庭的心上人谈婚论嫁;我们也不需要在挂满政治标语的街道上去聆听某些狂热分子激情澎湃的演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呆在自己的屋里不去理会外界政治的鼓噪;我们可以无心过问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只把目光投射在有关教育部的改革措施上;我们可以在饭桌上同家人朋友们谈论政治,运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去抒发对于某项决策的不满或者鞭辟入里地针砭时弊。
然而,我们之中很多人并不在意政治,并且彻彻底底地试图忘记政治的存在。上一代人因为经历过政治的洗礼,而不愿意让我们这一代承受曾经被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比他们幸福,代替他们去实现所没能实现的目标,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以经济和文化而不是政治为主旋律的时代舞台中,展现个性的美。这成为了一种潜移默化的灌注,他们用失衡的爱和焦虑的企盼为我们迷失的价值观,悉心输液。当然,我们在输液时本身就化身为病人的形象。
由此,我们更加在乎自己,把享受的美当成装饰,故弄玄虚;我们更加脆弱,把忍受的轻微阵痛当作是生活的致命一击所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更可怕的是,我们崇尚理想,崇尚那些缺少信仰的走秀、矫揉造作的失态。我们将那些把自己定位在娱乐时尚海报上的文化统领者捧在温暖的手心,小心地保留在自己的梦境中……
记得有一阵子,我是那么一个充满理想,同时又缺少耐心的热血少年。我热爱生活的每一页。那个时候我却同时关注政治。每当课余闲谈的时候,我都拥有着与众不同的政治主见,我喜欢西奥多·罗斯福,并经常在众人面前提及自己最新占有的国际政治新闻。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军开战的时候,我就曾用一个身临其境的战地记者口吻,鼓噪着双方的实力对比和目前所达到的伤亡数字。多数情况下,同学们的兴趣会被点燃,他们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关乎政局的资料从脑子里掏出,然后互相交换自己的道听途说,再把那些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丑闻假说占为己有。我们就这样一次次谈论,没有因为话题的过于成熟而忘记我们的真实年龄。几年以后,当这些话题之于我不再遥远,也应该是我们拥有新见解的时候,探讨的声音却戛然而止。
丑闻对我们而言不再拥有吸引力。我们开始发掘谈论娱乐信息,谈论难以获悉的小道消息。如同一个开启全新生活的密探,我们传染着彼此有关生活的新认知。在忘记原先主题的同时,我们渐渐忽略自己有关旧世界的领悟。我们已经将双脚踏入一个更加具有魅力的领域之中。那里没有政治的硝烟、国会席间由各抒己见而爆发的唇枪舌剑、被政治黑手在幕后操控的谋杀和恐吓、皮影戏一般教人无可奈何的派别冲突,没有恐怖组织的秘密特训、反对党的游行示威、政治领袖在临对失业和通货膨胀时的举重若轻、种族灭绝、军警朝宗教狂热分子投掷催泪弹时的耀武扬威、通过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军人政权、以及前总理的流亡,没有军备竞赛、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同裁军相关的一系列军事措施、反政府武装同正规军的针锋相对、信息战带来的尔虞我诈、留存于人民口中的关于某个民族英雄的传说……然而,我们的新领域中却充满着明星的璀璨光环,我们崇拜网络里一炮打响的新个体,我们热衷于担当商业社会的炮灰、棋子,在一个喧嚣四溢的烟尘时代中,淡忘自己的自尊和个性。我们就这样不断地寻求新的商业热点、在退出“政治舞台”的同时,因祸得福,却又患得患失……
这是新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因为颠覆了生活的本源,最终成为一个十足的出局者。如果说政治的局促制造了“垮掉的一代”,那么我们这一代青年们,遗忘政治、让商业成为精神领袖,不断盲从的幻想,又将制造何种苦痛的生命群体?海明威冠名过“垮掉的一代”,称他们是“迷茫的一代”。而今,我并不认为同我一起经历遗忘的一代人是再版的“垮掉的一代”,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