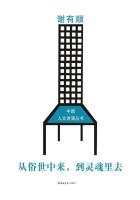我甚至相信(或者让自己相信),我们的人生似乎仅仅经过了时间的过滤,相信每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同时发生。
什么你都不准忘。
——菲利普·罗斯《遗产》
生活一旦贴上了工作的标签就会变得中规中矩。近一周以来,我的接线业务十分繁忙,以致使我缺少了原本的安逸。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我似乎重新找到了某些我原本缺少的元素——我的热情、我的严谨以及我的期盼!我希望这份工作能够替我的生活带来曙光,能够让我有资格成为一名拥有独立公寓的现代青年,而不至于像这样两手空空地寄人篱下。还好,一切迹象似乎表明,凭借我现在的发展和心态,我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话虽这么说没错,可是我的困惑却始终伴随着我。那就是,接受这份工作一周以来,我几乎随时都处于待机状态,任何时候我都必须留守在自己的手机旁,因为客户可能随时都会打通我的电话,他们可能在我刮胡子的时候,让我挂着一脸泡沫,像个圣诞老人一样听着他们的叙述;可能在我寻找某样覆盖在层层书报下的餐具时,为我好不容易理顺的思绪添上一堵毫不相干的声音;更加恼人的是,电话的铃声甚至会在夜间想起,此时,一定是某个因为从梦中惊醒而诗意大发、充满感慨的中年妇女或者是一名因为怀念昔日的玩伴而无法入眠的谢顶先生(我的猜测)打来的电话。总之,我的生活突然间被人催促着向前展开。我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一切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不过,还未在我来得及思考的时候,未知的声音和历史又如铺天盖地的沙尘,席卷而来。我没有思考的空间,就这样在督促和引诱的作用下,朝着那个可能完美的结局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不得不说,这么些天,我的耳中虽然回荡着无数的声音——一个原本应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却操持着抑郁忧伤的口音;一个失恋不久的年轻小姐希望抛弃一切烦恼时逻辑混乱、受到情感冲击而胡言乱语的声音;一个紧张兮兮说话时断断续续,好像在躲避某种监视而缺少质感的少年的嗓音;一个似乎正因缺少话题而沉默良久,又不愿就此挂断电话的倔强的声音;一个躁动焦虑、恐惧过去、却又要表示忏悔的声音;一个一度对于美好的童年时光着了魔,温情款款、如数家珍的甜美喉音;一个痛恨自己的过去,甚至滑落到荒废的情感边缘,深刻而又无能为力的嗓音,以及一个伪装好的僵硬的声音、属于蓝的声音。我的第一本笔记簿也即将被我记满。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无数生活的片断——我的记忆和客户们的记忆混在了一起,一开始我选择用目光剔除其他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仅仅只是因为业务关系而为我暂时保存)后来,我开始注意到,我的记忆正渐渐埋葬在那些占据主导的他人的记忆之中,以至于我几乎分不清哪些是我的,哪些不是。
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学习帕慕克先生那样纵容着西方人充满想象力地描绘他的故乡和记忆,把它们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我开始混淆是非,混淆自己曾经迷惘过的任何困扰,而把那些困扰拱手相让。我开始让自己成为在一次咖啡厅里发生的斗殴和枪杀的目击者,我开始渐渐相信自己曾经意外地出现在一个法庭的听证会上,亲眼目睹着父亲和母亲的唇枪舌剑,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挑战过教育制度而最终遭到休学的惩罚,我开始一遍遍地呼唤自己的身世,属于我的另一部分记忆以及我的情感旅程(我的初恋),我开始迷迷糊糊的从笔记簿上看到那个近来经常在我梦中浮现的情景:一个佝偻的背影骑着大海的浪脊渐渐远去。我迷失在属于自己和属于别人的追忆之中,我似乎成为了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倾听过去的声音、记录曾经的路程,然后在回想中提炼生活的金玉良言和怅然若失。
除了同蓝的那次意外交谈以外——后面几天,他似乎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也许他又在酝酿某项足以撬开我嘴巴的计划吧——这些天,我的思想深深地徘徊在一些美妙特殊的片断之中。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为之停滞不前的冲动,从而充满幸福的孤独与快乐的惆怅。正如我刚刚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成为了另一个我,一个由许多个不断增多的别人的片断(而且将继续增多)组成的,不知道该不该属于我的人生。那么,就请看看我这么些天所找回的那些强迫同我有关的过去吧:
迷失的愤怒
在两个伟大的时刻之间,总有一些跳梁小丑从历史的缝隙间探出头来冒充伟大。他们摇摆在两个极端间,露出异常的悲悯抑或是狡猾。随后,他们在万籁俱寂的消沉领域中摆开跳跃性的姿势,迈着滑稽的舞步引领着某一阵时代的季风掠过少男少女的眼前。盲目的跟风——我指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使更多的小丑探出身来投其所好。这使我想到了童年时一则关于魔笛的童话故事,说的是,一位游街艺人有一根魔笛,吹响它,那悠扬深远的笛声,会诱引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紧随其后、翩翩起舞。他们分不清方向,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究竟要像这样快乐地旋转多久,跳到哪去?我们无从知晓。
同时,那些真正的伟大者的光彩却被黯淡消沉的黄昏默默覆盖,他们的书卷、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的人文关怀都成为了记忆符号,我们只有从回忆之中才能发掘那些零落的孤独。那些同这个时代并不契合的伟人们,那些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崇尚纯艺术创作的思想家们,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将主导艺术和时代的权力拱手相让!
迷失的个体
在我生活的间隙,发生了许许多多我无暇顾及的事情,从过去到现在,我似乎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彻彻底底顾全大局的人。我会在某一个清晨洗漱更衣时,对一场已经发生无数次的街头争执引发的行凶杀人案漠不关心;我会在忙碌于手头的家庭作业时,忘记在市中心的公园附近有那么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存在;或者,在我与几个玩伴出没于某个居民区的窄街小巷中时,某一位并不能称作杰出但多多少少为市政工作做出贡献的行家里手也在和往常一样外出时因为心肌梗塞而死在了人行横道上,而他死时的方位距我不过三个街区。当我默默逃离事发地点的时刻,而在几个小时后得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同我擦肩而过时,我的脊背就会卷起一阵凉意。我会不自觉的将自己变成是我所错过的另一个我。我会想:倘若我出现在事发地点,是否会成为随后一场争论的介入者、一场法庭辩论的目击证人,或者,我是否会干脆成为那件事情的被害人,现在正躺在医院的急救室中接受电击的最后拯救?
好在,一切都相安无事,几小时前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其他的事情在几小时以后失去常态。我还是我,一个仅仅只是稍显焦虑地停顿了思维,为那些繁琐的俗事风波悄悄留有了狭小的空位。虽然我心中的魔鬼总会将我卷入到一件不相干的事件中,但,我却疲于应对这每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曾经在做一次访谈节目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分析他创作影片《两生花》的初衷时曾清晰地指出:“我认为我的影片就是告诫所有的人,在对待生活时,我们应该更加的谨小慎微。我指的是你在任何情况下所作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会成为铸造他人悲喜剧的某种契机,而在你身边可能发生的一切也许最初是由别人无意铸造。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生活得谨慎些!”
正如很多作家所叙述的那样,世间始终存在另一个你,一个可能同你过着相反物质生活的你,他正占有你没有得到的,而失去你所占有的东西。我想,这就是生活永远不能尽善尽美的原因。
迷失的希望
把战争当成一个话题,本身已经令我眼前浓烟滚滚了。我是梵,我不喜欢谈论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距离我太过遥远的另一层生活。可是,它今天却成为我有关记忆的片断,请容我诉说。一个和平的建设氛围让我没可能经历那些发生在矛盾深重地区的枪林弹雨,再加上,我似乎早已经错过了血雨腥风的年代。可是,我竟然发现自己的过去充满了挑起战争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扫除任何我所瞧不起的人或事的野心。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几个玩伴间率先发明了一种战略游戏,那就是被我冠名“模拟战场”的游戏。道具仅仅只是一张地图,游戏中,我们化身为替各自的君主效劳,并被提供了1万人马。而我们各自的基地要被我们圈定。随后,我们轮流确定自己的进军路线,两军遭遇时,我们以猜拳的胜负来减少各自对垒的兵力,首先占领对手基地者为胜。这样的简单游戏在我还不知道电子游戏的时候,充当了所谓十年后的电脑游戏的角色。并且让我在若干年后对于地图中的地形图标极为敏感。事隔多年,在随意翻动地图的时候,我仍会回忆起我们曾经充满自信或者犹豫不决时的纸上谈兵:“从德黑兰调动3000军队进军卡拉季、退守波士顿、我已经事先在赫尔辛基安插了军队,你上当了……”
长大后,从地图走入现实,我关注实事,尤其是在我担任秘书的那一阶段时间。我深刻的认识到偌大的世界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民族、宗教、资源、土地、水源甚至是某某主义之间永远没有一个维系安宁的契约。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充满了明争暗斗。使人们永远属于自己的立场、属于自己的国度。战争随即会被口实推波助澜。将壮丽的战场玩弄于鼓掌间的幕后政治宗教领袖们,他们都是高超的人类分析学家,他们像一名外科医生一样,将双手娴熟地在病患的全身游移,随即掏出肢体的软肋。中世纪西欧最大的煽动家乌尔巴诺二世教皇清点着自己的浩渺无穷的账目,将人民的贫困和蒙昧归咎于异教(伊斯兰教)的侵犯和圣城耶路撒冷的陷落,1095年12月26日他在法国克勒芒召开会议,利用人民的蒙昧和对于宗教的恐惧和盲从,大声疾呼: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参加远征的人可以赦免罪孽,战死疆场的人可以升入天堂。于是,持续100多年(公元1096年—1291年)先后8次的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帷幕。无论是从塞尔柱王国的侵入(反侵略),还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几度易手;无论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无功而返,还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制造的对于君士坦丁堡长达一周的野蛮洗劫,战争带给穆斯林们和基督信徒们太多的鲜血与挣扎。在血与火的兵戎相见中,黎民百姓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他们所笃信的上帝。这是东西方宗教之间一次最大规模的碰撞,战争,火星四溅,希望就想枯叶一样卷曲、融化。900多年间,战争的火焰未曾熄灭,对于那些历史,已经没有必要接受我的指名道姓了。在我正式进驻政府大楼工作的时候,也是正值以巴战争越演越烈的时候,也正是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数字与日俱增的时候。随之,火箭弹的炮轰、“飞毛腿”的还击、卡宾枪同AK-47枪膛交换着热量、美国军政首脑的满脸倦容和刻满额头的愁绪、被烈火烧焦的枣椰树以及阿拉伯式的建筑废墟、跪在路边被白色头巾盖住面颊的正在默默做着祷告的阿拉伯妇女、出现在伊拉克女作家贝图儿·凯黛丽《天空如此之近》中东西方尖锐的价值冲突、在底格里斯河岸边巡逻的美军装甲车以及异常警惕的狙击手、在巴格达市集中因为爆炸而一度混乱的人群散播的恐慌和绝望、聚集在什叶派清真寺外等候阿訇传唤的信众们以及他们写在脸上的焦虑、从逊尼派的区域内传来的不远处库尔德人的惊呼、伊拉克逐渐减少的货郎担,逐渐增多的警力、警方设置的以防爆炸车的层层路障、一望无际的黄色尘埃和古都巴格达断壁残垣、深沉的夜色下渐渐被人们熟悉的零星的交火,还有那些决议逃离又不知何去何从,站在开阔地的难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了构置悲伤和恐慌的拼图,这样的场景是我在“战争模拟”中无法看到的也是无法预估的。游戏中我们唯一留下的战争的痕迹仅仅只是被橡皮不断擦去的伤亡数字,我们可以把损失不计入账下,也根本不需要为虚构的损失承担罪责。但是,当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巴格达的浓烟下巡逻时,当一个巴格达共和国卫队士兵中枪身亡、横尸街头时,当一名美国士兵陷入了电影《锅盖头》中暴露出的,诸如在外征战导致妻子的叛离、复仇欲望的增强、期盼战争结束同时又希望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的矛盾心理、对于尸骸的恐惧、孤独时的性饥渴等情境中时。我才知道战争的伤痕是如此的刻骨铭心。
我不知道,我那热衷于战争的过去(除了“战争模拟”以外,我还喜欢翻阅战争书籍、画下我想象中战后尸横遍野的情景、有时我会写写自己有关诸如坎尼平原战役和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些看法、我甚至对摆弄枪械一度怀有极大的热情)将埋下何种人生伏笔,它又将在若干年以后怎样进一步地影响我的生活,抑或是我之前所提到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生活着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我,将会造成怎样的个体悲剧甚至是集体的悲剧……我不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童年时代就梦想成为第二个阿道夫·希特勒、第三个拿破仑·波拿巴,以至于成为第六或者七个亚历山大、恺撒。正如我无法估量世界上究竟会出现多少个还没能独立思考就“口出狂言”将要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孩子……层出不穷的假设、宣言、效忠、背叛和失败过后,我们将以何种悲悯收拾我们残破的生活,将以何种借口尽量削减战后重建工作带来的巨大开支,将何以让一个一度被奴役的悠久民族重拾他们曾经辉煌腾达时的民族自信心?我们又能如何在彼此间杀气腾腾的那双明眸中找到人性的温存和关爱,如何在反复的屠城过后不受到灵魂和上帝的谴责,又如何摆脱战争后的伤亡单和家人四处逃遁、生死未卜带来的深深遗憾?既然如此的苦痛都是在我们称作圣战或者民主独立运动带来的话,既然“捍卫人权”赋予我们草菅人命的权力的话,那么生活中的希望又在哪?
请告诉我,当一群手提枪械的少年没有出现在温暖的课堂中,而是围在一个他们敌人的尸体前,欢呼雀跃时,你看见希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