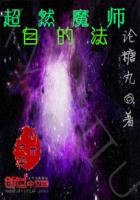最近,这里在传物价上涨的风声,还有人说省城已经买不到盐巴、大米这样的生活必须品了,说很多人都到玉水来采购。你妈迅速进了盐巴、白糖,还要毛巾、香皂什么。不过还真的卖出去了,还有人不断地来采购,你妈直后悔该多进些。应明抱回了一台18英寸的茶花牌彩电,他说还能搞到一台21英寸的金星牌彩电,你妈说买了留着他结婚时用。每天就看他们俩瞎忙,他们还买了能吃两年的大米和白糖。
家里一切都好,你专心学习就是了。应辉今年就毕业了,据去年的分配情况看,他们学校留在北京的不多,他说他想到深圳去。我和你妈的态度是由他自己决定。
三
过了一个学期,王美琴在教师宿舍分到了房子,她要应红住到她那里去,接下来二话没说就翻卷了应红的行李,收拾着应红的东西,她说,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住什么集体宿舍。
王美琴把应红领到了她的宿舍,倒还过得去,两室,为了让应红住进来,王美琴专门为应红买了一张床。王美琴让应红看房子,熟悉环境。应红转着,其实房子并不大,除了那两室外,还有一个卫生间,一间厨房,有前后两个阳台。这栋楼就在校园里,是在一个高处,背面是对了一片树林,就是盘龙江边的那一片,密密的,杂草丛生着,站在阳台上看那里,就像是一堆刚割下来的青草。前面是房子的屋顶,有平顶的,也有灰色瓦顶的,鳞次栉比地铺向远方。
她们更多的时间爱呆在后面的阳台上,看那些绿色,两把椅子,一个方凳做了茶几,泡上两杯茶。话题是无边无际的,像一片海洋。这一次,她们终于谈到了窦志强。在这之前,她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个话题,像是遗忘了,又像是在小心回避着。王美琴的手背上至今还有疤痕留着,疤痕已经和周围的皮肤组织连在了一起。
王美琴说,我早就知道结局一定是这样的。
应红想她还是那么冷漠,在对待窦志强的时候,就连他不在了,她还是这样。应红说,都怪我,那段时间我和他交流太少了,可他是需要我的。
王美琴说,自作多情。告诉你,他们家的人都不正常,这个家族恐怕有忧郁症遗传。
应红说,怎么又扯到家族了?
王美琴说,你知道窦志强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
难产。生窦志强的时候难产。
王美琴立刻打断了应红的话,错!
应红看着她,目光不解。
王美琴说,他母亲就是自杀死的。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你看看他姐姐那个母老虎样,早晚也要走这一条路。
应红说,你不要这样说他们了,窦志强也未必喜欢他们那个家,可是家并不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吗?
王美琴说,这一切都是他们窦家自作自受,当然把你作了牺牲品。
应红说,也不能这样说。窦志强是真的爱我的。还好,总是有个孩子。
王美琴说,其实最不好的就是留下了一个孩子,你想想,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上会受到很多歧视的。
应红说,不会吧,我想不会的。就是会我也会尽母亲最大的力量的。我想好了,等我毕业以后,在这里找个工作,我就把她从玉水接来,她离开了玉水,别人就不会知道她的身份了。
你如果留不下来呢?王美琴说。
不会吧,反正我会尽力的,我一定要努力。应红说。
但愿吧。你总是把什么都想得那么好。
应红笑了。
自从应红住进了王美琴的宿舍,房间里有了人气,王美琴也有兴趣到小菜场买菜了。本来就有一个小厨房,有煤气罐,在过去,王美琴从来没有用过,厨房只是她洗手的地方。当然厨具也是新买的,就好像新建立的一个家。这一切都是王美琴去操办的,应红并不知道。应红回到宿舍就看到了,应红的心暖了,嘴上说,你要改斜归正了?
王美琴说,你不是吹自己怎么会做饭?考考你。
应红大叫,哦,你是想找个炊事员啊!
王美琴依然是单身一人,应红也没有问过她,她记住了王美琴说过的话,秘密,秘密就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有了厨具当然就要做饭了,买菜是王美琴的事。在校园家属区的一栋宿舍楼前,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有了一个小菜市,有卖肉的,也有卖鱼的,卖米线、耳块的,蔬菜很多,都是挑了担子来的,水淋淋的,像是摘菜的时候正在下一场雨。要买菜就得蹲下身子,在圆圆的、扁扁的竹筐子里仔细挑选。王美琴买菜从来不问单价,只问最后要付的钱数。有几个常来卖菜的,见到王美琴就打招呼,招着手让她买自己的。王美琴也听招呼,有时根本就不蹲身子,只是任卖菜的农民拿什么给她,她就要什么。回到宿舍有时免不了被应红数落,什么烂菜你都买回来。王美琴探了身子,烂吗?哪烂了?两个人像在过日子。
王美琴买回了酒,还有一套酒具,透明的玻璃小酒杯,单薄的,很矮,没有任何装饰,应红很喜欢,喜欢用手摸小酒杯的感觉,喜欢她也不喝酒,就只是看王美琴喝。做饭的时候她是想了要下酒菜的,油炸花生米、爆炒牛干巴,再不及也要油炸兰花豆等等。应红下午的课少,有空在家里做一顿好饭。王美琴也有很多时间,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像是她这个人消失了,只留了应红在她的自己的房子和厨房里忙碌,应红也不问她在干什么,是根本不用问。
这是另外的一种生活,应红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琐碎的事情应红总是能应付自如的,可是在昆明的日子,让应红总有一种水上浮萍的感觉,尽管自己在这里有过四年的求学生活,但应红还是有一种没根没底的感觉。她尽管事事能干,却从来没有主人的感觉,做饭只是一种机械的劳作。
生活在别处。应红想。她时常想起玉水,那些往事经常像玉花江的水一样,无声无息地进入她的脑袋,她并不是自觉地去想的,那其中有很多让人不堪回首的事。
这样的心情应红没有告诉王美琴。儿女情长的话题总是不会让她们产生共鸣的,应红这样想。不说出来就积在自己的心里。有时目光看了别处就收不回来,目光直成了一根木棍,她自己不知道。她最挂念的是金花,那个女孩的样子时常进入她的脑子里,他们说她长得像她的父亲,有那么一双忧伤而潮湿的眼睛,还有那白皙透明的皮肤。应红仿佛看到了那两片红红的嘴唇,那是她给的。他们在她的身上融合了,又由她体现出来。应红被安慰着,又被刺激着。
有一天,应红又接到了家里的来信,随信寄来了金花的一张照片,彩色的,女孩骑在一个石狮子上面,很羞怯的样子,大睁着眼睛,刘海齐刷刷地排在她的眉弓上面,耳朵两旁是齐刷刷的发梢,应红举了照片,女孩的目光就定定地看了她,那目光对母亲是陌生的,闪着问号,像在追问,包裹着目光的依然是忧伤和潮湿。应红的心一下子被击中了,她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向邮局跑去,她要给应明打电话。应明有了自己的店铺以后,安装了一个电话,应红从来没有打过。打电话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离应红的生活很遥远。应红和应明约好,第二天把金花带到应明的铺子上。
应红没有想到,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邮局里挤满了打电话的人,应红挂了号,就在候话厅里找了一个地方坐下等候,她的眼前是来来往往的人,应红在想着金花的样子,产后在医院婴儿室的那一次。那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一张粉红色的小脸,紧闭着眼睛,大张着嘴巴,说不清她是在哭泣还是在叫喊,或许她已经知道她的父亲把她抛弃了,总之,她就是不睁开眼睛。那是应红永远无法忘记的画面。应红想起自己抱住她的时候,托口叫出了她的名字,像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那个女孩的眼睛睁开了,那是一双头一次看世界的眼睛,可是应红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目光中的忧伤和潮湿,应红认定她就是自己的。
候话厅里不停的有喊号的声音传来,应红的思绪还在过去的时段里,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女孩弯着眼睛对她笑着,女孩的笑撕碎了应红的心。应红把自己的脸挤在了那一张小脸上,泪水在女孩的脸上流过,女孩沉默着,张开小嘴吮吸着母亲的眼泪,像在吮吸母亲的乳汁。应红的眼泪滂沱起来,她的心轻了,因为郁积的泪出来了。突然,那个漂亮的小女孩从应红的脑袋里消失了,就好像一张图片被一阵风吹走了一样,应红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她在使劲恢复着自己的记忆,可是女孩的样子消失了,突然消失了。应红在脑袋里紧急搜索着,她就好像进到了一间空房子里,她什么都看不到,她在用手摸,用脚踢,可是她什么也没有碰到,什么也没有抓到。应红急了,她站了起来,跑到柜台前,问叫号的,到我了吗?叫号的白了她一眼,没有理她,她身边的一个大爷说,姑娘请你排队。她又沮丧地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心里焦急万分,越急脑袋里越是一片空白,那个女孩的样子还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应红张着眼睛四处看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的眼前依然是来来往往的人,耳畔是一些乱轰轰的声音,电话亭里有人的身影,有一个女人在流眼泪,另一个电话亭里是一个男人,他的表情很激动,手在夸张地挥舞着,这个世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似乎总是在发生许多事。
终于叫到应红了,应红冲进电话亭里,她向接线员报了玉水的电话号码,就进入了焦急的等待中,电话亭把外面的世界隔开了,应红屏住呼吸,她生怕呼吸声大了会把正在连接的电话信号吹跑了,等了好久,像是接线员把她忘了一样,听筒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应红又把电话放到了话机上,她再一次拨接线员,接线员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用了一句职业语言,应红又进入了等待,信号在听筒里呼啸,风一样,过了,又来了,终于远远的有了一个声音,他们都在大喊着,应红听清了是应明的声音,效果差极了,应红在大声叫着。后来,一个细细的声音传了过来,应红喊了起来,金花,金花!女孩的声音消失了,又传来了应明的声音,一下子清楚了,他说金花不愿意说了,一个孩子忸怩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奶声奶气的,应红的心紧了,接着又传来了应明的笑声,应明说她很好,特别好玩。后来应明又特别说了一句,你就放心得了。
应红并不是不放心,她更多的是在纠缠不安中,她被这种不安折磨着,她在追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金花?这个追问就好像是一种犯罪,她一夜一夜的失眠,她总是梦见金花在哭,一张肮脏的小脸任眼泪在上面流淌着。
应红动了退学的念头,她几次想告诉王美琴,她在最后都忍了,她知道她不会在王美琴那里找到同情的,王美琴只会痛骂她,并且看不起她。
她想到了河前,想到了玉花江,那一条永远平缓流动着的江水,清晰地展现在应红的眼前,那个画面像一只温暖的手一样在抚慰着应红。应红想到了那些美丽的田园,那些黄昏时的晚霞,绿色的蚕豆苗,在细微的晚风中荡漾着绿色的波涛。
可是她不能回去,那里还有一些让她伤心的往事。那些往事就像是一道栅栏一样,挡住了应红回去的路。
闲暇的时候,应红还是要想金花,那个女孩的样子在她的眼前飘动着,一会儿清晰无比,一会儿又模糊不清。她常常站在后阳台上,看流进学校来的那一条盘龙江,站在这里看到的江水是静止不动的,亮亮的,像一块被遗弃了的玻璃,应红想要真是一块玻璃倒好了,尽管她不再去刻意想窦志强,但是直到现在,她的生活里也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窦志强的男人出现,窦志强成了她的生活中至今为止惟一的男人。
有时,王美琴冷不丁地问她一句,你在发什么呆呀?
应红惊醒了,说,没有啊。
王美琴说,还没有呢?你看看蜘蛛网都要把你罩起来了。
应红就尽量注意,不让自己走神的时候被王美琴看出来。
不过王美琴的目光像是带了放射线似的,总是能看到她的心里。
再一天的晚饭以后,俩人在阳台上坐了,王美琴说,又在想金花了?
应红点了头,她并不希望是这样的,她总觉得自己在王美琴的面前就好像是一个透明体,不仅能让她看到肌肤,还能看到骨骼和血管。
如果有一会儿,应红没有说话,王美琴就问,你怎么了?
她并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是一些情绪,没有办法说清楚。情绪就是情绪,上来了,人就有反应。有一天应红就是有了一种情绪,她知道这样的情绪是莫名其妙的,就避了王美琴,一个人进了自己的房间,对着窗户暗自垂泪,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了,王美琴站站在门框下面。
应红觉得尴尬极了,她急忙揩了眼泪,假装没事,说,你应该先敲敲门。
王美琴说,这有什么?我是怕你出问题。
应红没有再说什么,她心里纳闷,会出什么问题呢?可是,她动了搬出去住的念头。
有了这个念头,应红就悄悄地在外面找起了家教的活,她想做家教一来可以有一些经济来源,二来也有了搬出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