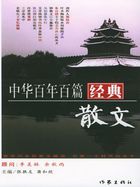《聊斋志异》是一部歌颂性变态的小说吗?
有人曾经宣称《聊斋志异》是一部宣扬性变态的书,事实果真如此吗?
虽然有学者曾经说过:在《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由狐妖故事所组成的妖精交响曲,事实上就是蒲松龄所谱写的『欲望交响曲』,它们所要满足的主要就是人们的色欲与财欲。其中又以色欲为主。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视为性变态文学,因为蒲松龄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人与妖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反映长期受封建礼教压抑的人们对性爱的渴望。在这一大背景下,那些男性甚至不怕妖魔附体,也不怕自己性爱的对象就是狐狸等野兽。精神分析学派的祖师弗罗伊德曾经说过:”文艺是性欲的转移和升华。””人们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或是由于自然原因,实现不了某些愿望,文学给予替代性的满足,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如果我们运用弗罗伊德的理论进行解释,就可以明白,《聊斋志异》中的人妖相恋是源自作者的一种潜隐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者内心深处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希冀和追求。
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篇小说,在︿卷十·五通﹀中,蒲松龄比较真实地写出了旧时江浙一带的五通神崇拜。在这篇小说的一开头,蒲松龄就写道:
有赵弘者,……妻阎氏,颇风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剑四顾,婢媪尽奔。阎欲出,丈夫横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爱汝,不为汝祸。”因抱腰举之,如举婴儿,置床上,裙带自脱,遂狎之,而伟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绝。四郎亦怜惜,不尽其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当复来。”乃去……至明,(夫)视妻惫不起,心甚羞之……妇三、四日始就平复,而惧其复至……四郎挽妇入帏。妇哀免。四郎强合之,血液流离,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妇奄卧床榻,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约妇痊可始一来。积两、三月,一家俱不聊生。
虽然一家人都非常痛苦,可是却无可奈何。后来出现一位勇士,一刀砍死了”四郎”,才发现这四郎居然是个马精,接着又杀死了前来相助的两只猪精,直到最后,五通神基本被消灭干净。在这篇小说中,令人感到疑惑的并不是蒲松龄对五通神的描写,而是对其中性爱场面的描写。难道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说,这是一部宣扬性变态的文学吗?
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恐怕并非如此。因为这篇小说中的主角”四郎”是一匹马变的妖神,尽管它在性爱的过程中非常可怕,作者也把它的施暴过程写得津津有味,但是作者的目的恐怕并非如此。用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只是作者为了真实再现一个妖神对女性的摧残而已;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完全丑化这只马精,而是把它写成也具有”怜香惜玉”之心,如”怜惜,不尽其器”,”约妇痊可始一来”。
除了︿卷十·五通﹀外,︿卷二·巧娘﹀、︿卷二·林四娘﹀、︿卷三·伏狐﹀、︿卷四·念秧﹀、︿卷五·伍秋月﹀、︿卷五·荷花三娘子﹀、︿卷六·林氏﹀等等都对性爱有比较大篇幅的描写,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呢?如果没有这些相关的性爱描写,是不是会影响这些小说的艺术性呢?我们还是以︿卷十·五通﹀为例,如果在这篇小说中没有性爱描写,那我们几乎看不出五通神究竟有多么可恶,人们想尽办法消灭五通神也就成了毫无理由的事情。更何况五通神本来就是一个淫神,如果将其中的性爱描写去掉,那又怎能体现出这是一位淫神呢!当然,这篇小说可能有些例外,那么,在其它的一些小说里,其中一些性爱描写原本是可以去掉的,蒲松龄为什么没有去掉呢?
我们都知道,《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广泛搜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而一般老百姓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在传说故事中掺有性爱情节是很正常的事。而蒲松龄为了让自己搜集的故事保留更多原有的风格,也只好保留下那些性爱情节。更何况,有的小说其情节本身就是靠性能力来推动的,如︿卷二·巧娘﹀,其情节就是靠男主角傅廉性能力的恢复来推动的,如果其中关于性的东西全部删除,这篇小说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而明朝中后期,社会环境极其开放,性爱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在明朝末期才会产生以《金瓶梅》为首的一大批所谓黄色小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蒲松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落魄文人,他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将性爱观念表现出来,似乎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单纯只因为他所撰写的作品中有较多的故事涉及到性,就称之为是渲染性变态,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蒲松龄的作品也只不过是以批判社会黑暗、人世污浊为主体的小说而已,如果我们人为地为它增加更多的言外之意,反而是对蒲松龄的误解,对《聊斋志异》的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