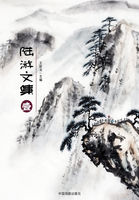在传播效用上,体制内主流媒体对行政的影响力,为其他媒体所不具备。这一点,仅从近期曝光的河南“双汇”瘦肉精、首都机场高速违规收费、广西来宾传销等事件上,即可见一斑。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多经媒体披露和网络盛传,但悬而未决,而央视一次触击,就立竿见影,换来地方政府的“紧急行动”。逻辑很简单:权力感应,政治回声。这虽是个让人愤怒的逻辑,但节目播出的实效又是积极的,符合社会期待。在新闻操作上,它们被央视曝光,全是各栏目的自然报题,属自选动作,并无坊间猜测的政治性安排和高层授意云云。
3
近两年,网络微博这种被称为“个人媒体”的新事物风靡天下,“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人人雀跃,人人欢呼,尤其在它打了几次漂亮仗后,前景一望无际,一片光的海洋,我也有点晕眩。但很快,我发现了新的事实:“真要围住一个东西,不让它逃走,须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才行。蚍蜉撼树,靠的是人海战术。而网络社会的特征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焦一个,忽略无数……对铺天盖地的虫害,围观只相当于生物防治,且每次都要牺牲几只带头的螳螂。”“在民意不能自动生成权力的时代,再人山人海的围观,也只实现效应而非效益,它须惊动权力、招来权力目光、引起权力焦虑才奏效……而它更大的作用,很可能在于联络和互动,在于彼此激励、增强信心、传递会意。”(以上为我两条微博发言)
我个人以为,围观改变不了中国,社会情绪的一致很说明问题,但并不直接修改什么,相对实体政治的坚固和磐重,它显得过于乐观和务虚了。再强烈的网络效应,也只是属于意见、声音、姿态的范畴,属于系统内繁殖,它并不具备直接和外化的行动品质,而对于其间接性,我们并不陌生,民意储备早就完成了。缺的还是路径,民意合法进入体制并上升至权力的路径。而且,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体制信任,双方都要有诚意,都要不计前嫌,学习妥协,给对方以安全感。
所以,网络时代虽转移了我们对主流媒体的注意力,但它的进步与否仍很关键,它毕竟占据了相当大的受众份额,更重要的是它对体制和体制相关人群的影响力及其符号性,远非网络可及。我常对自己和别人说,不要嫌弃它,至于它特殊气候下的糟糕表现,你完全可视为无效传播和形式主义。体制内媒体不进步,网络再怎么自由,南方报业再怎么奋勇,我都乐观不起来。共识和卓见不能圈在沙龙里,不能只搞自我复制和近亲繁殖,要推动体制,即要打交道,搀扶也好,安轮子也好,肩扛背挑轿抬都行。而泾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来,或搞空谷足音,立场上很决绝,道德上很清白,但失去了作用于对方的机会,是决裂的意义大还是合作的意义大?要改变一个人,总不能连理都不理吧?除非你不想改变,只盼这个人消失。社会进程是合力的结果,是四面八方交汇和平衡的结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派、中间派共同化合反应的结果,当然更取决于它们的比例。我推崇并尊重这种合力的阵容,希望它比例合理。
有时看网上发言,我纳闷为何连我欣赏的一些央视节目都遭羞辱,是期待太高?或怒其鲍肆出身、恶屋及乌?像曾经的《新闻调查》《社会记录》《新闻1+1》等栏目,我觉得它们已呈现较纯粹的媒体特征了,自选动作远大于规定动作,且以批评性报道为主,传统的宣传功能已大大弱化被媒体本能、职业理想和荣誉感、被内外部的竞争。当然,和一些纸媒相比,它的选题空间和话语权还是拘谨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它的紧缩和动作僵硬,这也是常被民间诟为“失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近年来的重大焦点和热点,比如黑煤窑和矿难、汶川大地震、华南虎事件、许霆案、三鹿奶粉事件、楼歪歪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王帅事件、孙伟铭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邓玉娇事件、唐福珍事件、李庄事件……它都没有缺席,甚至贡献了较扎实的事实部分,从而给民议、网评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材和起点。
无疑,这个时代对“声音”符号的渴望和消费需求是极旺盛的,总希望你能把意见以最清晰、饱满、露骨甚至刺激性方式抛出来,并以此去定性一个媒体的红与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理解这种渴望,也深以为声音的珍贵,但它更适用于有条件的媒体。因为角色和场地不一样。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大事实小言论”,电视不同于纸媒,文章是靠言论取胜的,而电视媒体的重心不在观点和发声,而在于现场部分,你给观众提供充裕的素材、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点就够了,你的“喉结”特征要让位于“眼睛”功能。
我想,之所以招来民间那么多责怨,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只是精神靶子,民间需要这么一面可以吐痰和掷物的墙,选择你当这个情绪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当之无愧,也许你有点冤,也许个体冤而整体不冤,也许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许初衷冤而事实不冤,在现有环境下,你必须为自己的出身埋单。再说对一个占有最大国家资源的媒体来说,再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过分。
以上举例,仅指向新闻频道的栏目单元,尤其改直播前的状态。我留意到,民间对央视的诟病,多集中于它的时政报道。坦率说,许多年来,时政报道的话语系统改进很小,叙事逻辑落后,这一点,主流媒体都一样,几乎被格式化了……即便从宣传上讲,也是低效率的。在这样的框架下,连“先进事迹”表彰也报废了,其实,有些“好人好事”作为精神事件和人性闪光,是很珍贵的,尤其道德荒芜的时代,这些萤火虫般的人和事,若得到更自然更本色的解读,换一种目光注视,很有意义。
4
媒体的事业空间和理想荣辱,首先取决于大的新闻环境,其次取决于它的管理者团队。在一个职业系统中,良币和劣币总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该比例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扑克牌,怎么组合,怎么出牌,考验管理者的判断和魄力。有时,良币多了会视为问题,因为它改变了构成。劣币多了也不行,因为一个媒体,它在民间的那点信用、口碑和收视率,要靠良币去积攒。过去有个说法:良币是给下面消费的,劣币是给上面消费的。我认为是个过时的策略,因为即便站在上面看,若不能保证良币的繁衍和足够份额,劣币是花不出去的,这是个捆绑式的销售,劣币是沾良币的光,吃的是良币利息。
一个媒体,凡好的历史时期,都和管理者的担当与智慧有关,他们在职业理想和体制职能间找到了结合,在积极和保守间找到了平衡点,在个人荣誉和集体使命间找到了并行感。央视新闻的黄金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是难以超越的标杆。
大众对电视媒体的兴致,很大程度上投注在主持人身上。其实,对媒体的观察和评价,也可借这个线索,比如白岩松,他可谓央视新闻二十年来最有标志性的人物,从专业角度,我尊重并欣赏这个人,我跟很多年轻的同事说,他做得真不容易,很心累。他有成熟而系统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很重要。独立的价值观和语言系统,是一个新闻主播最重要的装备,国内大部分主持人都不持有。我觉得在和体制寻找接口与组织有效对话方面,他努力了也尽力了,多数情况下,已把允许的话语能量调到了最大值。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甚至已脱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也给他争取了较大空间。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这种略显克制的角色,这种圆润而不失锐度的声音。再过些年,等我们走出了很远之后,回过头,我们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给予先锋和勇士之后的掌声给予它,感谢它的迂回和断后。
在体制内做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很难,会很痛苦,很受伤。只有身在其中才深知这种难。他们身怀良知,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物以类聚,有时靠个人之力争取一个选题,挽救一段影像、一两句自以为关键的话……从我个人的精神角度,我给了这些同事很高的评价和尊重,我理解他们的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要做事,哪怕是有限和极有限的事。否则,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就浪费了。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问原《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和悲怆,当你把用尽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识同人那里,却换来满脸不屑的时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面露苦涩:“是,人家在体制外的表达,已走了十步,你才踩着雷挪了两步,这是怎样的龟兔赛跑啊!”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交叉,能想象那种龟兔聚会的情景。龟是永远赛不过兔的,但这个时代,龟占基数,这个庞大的队伍需要导航。所以,兔子率领兔子,乌龟引导乌龟,龟要胜出的不是兔,而是趴着不动或跑得慢的龟,兔也一样,各在自己的系统里。
要谈理想,更要做阶段性的事情,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季羡林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学者如此,体制内的良币若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总之,既然放足时代尚未到来,那就先裹着小脚赶路吧。别放弃,别抛弃,别强迫它和别人比,要鼓励它和自己比。
选自《天涯》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