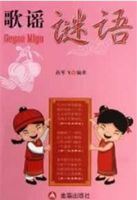与此同时,她也在每时每刻,给予我极其细致的关怀。由于有了她的关心,我的处境似乎好了一点。因为她在食堂做饭卖饭,所以我每次买饭的时候,饭盒里的饭菜,总显得比别人多得多。我知道是她在暗地里悄悄帮助我。有了她悄悄的帮助,就使我在超重体力的工作中,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来补充身体。后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是出于嫉妒之心,还是对我的仇恨之情,把她的行为告发了。于是她受到了警告,工队里的领导不允许她再卖饭,只让她在后面管盛饭菜。可胆大心细的她,在一个休息日后,给我带来了一个印有红花的饭盆儿。她说有了这个特殊的标志,她就知道哪个饭盆儿是我的,在盛菜的时候就可以往里面多盛。
我知道这样讨大家的便宜不好,就不愿意用那个饭盆儿去买饭,可她却十分认真地和我发了一次脾气。她说,许他们欺负你,就不许我照顾你吗?我无言以对她固执霸道的热心,便也就在感动之余顺从了她。
可是,我们两个人的接近,尤其是她对我的关照,使她遭到了报复。她被调出食堂,到工地上干活。建筑工地上的活儿,基本上全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她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够吃得消呢。为此,我痛苦万分(而且,至今我都怀有内疚),都是我连累了沈惠琳。
那时我们正为这个新建的兵工厂修路搭桥,整天打炮眼,开山放炮。劳动强度大不说,还非常危险。因为几乎每天都有哑炮出现。虽然排除哑炮这样的工作,从来也不让女工去干,可在打炮眼的时候,女工还是要担负把扶钢钎的活儿。这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一天8个小时,10磅的大锤,要在那细细的钢钎上捶打数千下,扶钢钎的人,还要不断地转动钢钎,稍有疏忽,大锤就会狠狠地打在扶钢钎的人的手上。
沈惠琳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被惩罚到工地干活。每当我在杂乱的工地上,看到她瘦小的身影时,心里就十分痛苦。为了弥补因我而给她带来的灾难,我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她。为了使她高兴,我常常偷偷从工地溜出,跑到附近的山上,寻找野酸枣和核桃带回来给她。有一次我竟然在那荒芜的大山中,发现了一颗长满了果子的杏树。我高兴得像只猴子,连蹿带蹦跑回了工地,并暗藏着这个欣喜没有告诉她。
那天黄昏,我悄悄用眼神,把沈惠琳约到工棚外面,然后拉着她的手跑进群山之中。山里的黄昏,静悄悄地铺满了迷人的绿色,但是,这迷人的宁静,被我们两个人欢快的脚步踩碎了。
我带着沈惠琳找到那棵杏树,指着那满树深黄色的野杏让她看。沈惠琳笑了,笑得眼睛眯眯的特别好看,脸上的两个小酒窝也仿佛在快乐地哆嗦。她揪住我的衣袖用力摇晃,笑着喊道:“我要吃—我要吃!”
我飞快地爬上树,一边摘野杏,一边把大个儿的给她扔下去。沈惠琳便笑着在地上爬着捡野杏,还用吃完了的杏核砸我。直到我把所有的衣兜都装得满满的,便抱着树干在上面吃野杏。沈惠琳站在树下,始终仰着头看着我,红扑扑的小脸上仍然漾满了甜甜的笑。看我只在树上吃杏,她笑着问我:“嗨!你干吗不下来?”
“我就是不下来。谁让你用杏核拽我。”
“讨厌!快下来!”
“不,我要把杏都吃光才下来,一个都不给你留。”
“你要再不下来,我就走了!”沈惠琳真的生气了,她撅着嘴转身就走。
我赶忙从树上蹦下来,追上她,一把将她抱到树下。沈惠琳便笑了骂我:“再不下来,我就永远也不理你了!”
我们两个紧紧靠在树下,吃杏肉砸杏核儿,谈天说地设想着自己的未来。那一个个圆圆的野杏,散发着醉人的香甜,沁透了我们两颗年轻的心,让我们暂时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庸俗和烦恼,只沉浸在我们青春浪漫的自由之中。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迷人的夜色,覆盖了大山,周围的绿色植物也沉入了自己的梦乡。飘飞在大山中的青草气息,轻柔地包裹着我们,惬意极啦。黑色的半空里偶尔有什么东西飞过,听得见它“嘎嘎……嘎嘎……”孤独的鸣叫声。我猜想,它正奋力扇动翅膀,要撕破这山野中黑色的天幕,让天地间有一丝丝光明。当我们沉浸在心灵碰撞的激情里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激情里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远山处传来一阵野兽的嗥叫,冷不丁地给这静谧的、黑黑的夜晚平添了一点恐怖。
正是这野兽的嗥叫声,把她推进了我的怀里。她娇小的身躯似在轻轻颤抖,双手却有力地把我搂紧。她额头前蓬松的短发,被山间的野风吹动,带着她的体香顽皮地搔挠我的鼻孔。我转过头去,感到她正高仰着她红扑扑的小脸,就像刚刚她看着野杏树上的我一样认真,一样着迷。我低下头去,让距离将黑夜从我们中间赶走。是啊,距离就是黑暗,距离就是障碍,我们不要,我们不要黑暗!
噢!我看到了,她微微闭着眼睛,长长的眼睫毛,忠勇的卫士似的掩盖着她的羞涩,红润润的双唇却张开着,一个湿滑的舌头裸露在那里时隐时现,仿佛是一朵正在开放着的花,在期待着雨露的滋润。她的一只胳膊绕过我的身体,把小手轻轻抚在我的腰背上,把一种灼热固执地印在那里,并让这灼热穿透我的皮肤,深深地渗进我的骨髓之中,让它蔓延到我的每一寸肌肤里,让它像火一样在我的身体里燃烧。我觉得那是一种无声的诱惑,是爱神突然降临到我的身畔。这时,黑的夜幕,仿佛已经悄悄地从宇宙间退去,一缕金色的光芒笼罩住我们,绿的山野里,飘飞着无穷无尽的柔情蜜意,小天使似的在我们周围笑闹。
此时此刻,我的心感受到她青春的躁动,迷失于她女性情感的万有引力之中。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嘴唇碰在了一起,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吻,它促使我的灵魂,随着她的肉体和她轻轻的呻吟一起颤抖。在那个吻里,我无法左右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只是忙乱地寻找着她纯洁火热的所在,放纵地将自己深深地伸了进去,并长久地陶醉在裸露着她青春湿润的口唇上。那象征着我们情爱开始的吻,带着在田野间弥漫的杏香,带着我们青春的羞涩和放纵,带着我们情窦初开的盲目和力量,让我们长久地徘徊在那透入骨髓般的细腻感觉里。
夜的宇宙间,轻轻飘荡着我们甜甜的笑声。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两颗心越贴越近。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我在市政公司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了。
由于有了心的另一种慰藉,笨重的体力活儿竟然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曾经试图改变自己。可无论我怎样的努力,也无法使我和那些人融为一体。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轻薄的屏障,彼此能够相见,却无法相融。因为,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方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关注的不是个人怎样修身养性,不是怎样攫取知识,不是怎样努力建设国家,而是时时刻刻关注着别人的大脑在想什么。一旦他们发现你的思维能力超越了他们的蠢笨时候,你就注定要遭殃了。
那是在一个叫青水涧的地方,因为修桥,我们工队调来了一部WKAS,这是一种大型打孔机械。当时非常矛盾的是,只有一位随机器调来的师傅能够操作它,而打桥桩的孔,又需要日夜不停地连续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队领导决定从我们这些壮工里,选几个年轻人去学习操作。而被选中的五个青年工人里,想当然的没有我。
那个时候,我也从不奢望会有什么好事和幸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那时,我除了每天应付8小时的艰苦工作和3小时的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外,就是拼命地读书。虽然那时的书非常单一,书里的内容也绝大部分是空洞的说教,可我仍然从其中找到了许多有关人文学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中汲取我需要的营养。那个时候我仍然时刻想着用自己强健的身体和聪明的大脑为这个行业贡献自己的全部身心。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创造的财富,都是为国家做贡献,都是属于这个民族的,我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那些学习操作机械的人,是在四个星期后回来的,可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学会了操作那台打孔机。面对这种尴尬的结局,他们一筹莫展。于是,就使我有了一个初露锋芒的机会。我对那个随机械一起调来的师傅说,我能试试吗?开始他还不相信似的看着我,但他又马上点点头,然后给我讲了一遍操作规程,又开动机器亲自为我示范了一遍,然后就停下机器让出了操作台。
我胸有成竹地走上去。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地知道:天生做工匠的人,是用不着学徒的。早在7岁刚刚上小学那年,我就用铅笔刀把一块橡皮,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猴子。而我没有学过美术,更不懂得雕刻。只是用心灵感悟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因而,我坚信,我年轻的生命,可以应付任何来自生活的挑战。WKAS的周围站满了人,他们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在那许许多多的眼睛中,我看到了她和好朋友们的期望和鼓励,就更加充满了信心。
河套里的秋风,带着丝丝清凉,欢快地笑闹着,我却感到全身燥热,非常紧张。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我的命运而搏斗,成功了,它将预示着我将来事业的好转;失败了,则可能造成我在这个单位永世不得翻身。那些家伙会嘲笑我吹牛皮,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我。
为了证明我个体生命的价值,为了让那些人知道“知识和能力就是力量”,我暗自憋了一口气,把手伸向那台庞然大物,毫不犹豫地扳动了启动手柄。“轰隆”一声巨响,WKAS的柴油发动机咆哮着启动了。在它野马奔腾般的狂躁中,宇宙万物仿佛变得渺无声息,整个河套中都轰响着它吼叫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却突然平静下来。我用双手握紧操作手柄,轻轻拉动,让离合器摩擦、结合,粗粗的钢丝绳慢慢绷直了,那重达2吨的大铁锤被我稳稳地悬吊在空中,又准确地将它轻轻地放进浇铸桥桩用的沉井之内。“呼啦”一下子,黏稠的泥浆水,被大铁锤挤出了沉井,变幻着得意的奇形怪状,用它红色的浊流,染脏了奔流不息的永定河水。然后,我按照操作要点,把机器设定到工作档位上,让它轰鸣着,向大地开战了。没有欢呼,也没有掌声,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成功了。看着打井机颤抖咆哮着,“咚咚,咚咚,咚咚”地在沉井里,强劲有力的不断地锤击,看着坚硬的大地,在它的锤击中无奈地哆嗦、呻吟,我热血沸腾了,全身洋溢着男人的阳刚之气。仿佛那个上下运动的铁锤就是我的身体,我要用我生命的力量将地球击穿。
经过他们开会研究,我在控制使用的框框里,成了操作那台机器的三个班次中,其中一个班次的领班人。生活虽然依旧,但是到底有了点转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和我分手了。因为我看到了一幕丑陋的事情。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深夜,打孔机出了故障。我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冒雨奔回驻地去找那个师傅,想让他帮助排除机器的故障。因为建桥打桥桩孔,是不能长时间停机的。长时间停机,沉井下部会被流沙侵袭,刚刚打好的桥桩孔有坍榻的危险。可到了他的宿舍才得知,那个师傅家里有急事,连夜赶回城里去了。事关重大,我不敢耽搁,连忙跑到队长宿舍,推门闯了进去。
开门的声音,淹没了一种女人的呻吟声。跟着一片乱七八糟的声响从床铺那儿发出,两条闪着白光的肉体正在忙乱地遮掩躲闪。虽然是在暗夜之中,可我还是看清楚了,那个女人是她。因为我对她的音容笑貌太熟悉了。
全身湿透了的我,落汤鸡似的站在那里,不会说,不会动,身体麻木得像一具木雕。我的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心脏怦怦怦怦地狂跳,仿佛就要炸裂开来。我粗糙的大手紧握成拳头,准备扑上去把那个男人砸扁。但是,在我还没有行动以前,她赤裸裸滚下床,跪倒在我的面前。此时,那个男人正在慌乱地穿衣服。她浑圆白嫩的双膊,紧紧抱住我湿淋淋的两腿,使我不能行动。她仰起头,声音急促而颤抖地哀求我:“求求你,你别说,也别打他。是我愿意的。求求你!”
“为什么?为什么呀!?”我像野狼似的嚎叫起来。
她哭了。好半天她才抽泣着说:“我受不了了。太苦了,太苦了!我想离开这里,去别的单位、去上学,去干什么都成,只要能离开这里。我是一个女人,我真的受不了了。他,他已经答应我,帮我离开这里。求求你了,求你了!”
黑暗中,她的头使劲向上仰着,刚刚被那个男人蹂躏过的身体,紧紧地贴在我腿上。她无遮无掩的前胸,随着她的抽泣一下一下地耸动,仿佛是在给我一个永无休止的挑逗。
听着她的话,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罪恶的阴谋。那个臭男人,已经近五十岁了,而且家有妻子儿女。他平时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他满嘴都是革命豪情和政治思想,骨子里却是个男盗女娼的家伙。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要求我们做一个政治上进步的人,做一个听话的青年。可他们却灵魂肮脏物欲横流,暗地里做着践踏我们青春的勾当。
看着瘫软在我面前的她,那么柔弱那么可怜,我的心悲泣了。她毕竟是真心帮过我的姑娘啊。当时我的心里非常清楚,我复仇的机会来了。在那种禁欲的社会环境中,只要我把这件事说出去,那么,这个家伙就会因所谓的“作风问题”而身败名裂。那样,他的处境肯定比我还糟。可是她怎么办呢?她的名誉也会玉碎瓦破。我不能做这种无情无义的事情,万般无奈中,我摇了摇头,低声说:“为了你,我什么也不说。”然后转身走出了那间肮脏的屋子。在推开屋门的一刹那,我猛地转回身,咬着牙对那个家伙说:“你记着,这笔账我早晚要你偿还!”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死一样的沉寂。我转身走进雨夜之中,万没想到的是,追随而来的却是那个家伙得意的笑声,还有她痛苦的哭号声。
秋雨仍然不停地下着,我茫然地沿着山间公路向工地走去。山区的夜没有一点光亮,到处漆黑一片。暗夜中我一个人的独步,是多么的凄凉啊。无情的秋风吹透了我湿淋淋的衣服,也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是整个宇宙都在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