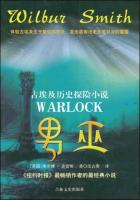轻浮的笑。幸灾乐祸的笑。窃窃私语的笑。外力的作用打开了岩浆的缺口,喷薄而出。袁玫用力抽回自己的手。胡成却不放。她再用力。抽伴着甩,竟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岩浆流尽,只剩僵硬的雕像的躯壳。她摇摇欲坠,一手搭在自己额头上,趔趔趄趄了几步。
“谁,谁******敢打我?”胡成摸了把脸,使劲正了正身子,始终处于半眯状态的眼睛东瞧西看了一番。被酒精拖住了重心,他的脚步随着脑袋的转动左右颠簸,“谁,谁呀,怎么******不说话?”
所有的声息瞬间凝固。空气被压缩得几近极点,任何一丝碰撞都足以擦出燃烧的火光。
石雕被压碎,坍塌,一地碎石。碎成一点点晃眼的白,碎成一阵阵逼人的寒意。袁玫打了个冷战,嘴唇难以自持地剧烈抖动。她握紧手中的拳头,扭头就要冲出房门。
“小袁,小袁,你不要这样,胡成,胡成,他喝醉了!”有人拉住了袁玫的手,试着劝说,“难得几个老朋友聚在一块儿,胡成也很少这样的……”
难得几个老朋友聚在一块儿?天啊,还难得?这几年,你们聚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吗?胡成很少这样?只怕是我没见到的比这个还要厉害得多吧?袁玫用大大的眼睛瞪了一下那人,想说的话终究没说出口。人前,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还在维护胡成的面子。
袁玫挣脱了那人的手,“砰”的一声摔门而出。
冷风吹来,袁玫紧了紧身上的大衣。已是午夜十二点多,大街上一片冷清。她漫无目的地走,脸上一阵冰凉。一摸,一脸泪水早已在寒风中失却了温度。跌跌撞撞地走出一段路程,她才猛然发现,自己正惯性地往家走。回自己的家?不,不能这么狼狈地回去!不能如此视若无睹地纵容他!袁玫收住脚步,下意识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娘家?不!别再让父母跟着受气了!当初,他们坚决反对我们的婚事,而今,他们却希望我们好。路是自己选择的,与其让更多的人来分担,不如让自己一个人承受。她下意识地选择了过桥,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酒啊酒,你难道把我害得还不够吗?你还要害我到什么时候?
如果不是因为酒,袁玫不可能嫁给胡成。
幼师毕业后,袁玫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在东关乡妇联。胡成也在这个乡,是司法办的小办事员。刚满20岁的她有如出水芙蓉,除了皮肤不够白晳外,164厘米的身高,凹凸有致的身材,长长的披肩发,柔情似水的目光,让她很快就成为年轻男同事瞩目的焦点。很多小伙子左权衡右掂量,没有了追求的勇气,只有胡成单枪匹马开始了勇往直前的追求。90年代初,论家境,胡成自然是首选。他家也在城关,有房有店面,又是家中独子;论身高和长相,173厘米的他也算是一表人才,甚至是玉树临风。可不知为何,她总觉得职校毕业的他,身上缺少一种自己喜欢的气质。他的一表人才只停留在表面的一层纸上,禁不起琢磨。所以,对于胡成的穷追不舍,她只报以冷漠。她把热情投给了另一个年轻人——时任乡团委书记的于洋。虽然于洋一直不动声色,但她可以感觉到他不动声色下的好感。与胡成正好相反,于洋家境不好,长相也一般。他比袁玫大两岁,大学本科学历,170厘米的身高,长得斯文秀气,甚至还带点学生的憨态。但他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书法,更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全县十几个团委书记中屈指可数。那一年,县委办正在对他进行全面考核,有意把他往城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