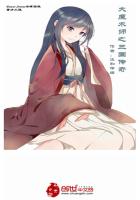趴好之后,我将伪装的巴特雷长枪管儿轻轻捅出迷乱的草丛。周围的空气很潮湿,肚子下面湿漉漉的植物,虽然柔软,却让我很不舒服,因为现在没有厚实的狼皮格挡,敌人的伪装服有点单薄。
由此推测,那几个散落在两侧峰顶的海盗狙击手,一定也舒服不到哪去。上午七点二十四分,我仍趴伏在深深的草丛里面,略略仰起脖子,搬着望远镜观测两面峰顶的树林。此时,降雨停止下来,只吹过山风时,冷得人难受,好比穿着短袖走在秋末冬初的黄昏。
八点三十二分,当一条手腕粗的锁链蛇从我枪管上缓缓爬过,一千一百米远的第一个牵魂再次中弹,但我丝毫没注意到子弹射出的方向。
我伪装的伏击点,是在天黑的时候设置,天空开晴后出来赶早的太阳,刚从淡墨色的天际露出微弱的鱼肚白,我就没再动过,敌人不可能发现我。
现在,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又过了二十分钟,我腰上的无线通讯噪音波动异常,很显然,至少有一个海盗狙击手在不断向我靠近。我很担心自己更换的衣物上隐藏了纽扣式定位系统。
若真跑过来一个或几个海盗狙击手,把我当成同伙靠拢,那样就很危险。我急速关掉伪装服上的无线通讯开关,手上的望远镜,始终盯紧两点钟位置的那片树林。
当我发现一双急速奔跑的脚,敌人已经出现在五百米远的位置,这不禁使我一愣,对手居然从我后方奔跑过来,他一定是感应到了讯号,向我急速靠拢,希望重新衔接上队形。
幸好我把乱频及时关掉,迫使那个敌人感应队友的讯号中断,不得不像无头苍蝇似的,调头朝正前方跑去。那个海盗狙击手,以为在队友守杀的狙击范围奔跑很安全,便放弃了迂折前进。
我快速放下望远镜,眼睛贴紧在狙击镜上,T型准线顺着缓缓扭动的枪管儿,很快捕捉到那两条在林间急速飞跑的小腿儿。
本想射击对方的头部或胸腔,可由于树上垂下的枝叶茂盛,遮挡住了目标的上身。圆形镜孔中,密集的林木底层视野很有限,只给我看到交错闪现的两条腿,在快速倒腾着奔跑。
“慢一点,再慢一点,回头凝望你的真主……”嘴巴默默唇语,几根柔软的青草,不断摩挲在我蠕动的脸颊。
“嗖呜”。抓住机会,就在那双跑动中的小腿突然驻足,等待大脑传达变换方向的指令,一颗尖鸣的子弹,猛得窜出枪膛,撞碎挡路的草叶,直冲目标飞去。
子弹的飞行速度极快,贴着树林下的地表,划出呼啸的火线,那些因潮湿而沉沉入睡的枯叶,被白线上的疾风卷得瑟瑟发抖,仿佛患重病躺着的人,想突然坐起,但又力不从心。
那个披挂着厚厚伪装的海盗狙击手,刚要抬脚起跑,子弹就打进了他左脚踝的凸球骨,使得这家伙整个人重重摔倒,好比奔跑的骏马忽然趟到绊马索,毫无保留的前倾摔趴,折鼻梁、断门牙、破肉唇自然来不及避免。
中弹的海盗狙击手,侧躺在潮湿的落叶上,极度惊恐的蜷缩双腿,欲抽身朝大树后面蠕动,寻找保佑生命的掩体。我狙击镜前方的视线,一排排大树犹如列阵的士兵,为了不丢失那条可以贯穿直线的缝隙,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拉出枪膛里的弹壳,手指再抠扳机,始终贴在瞄准镜上的眼睛,一刻不敢松懈的盯住目标。
“嗖嗡”。巴特雷狙击步枪,像凶残的毒蛇,及时补咬猎物第二口。子弹在极短的时间内,顺着尚有余温的空中弹道,再次钻进敌人的小腹。但我知道,这两枪都不是致命的,为防止敌人中弹后有时间呼叫队友,我不得不第三次扣动扳机,给他冒血的小腹再填充一颗子弹。
那个海盗狙击手,在树林下挣扎扭曲,异常的痛苦,他受伤的踝骨破碎得厉害,虽然脚掌仍连着小腿,就算拿到医生面前,也得用锯子割断。
我停止射击,眼睛依旧注视横躺的目标,海盗狙击手的头部和胸腔始终被一颗粗大的树木遮挡,但他汩汩冒血的小腹,已把外围的伪装布条浸渍饱满,猩红的鲜血颗颗凝聚,如沉甸甸的石榴粒,顺滑到衣物下面压的枯黄叶片上,旋转个不停。
看到抽搐的敌人渐渐僵硬,我总算舒缓一口气,射杀这个海盗狙击手实在冒险。第三颗子弹一定镶嵌在他脊椎骨的内侧,破坏掉神经网络,才没让他有机会调试波段旋钮,向队友报告遇袭情况。
掏出背包里一块儿干硬的鲶肉,塞进嘴巴慢慢咀嚼,假如因为刚才的三枪,不幸被敌人察觉,就算中上敌人的冷枪,也要做个饱死鬼。
十七岁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用食物填饱胃口的滋味儿,加入佣兵营地那天,这种饥饿感却被恐惧代替,我射杀过很多无辜的人,因为有时候,敌人也是无辜的。
我像一个被上帝和恶魔同时争抢的孩子,双臂欲裂的恐惧和痛苦,犹如铁蒺线绑在我的内心。但我知道,我必须活在自由里。
没人知道,一个鲜活的生命,趴在大自然的肌肤上隐蔽,怀念心上人时,脑袋突然被打爆是怎样一种恐惧。当初,我做那七个牵魂替身,等于给自己复制生命。
战场像一坑血池,我在里面摸爬滚打,深信着一种规律。交战双方,彼此的子弹都要互相射击,都有命中目标的可能。所以,我把自己的生命参与到几个稻草人偶里面,供给对方射击并命中,从而使自己在死亡筛选的漏斗里掉出来。
这是一种看不到的发自宇宙原点的平衡规律,注意不到这个深度,假如还想活命,等于破坏了一种叫“永恒”的东西。上帝的车轮,自然会把这种存在辗碎。
嘴里咀嚼着的肉干儿,像泥巴一样没有滋味儿,我现在就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右翼峰顶的海盗狙击手锁定。对方爬上高高的大树冠,等着打碎我探出脑袋,这也存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