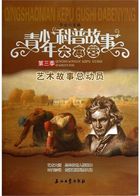歌德首先朗诵那个钟情于一位年轻女郎的老人唱的歌,接着朗诵妇女们的饮酒歌,最后才轮到激情澎湃的《为我们跳舞吧,特奥多尔》。每一节诗他都用一种不同的音调和节奏,真是精彩极了,很难再听到更加完美的朗诵。
我们不能不称赞盖哈特,说他为每一节选定的格律和反复都非常得体,非常成功,一切在他都轻而易举,都完美得不可能再完美。
“这下你看见了,”歌德说,“对于盖哈特这样一位天才,大量的技巧训练有什么好处。同时,写诗在他并非从事一种学来的职业,而是满足现实生活的日常需要,这也使他受益。他还常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游历,旅途中凭着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增长阅历,见识超过了我们那些靠学习才成功的年轻诗人。一个诗人始终坚守优秀传统,只继承发扬传统,的确不容易写出什么糟糕的东西。可另一方面,所有自己的创造,都需满足很多要求,都非常艰难。”
紧接着,我们观察了我们几位最近才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的创作,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写散文过得了关。
“道理很简单,”歌德说,“写散文必须言之有物;谁要没有什么说的,他就可以做做诗,押押韵,让一个词儿引出另一个词儿,最后就搞出来了一篇东西;这东西尽管毫无意义,可看上去却好像有意义。”
1827年1月31日,星期三
(谈中国小说;“世界文学”;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同歌德一起进餐,他说:
“在没与你见面的这些日子,我读了不少书,特别是一部中国小说,我眼下还在读它,觉得这部小说极为值得注意。”
“一部中国小说?”我接过话头,“那肯定挺怪的吧。”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怪,”歌德回答,“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加明朗,更加纯净,更加符合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富于理智,都中正平和,没有强烈的情欲和激扬澎湃的诗兴,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以及英国理查生的小说颇多相似之处。可不同之点还是在于,在他们那里,外在的自然界总是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人们总是听见池子里的金鱼在跳跃,枝头的小鸟儿在一个劲儿地鸣啭,白天总是那么阳光明媚,夜晚总是那么清朗宁静;写月亮的时候很多,可自然景物并不因其改变,朗朗月华在他们的想象中明如白昼。还有房屋内部也精致、宜人得一如他们的绘画。例如,‘我听见可爱的姑娘们的笑声,随即看见她们坐在纤巧的藤椅里’。这情景立刻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因为藤椅必然使你联想到极为轻巧,极为纤细。而且故事里随时穿插着无数典故,援用起来恰似一些个格言。例如讲到一位姑娘的双脚是如此轻盈、纤小,她就是站在花上,花也不会折掉。又讲一个青年男子,德性和才学都很出众,所以三十岁时便获得了和皇帝谈话的恩宠。还讲到一对情侣,双方长期交往却洁身自好,一次不得已在同一间房里过夜,仍旧只是以交谈打发时光,谁也不曾碰一碰谁。类似的无数典故,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然而正是这凡事都严格节制,使中华帝国得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还会这样继续维持下去。
“与这部中国小说形成极有趣对比的,我看是贝朗瑞的诗歌,”歌德继续说,“他的那些诗全以不道德的、淫秽的素材为基础,如果不是出自贝朗瑞这样一位大天才笔下因而尚可忍受,不,甚至显得优雅的话,那将令我极度地反感。你可自己说说看,中国诗人写的内容如此绝对符合道德,法兰西当代诗坛首领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有意思极了吗?”
“一位像贝朗瑞似的天才,”我应道,“也许根本写不了符合道德的题材呐。”
“你说的有道理,”歌德回答,“正是通过揭示这个时代的反常现象,贝朗瑞显示和发挥了自己天性之所长。”
“不过这部中国小说,”我讲,“也许是他们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吧?”
“才不哩,”歌德回答,“他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小说,而且早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莽莽森林里,就已经有了。
“我越来越认为,”歌德继续说,“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马提森先生因此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他是诗人, 我也不得以为,只有我是诗人,而是每个人都该告诉自己,写诗的天赋并非什么稀罕物儿,没谁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就有特别的理由感到自负。显而易见 ,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哦。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唯视其为杰出典范。我们不应该想,只有中国文学杰出,或者只有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只有卡尔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龙根之歌》杰出; 而总是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儿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典范,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塑造的是美好的人。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
我很高兴,听歌德就一个重要话题一口气谈了这么多。几辆雪橇驶过楼前,叮叮当当的铃声把我们吸引到了窗户边上;因为我们正等待早上驶往美景宫的橇车队原路返回。歌德继续做他富有教益的发言。话题涉及到亚历山大·曼佐尼。他告诉我,不久前莱因哈特伯爵在巴黎见到了曼佐尼先生,作为一位有名的年轻作家,曼佐尼受到当地社交界的盛情款待,而眼下却又住在了米兰附近他的庄园里,带着一个年轻家庭以及他的母亲过着幸福的生活。
“曼佐尼什么都不缺,”歌德继续说,“缺的只是自我认识,竟不知自己是一位多么杰出的诗人,以及他作为诗人所应有的权利。他过分尊重历史,因此在剧本中总喜欢加进一些议论,以证明他是何等忠于历史的细节。他写的事件尽可以符合历史,可人物却不是这样,正如我的陶阿斯和伊菲根尼也不是这样。没有一位剧作家啥时候见过自己塑造的人物;即使真见过吧,也很难照样拿来就用。剧作家必须知道想要达到的效果,并照此调整人物的性格。如果我照历史的记载塑造哀格蒙特,把他写成一大群孩子的父亲,那他在剧中的轻浮之举就显得很荒唐啦。也就是说我必须塑造另外一个哀格蒙特,让他与自己的行径和我的创作意图更加和谐;这正如克蕾尔欣所说,是我的哀格蒙特来着。
“如果只想复述历史学家的历史,那剧作家又有什么用?作家必须往前走,为我们创造出一些尽可能更崇高、更完美的东西。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全都体现一点伟大诗人的高尚心灵,莎士比亚的人物也一个样。这是对的,就应该这样写。是啊,莎士比亚甚至走得更远,把他的罗马人都变成了英国人,而且也有道理,否则他的同胞们如何能理解他。
“在这一点上古希腊剧作家又显得来如此伟大,”歌德继续说,“他们不大在乎史实多么真实,而更在乎剧作家如何处理史实。很幸运,我们现在还有《菲罗克忒忒斯》这么个光辉的例子,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全都写过这个题材,而索福克勒斯却后来居上,他的杰作很幸运完整地为我们保留下来了。相反,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菲罗克忒忒斯》,却只发掘到一些片断,但也足以看出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题材。要是我的时间允许,我想把他们残损的剧本修复还原,就像我曾修复欧里庇得斯的《法厄同》一样;这对我不会是一件不愉快的和无益的工作。
“处理《菲罗克忒忒斯》这个素材,任务很简单:就是要把菲罗克忒忒斯连同他的弓,从列姆诺斯岛接回来。至于如何个接法,可就成了剧作家的任务了,在这点上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都可以超越其他人。尤利西斯负责去接,可他该让菲罗克忒忒斯认出来呢或是不认出来呢,如果认出来了又凭的是什么?让尤利西斯独自去接呢,还是让他有一个同伴,又让谁来做这个伴呢?在埃斯库罗斯的剧本里,这个伴不为人认识;在欧里庇得斯那儿,他是狄俄墨得斯;在索福勒斯那儿则是阿喀琉斯的儿子。还有,菲罗克忒忒斯被找到时是个什么状况?那座小岛是有人居住,还是荒无人迹;如果有人居住,是由某个好心的人收留了他,还是没人收留他?诸如此类的成百个问题,都要由剧作家来决断,来选择或是不选择,并以此检验他们智慧的高低,分出彼此的胜负。症结就在这里,当代的剧作家们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而不是老在问一个素材已经被写过了或是没写过,老在南方和北方寻找闻所未闻的事件,结果常常又觉得这些事件太原始,到头来仅仅也只能是事件罢了。当然喽,要用高超的艺术手腕把简单的题材变成一部差强人意的剧作,可需要聪明才智了,而眼下缺少的正是这些东西。”
楼外驶过的雪橇又把我们吸引到窗前,仍然不是我们期待从美景宫回来的一行人。我们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然后我问歌德,《Novelle》改得怎样了。
“这几天我没有碰它,”歌德回答,“只是引子还是得动一动。当侯爵夫人骑马从小屋前经过,雄狮必须发出咆哮,此时我就可以对这头猛兽的可怕,插进几点很好的思考。”
“你这想法很英明,”我说,“如此一来,引子就不只很好发挥了本身的作用,就有存在的必要,还增强了后面发生的整个故事的感染力。在此之前,那头雄狮几乎都显得太温驯,根本没表现出一丁点儿野性。可你让它一咆哮,至少让我们隐隐感到了它的可怕;随后它温驯地尾随在吹笛儿的男孩后边,这就有了更大的震撼作用。”
“这样的改动和润色方式是正确的,”歌德说,“可以通过不断的创造,使一件尚欠完美的作品得以提高,变得完美。可另一种不断重写、翻新一件已经完成的作品,例如斯科特不断重新塑造我的迷娘,在她的所有其他特征之外又加上又聋又哑:这样个改法我可没法给以称赞。”
1827年2月1日,星期四
(求变是自然界与文艺的共同规律;歌德的自然科学研究)
歌德对我讲起普鲁士王储在卡尔·奥古斯特公爵陪同下的一次来访。他说:
“还有普鲁士的卡尔王子和威廉王子,今天早上也在我这里。王储和大公爵逗留了将近三个钟头,谈了各式各样的事情,让我对年轻王储的智力、品味、学识和思维方式有了很高的评价。”
歌德面前摆着一本《颜色学》。他说:
“我还一直欠着你的债,不曾回答那个有关彩色阴影现象的问题哩。可要回答得满足许多前提,而且牵涉到别的许多东西,所以今晚我还不想对整个现象作出解释,而是认为咱们利用几个待在一起的晚上,把《颜色学》整个通读一遍更好些。这样我们总算有了讨论的坚实基础,你自己呢不知不觉就掌握了整个颜色学。学到的知识开始在你那里显示出生命力和生产力,由此我预见到,这门学问很快将为你所有。喏,念第一章吧。”
说着,歌德已把翻开了的书摊在我面前。他对我的好意令我深感幸福。我读了讲述生理颜色的头几段。
“你瞧,”歌德说,“除了同时存在于我们体内的东西,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外在世界有的所有颜色,我们的眼睛也都有。由于研究这门学问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主观和客观,那么我一开始先讲属于眼睛的颜色,就是有道理的;这样,在后来的所有观察中,你总能分清楚颜色是真的存在于我们之外呢,或者仅只是由我们的眼睛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色。既然一切的感知和观察都必须通过这个器官,那我就先来矫正它,我想,我这么做算是抓到点子上啦。”
我继续往后读,读到了人眼对颜色有所要求的有趣段落:就是讲人眼总要求有所变化,永远不喜欢老盯着同一种颜色,而要求变换成其他色彩;这要求是如此活跃,人眼甚至会自行创造出实际上看不见的颜色。
由此谈到了一条重要法则;这条法则贯穿整个自然界,构成了人生以及人生一切乐趣的基础。
“它不仅适用于我们的其他感官,也适用于我们的高级精神活动,”歌德说,“只不过因为眼睛这种器官异常发达,要求变化这条法则在色彩方面就表现得特别显著,也最先为我们所清楚意识到。有些舞蹈极为我们喜欢,就因为长调短调交替,相反,如果光是长调或者光是短调,立刻就叫人厌倦啦。”
“这同一法则,”我道,“似乎也是好的文笔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总喜欢避免老调重弹。在戏剧里,这个法则如果运用得好,将会取得很多效果。剧本特别是悲剧,如果总是毫无变化的一个调调,就令人反感、 厌倦,而要是乐队在一出悲剧的幕间还演奏忧郁、低沉的乐曲,那观众更会感到难以忍受,便恨不得想方设法逃走。”
“也许就基于这条要求变化的法则,”歌德接过话头,“莎士比亚的悲剧也编织进了一些欢快场面;不过对希腊人更高级的悲剧,它却似乎不适用了:古希腊的悲剧多数都是一个基调贯穿始终。”
“古希腊悲剧也不怎么长啊,”我说,“所以同一个调子才不致叫人厌倦;再加还有合唱与对白交替,而且立意又那样崇高,还总是以鲜活、强劲的现实为基础,观众就不可能感觉厌倦了。”
“你可能是对的,”歌德道,“希腊悲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要求变化的普遍法则,也值得花些力气进行研究。不过你看见了,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一条颜色学的法则,甚至也可以用来进行希腊悲剧的研究。只不过得谨防滥用这样的法则,拿它做基础去套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物和现象;保险一些的做法是始终仅用它作类比,仅以它当例证。”
我们讨论歌德讲述他的颜色学的方法,也就是他总爱从原始的大法则推导出所有的一切,反过来又把许多的个别现象都归结到大法则上,由此便产生出可把握的并使我们的心智获益良多。
“这话不错,”歌德说,“你呢请别因此称赞我;可是这种方法也要求有学生来掌握,但不是一些生活散漫的学生,而是有能力重新把握住根本的学生。在我的颜色学圈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个挺像样的人,但不幸没能坚持走正道,我一不留神他们就偏离出去,不再是眼睛一直盯住要观察的客体,而去追逐某种思想去了。不过只要头脑管用,同时又重在真理的追求,那总还是会干出点名堂来的。”
我们谈到一些教授仍然坚持讲牛顿的颜色理论,不顾已经发现了更好的东西。歌德说:
“这不奇怪,这样的人坚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因为他们靠它生存。他们必须改弦易辙,可这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啊。”
“可是,”我说,“既然他们的学说基础是错误的,他们的实验又怎么能够证明出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