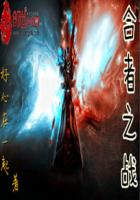此生我仅有的几个心系的人,对他,我依旧是那种道不明晰的情绪。想解开他忧伤的锁,却发现,竟然是自己使之愈悬愈多……让我认为他已死,是因为怕给不了我幸福;放弃了满门的血仇,不计那人亲手刺入他体内的一剑,是因为不愿触及我的恨意。而现下,要离要回,所有的选择他又默然地都交到了我的手中。
私入宫,即便他有方法,也是几多危险的举动。一旦没发现,我或许还有脱身之法,可若是以他的身份……远处的箫声又起,淡然的,却含不尽的情绪。我欠了很多人,也许,欠他最多。柳品笙,若我的心不会因他而痛,那么我们之间可是会轻松几多?又或者,这,本就是一个劫,无从阻断。
早早歇下,一夜间的梦中满是曲声呜然。过去的种种如影片剪辑,一幕幕清晰地过了脑海,一晌难眠。
待次日醒来时,乍睁眼所见的便是刺目的阳光。柳品笙带了我出去,马车一路颠簸,到了一处林子后停下,车夫收了赏钱也被打发了回去。抬头,远远的便隐约可见那红墙的宫城,透尽庄严。
“把这个换上。”柳品笙给了我一个包裹便离了一段距离,立在那替我把风。略好奇地打开,才发现竟是一套宫中太监的衣服。一时想到了小燕子偷扮太监的那副模样,我不由莞尔。看来这古时同现代比也不见得有多少落后,至少这混入宫的伎俩倒是千古未变的。
看了眼负手而立,处在不远处背对着我的那个男人,我的笑意淡淡的,开始解衫。
柔柔的风,把我同他之间的木叶吹地轻响。柳品笙一直没有回头,一直不曾。直到留下胸前的最后一个扣子,我突地“哎呀”了声。
“怎么了?”柳品笙极快地向我这移了几大步,但仍未将视线投来。以背对我,多有焦虑但尴尬地不好回头。而我,偏偏在这一问之下沉默不答。
他心下一横,转过眸来时便已是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但他所见的不是娇莹的玉肌,而是仅留一个扣子,微散领襟的束身宫服。一副嬉笑盈盈丝毫无事的神态迎上,我只见那张脸陡地低郁,便强装正经的嗔道:“方才我只是觉得这个袖子的工艺着实精制的嘛。”言罢,才不紧不缓地将最后一个扣子给扣上。
“走吧。”柳品笙的脸色更黑了,丢下一句话便顾自走去。
再也忍不住,我的笑声几多放肆地扩开。如是,他的步子复大,几近落荒而逃。
莞尔间,我亦跟上。
其实怎不知他内心的烦乱与涩意。若一路宫,他便无法断定我会否再随他离开,随他,去浪迹天涯的罢。在他看来,也许即将迎来的又是一别,却又要他亲手来安排上这次的离别……
但,只有我知道,自己是不会留下的。如果留下了,只会成为玄烨的一个羁绊,一如董鄂之于顺治;如果留下了,便又失去了自由,一如雀鸟困于牢笼……而我,不愿。
柳品笙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宫牌,带着我便从宫门堂而皇之地踏过了那条界线。我不愿意他随去,于是便议定了会面的地点后,各自别过了。
蜿蜒的宫道,虽然曾走过不知道多少次,现下以一个旁人的身份走来,又是另一番感受。
一路向澹烟宫走去,多只遇几个宫女太监,奇怪的只是,从他们的言语间竟然没有丝毫关于我“离世”的消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知道吗?宜贵人了病了。”
原本压低了帽子准备低低头便过去了,但宫女的话入耳,我不由地停在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