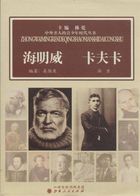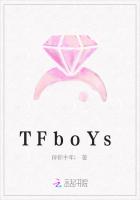就学术文化的繁荣而言,在青少年杜佑生活的时代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成果累累,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后世的总结性政治和文化学术作品,其中许多又是集体力量的产物。例如,开元初,秘书监马怀素、右常侍元行冲等受诏编次四部丛书,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元行冲等上所修《群书四部录》200卷。“藏之内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开元十五年,徐坚等人上《初学记》30卷,稍早,刘知几上《史通》、李延寿上《政典》、柳冲上《姓族录》200卷,开元二年,瞿昙悉达修成《开元占经》120卷,收集《纬书》77种,开元二十四年,张守节以30年功力所撰《史记正义》30卷完成进上,“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义”,“发挥膏肓之辞,思济沧溟之海”,二十七年,徐坚、张说、张九龄等撰、李林甫等进所撰、注《唐六典》30卷。《唐律疏义》的开元修订本、《大唐开元礼》等重要典籍及也在这时完成,及开元、天宝之际刘知几的儿子刘秩写成后来引发杜佑创作《通典》的《政典》35卷,等等。此外,稍早还有如《文思博要》1200卷(高士廉等撰,贞观十五年上)、《群书政要》50卷(魏征等撰)、《艺文类聚》100卷、《北堂书抄》173卷、《文馆词林》1000卷(许敬宗等撰)、《策府》580卷(张大素撰)、《三教珠英》1300卷(员半千、张说等撰)等大型文萃汇编类书编成。《龙城录》作者描写开元天宝藏书盛以上见《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类书类着录。
况说:“开元文籍最备。集贤院所藏至七万卷。学士张说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
就学风和文风而言,这是一个“诸儒争自名家”,风气不断变化的时代。德宗时翰林学士着名文人梁肃,在为对杜佑有影响的玄肃代宗时期着名文人李翰编文集时,曾在所写的文集序中这样评价这一时代的风气变化及李翰在其中的地位: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若乃其气全,其辞辨,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则有左补阙李君。”《新唐书·文艺传序》的作者则结合梁肃的评价,进一步总结写道:“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
玄宗好经术,群臣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梁肃的评价和《新唐书》作者关于玄宗时代文人风气一节的总结,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风雅革浮侈”、“宏茂广波澜”、“其气全,其辞辨,驰骛古今之间”、“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以及“诸儒争自名家”等看法评价,确实点出了当时风气变化的特征和文人学者政治家的心态心理特征。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文化氛围,无疑对杜佑的人生成长道路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时的杜佑,还只是一个不满18岁的年轻人,正处在学习知识、充实自己,感知社会、国家、人生,锻炼思维,培养学问兴趣的过程中。
关于杜佑早年的学习生活,由于史料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我们了解的也不多。比如杜佑受教育的经历,从父亲的官品地位看,开元二十八年到天宝十一年,6岁到18岁这段时间,他应该可以进京城的太学或四门学学习,但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已不得详知。似乎由于父亲在恒州、河西郡等地做官,又在杜佑12岁时去世,这一时期的杜佑基本上是在诸兄的照顾下长大的,可能是跟着诸兄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官场时事,培养学问兴趣,而没有正式进过诸如四门学一类官学学习。当然这只是推测。即使是在家跟着兄长学,以兄长的知识背景而论,他所受到的教育,在基本常识基础知识方面也不会与一般人有太大的不同。
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知识结构、文化素养看,不论杜佑是以什么方式受的教育,他的知识学习、文化素养的培养发展方向,应该是在经史方面,而不是在已经成为时尚的文学才艺方面。这一点,我们从杜佑的自述及不多的史料反映都可以得到印证。例如,杜佑本人在《通典序》中开宗明志便写道:“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以后又在《进通典表》里这样写道:“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及[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复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掇[轻]废。……每叹懵学,莫探政经。”
其中所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仕非游艺,才不及人”,印证以其他一些文献材料,可知应该不是杜佑的自谦之词,而是实情的写照。比如说,学诗作画习字,在唐代已是一般学子要掌握的基本功,也是很多士人进身的资本。但杜佑在这方面似乎不太在行。我们曾遍检《全唐诗》,希望能看到有杜佑的诗收录保留下来,但检索的结果令人遗憾,一首也没有见到。这在“于时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盛唐时代似乎很少见。
也说明杜佑不善作诗,或者可能也写诗,但没有写出过值得称道流传的好诗。唐人笔记还记载了杜佑这样一段佚闻趣事:
进入政界以后、杜佑在扬州做淮南节度使时,曾经向德宗皇帝推荐过一位诗人崔叔清和他的百篇诗作。但诗作进上之后,却得到德宗这样的评价:“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这说明杜佑在学诗作文方面确实是不擅长的,由此导致他的诗文鉴赏力有限。另外,杜佑在做地方官时,曾辟用了不少才学之士,如梁肃、符载、刘禹锡等人。其中又尤其对“材行有余”字又写得好的人尊重有加,如沈传师,史称“(沈既济子)传师字子言,材行有余,能治春秋。工书,有楷法,少为杜佑所器”。这可以说是杜佑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有缺憾的反映。当然杜佑也并不是没有文才,只是比起大家来水平一般而已。例如,对于一些喜欢的文学作品,他也是经常阅读甚至朗诵的。有一条材料就说,杜佑晚年特别喜欢朗读时人杨敬之《华山赋》的句子。以后他的孙子杜牧作《阿房宫赋》,据说就与杜佑经常诵读《华山赋》句子的熏陶有一定关系。《全唐文纪事》引《历代诗话》:“杜牧之《阿房宫赋》壮丽无比。或谓赋取意杨敬之《华山赋》。洪容斋谓:敬之赋内数语,杜佑、李德裕常所诵念,牧乃佑孙,则《阿房宫赋》实模仿杨作也。”
又,杜佑后来作有一篇《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短文,记述请名家指点引流山泉于城南杜曲别墅经过。看其短文,叙事铺陈,状物写景,都于平实中透着生动,还是写得较有文采的。如他写道:“佑此庄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阳。路无崎岖,地复密迩。开池水,积川流,其草树朦胧,岗阜拥抱,在形胜信美,而跻攀莫由。”“于是雉丛莽,呈修篁,级诘屈,步逦迤。
竹径窈窕,藤荫玲珑,胜概益佳,应接不足。登陟忘倦,达于高隅,若处烟霄,顿觉神生。终南之峻岭,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带。”“交清泉于瓛上,遭旱叹而淙注。止则澄澈,动则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泻。悬布垂练,摇曳晴空。”
关键在于志趣、发展方向不在这里。杜佑的志趣是经史学问,是典章制度,是儒家的治国理论。而从《进通典表》“徒怀自强,颇玩坟籍”、“每叹懵学,莫探政经”等句看,杜佑对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也有清楚的认识和考虑。换言之,杜佑对自己的才学气质是有自知之明的,正是这种自知之明使他有所选择,很早就走上了脱离文学时尚,追求经史典籍政治制度、治国之道的学问发展之路。
又例如,杜佑以个人之力完成《通典》写作,曾广征博引,参考使用了大量的政府文件和官私典籍文献材料,他是如何接近这些材料的,有什么途径,我们也不是很了解。推测是两条途径。首先是他入仕以前,长兄信在国子监做官,次兄位先后在中书省和京兆府做官,使他得以有机会有条件接近和看到大量的国家藏书和地方文献资料,为他广泛阅览和积累资料提供了方便。入仕后做地方官、直接参与政治实践,接触官方新旧史籍文献资料特别是时事政策文件就更有条件了。其次是他留心收集,不断积累个人藏书。杜佑喜欢读书,家中藏书很多。杜牧后来在回忆家世、劝教子女时,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弛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经书括根本,史书知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愿尔一柱后,读书日日忙。”“万卷书满堂”,可见杜佑一生,藏书不少。唐人限于书籍制作条件,如出书全凭手写、印刷术刚在产生中、卷轴式装帧形式等等,图书刊行流通并不普及。学者藏书,上万卷者已很少,上万五千卷者有史家蒋系父子,上两万卷者,已知似乎仅有着名史学家韦述和《唐会要》的初作者、大致与佑同时的苏弁、冕父子等少数几家。史称“冕攒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父)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杜佑有书万卷,可以说已进入唐代藏书较多学者之列了。又,以后杜佑的幕僚符载在所作《杜佑写真赞并序》里曾这样形容他的学问之路:“公之为学也,冠冕六籍,衣裳群史,履屡百氏,每读书取其实而不取其华。”谓杜佑治学,是以诸子百家为基础,以诸史为支柱,而居于学问之首统帅思想的则是诸经典籍。这个形容评价,与杜佑自谓“颇玩坟籍”正好呼应,可以说是得其志趣,恰如其分的。
三、“本以门资,幼登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