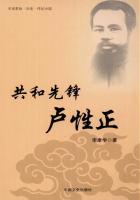不过在这里也应指出一点,杜佑的历史观,有其进步的一面,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也一样可以肯定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其保守、消极的一面,从今天的角度看不可取、应予否定的一面。对此,我们应该予以注意。例如他对少数民族的看法,认为进化慢,野蛮落后,以及由此看法而来提出的处理四夷关系问题的政治主张,就是典型一例。他甚至认为,夷狄之人尚处于中华古代的发展阶段,既落后于又无助于中华的文化发展,因此国家没有必要投入太大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武力征服、战争讨伐、政治控制。强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自身的发展受到损失拖累。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成就巨大但不能长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终以事胡为弊”,即把很大的国力投入到了控制或防御沿边“胡”人即少数民族关系上。秦鉴在前。而唐天宝以后,国家力量的衰弱,安史战争祸乱的酿成,在杜佑看来,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民族关系的处理失策这个问题上,即也是投入过多的国力处理边地民族关系问题,造成力量衰弱,矛盾生发,导致严重的后果。他曾感叹地假设,“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并以秦、唐为鉴,顺着这个思路,得出了“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的结论。
对于杜佑的这种实质是轻视少数民族的大国优越感或文化优越感思想,笔者认为,有其不足之处,是观念落后保守所致,这是考察杜佑思想应该注意的。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看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他考虑民族关系问题,并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而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话的。换言之,杜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思考这个问题时,面对的是唐王朝国力不足、藩镇内患尚无力应付的局面。
因此可以说,国家发展不景气,政治、经济皆困难,是他如此思考问题,从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取“持盈知足”态度、主张立足于防守的主要因素。
二、“盖是人事,岂唯天时”:非天命的社会变革认识论
“天命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界长期以来在思考国家政治、社会变革一类问题时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要义是人事为天命所支配。西周的统治者,用它处理封建政治问题,处理周王室与分封国的关系,维护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共主的地位;秦汉统一以来,转而维护、论证新政治体制的儒家等学派,也用它来解释阐述时代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引导人们对社会变革的认识,论证所在王朝统治的“君权天命”合法性。与天命论同时发展着的则是非天命论的思想潮流。这股潮流在先秦便以荀子、韩非子等人为代表,在魏晋便是无神论的思潮,发展到唐代,就是唐初的反谶纬神学思潮、唐前期刘知己的非天命论无神史观,到唐中期柳宗元为代表的“天论”思潮。
杜佑总的来看是反对“天命”的。杜佑一生,很少讲怪力乱神,从来坚信事在人为。杜佑用来引导自己认识国家政治、社会变革的思想是非天命论的思想。或者用现在的观点去判断,在当时“唯物”与“唯心”的思想阵营里,他的思想,是可以用“唯物主义无神论”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的。他在天人关系的认识方面接受和继承的是先秦以来荀子、韩非等儒-法综合思想家“天人相分”、“交相胜”、“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传统。
他与荀子等人一样,认为有些事的兴衰成败,决定的因素是人事,而不是天命。对于天命论及其衍生思想如“五德终始”运期循环论的说法,特别是东汉谶纬神学的说法,他的态度明显的是不相信。我们翻检《通典》,与天命论关系密切的有关天文历象、阴阳五行、卜筮、灾祥、历数、谶纬一类内容,只有《礼典》有很少的涉及,也是出于材料引用的需要,直接的谈论基本上看不到,即可为证。由此想到他说自己“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也确实不是虚言。另外,如谢保成在《隋唐五代史学》一书中评论指出的,中唐以前的史学界,形成一股冲击神学史观的潮流,否定天命论是其中之一。杜佑前面,唐前期的思想界,魏征、刘知几等人,都是对天命论持批判态度的政治家或学者。其中刘知几着《史通》,对于政治兴衰成败与人事、天命的关系有这样的看法,“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妄褒贬,以之垂戒,不甚惑乎!”刘知几《史通》影响甚着。刘知己的思想,对杜佑的思想一定有影响。
但是,杜佑也不是完全反对天命论。在有些场合,例如国家政治、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上,他也有不加分辨地因袭成说,讲一些天命论观点的地方。给人的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杜佑或者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如此,或者则是思考不彻底,他的思想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不信天命,以积极有为的态度看待人事,相信人事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也不否认天命,例如也认为王朝更替是有应命承运的成分的。是一种非天命论思想为主、杂夹一些天命论思想的矛盾统一体。
杜佑的非天命论思想,可以从他以军事安排为例对人事和天时的因素对古今国家治乱兴衰时势变化的作用影响分析看到反映。
人事在杜佑这里即安邦治国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治行为。“天时”,从杜佑的有关论述看,既指“时机”、形势、客观条件如年成好坏、“因缘际会”,也指“天命”,即“尽人事、听天命”意义的“天命”,以及王朝的统治是否受命于天的“天命”。更多的是这层意义的含义。杜佑在另外的场合,说过“夫圣人之运,莫大乎承天”、“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的话,有助于对他的“天时”说法的理解。另外,荀子是杜佑崇拜的人之一。荀子《天论》的着名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与杜佑的思想有内在的为后者所继承发挥的关系,也有助于对杜佑思想的理解。
在杜佑看来,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治与乱、兴与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些场合,人事的作用影响因素超过了天时的因素,比如说国家的治乱兴衰,关键因素就在于人事,在于合适的制度安排和政治施为。这是古今历史都能证明的。他在《通典·兵典·兵序》写道:“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遍海内,强弱相并。秦氏削平,罢侯置守,历代因袭,委政郡县。缅寻制度可采,唯有汉氏足征。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凑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开元初每岁边费,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以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至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牟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
在这里,杜佑通过分析历代的军事安排得失,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战国强弱兼并,战争不已,与商周分封制的“兵遍海内”军事安排有关,两汉承用郡县制,但采取“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的办法,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是最佳的军事安排。相比之下,唐玄宗时期的做法,重视边防而忽视中央,“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以致于形成“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干弱枝强局面,就显然是失着了,安史之乱,国家由盛转衰,正是这样的军事安排造成的。所谓“地逼则势疑,力牟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顺便指出一点,杜佑在这段话里,还从制度安排得失的角度,对安禄山个人的反叛原因作了解释分析,提出了朝为伊尹、周公,夕成窃国大盗,不过是“形势驱之而至此矣”,而未必是“素蓄凶谋”的看法。这个看法,强调制度安排、形势变化等客观条件对人的思想变化的影响,是见地深刻的看法。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诸多人事因素造成了这次影响深远的战争叛乱。杜佑显然很重视对导致安史之乱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分析,曾先后两次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并在多处场合引用分析这个问题得到的结论。《通典·兵典·兵序》这里是一次。另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是在《通典·食货·轻重》篇的最后,作“论”总结全篇时。这一次,他是从军事安排失着引起经济困难财政危机等连锁反应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的,原因分析之后,再次强调了人事因素影响的重要性。“盖是人事、岂唯天时”这个论断,即在这次讨论时提出。
杜佑在这篇“论”中写道:“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经费之外,常积羡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言利之)道行矣。
割剥为务,歧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