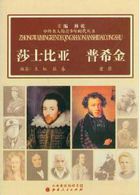以上简述的是德宗以前的宰相制度及其运作情形。德宗时期,决策多依靠身边的内廷亲信如翰林学士等所谓“内相”,外廷虽有宰相但不信任,甚至固持己见,认为“凡相者,必委以政事”,有过命宰相分判尚书六曹庶务、使之成为具体政务管理者而非议大事者的尝试,宰相制度处于徒具其形式状态,或者说基本上未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宪宗即位,励精图治,虽然年轻但也正由于年轻而关注思考帝王为治之道的问题,虚心下问,谋及时相有经验的杜黄裳等人,得出了治国“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哉”的认识,于是一改德宗旧习,恢复了宰相制度,特别是恢复了延英召对议政的制度,使朝廷政治为之一新。史臣蒋系叙述其事并高度评价道:“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觊慕不能释卷。
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治)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以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自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
二、辅政三朝
杜佑自贞元十九年入为相至元和七年致仕退休(当年去世),连辅德、顺、宪三朝,在相位近十年,似乎是当时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不仅如此,他为相时已69岁,退休时已78岁高龄,也是当时宰相中年龄最大、阅历经验最多的一位(仅元和元年去世的宰相贾耽差可比肩),时人也是后来的同事户部侍郎郑余庆已称他为国之元老、朝中“首相”,认为资历、德望无人能比。那么,这三朝政治已如上述虽然风云变化、一波三折,动荡不已,但也复兴有望,正处于中唐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杜佑为相,在这样的时局形势下,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首先是贞元十九年二月初拜相,即上新纂《理道要决》十卷三十三篇,向德宗阐述《通典》的思想内容、表明自己的经济为先、制度建设、重视选举、适时变革、礼乐教化等治国理政观点(详见本书下篇讨论)。
其次是德宗末年,以德高望重的元老身份,在皇位变化、各派势力斗争激烈的形势下平衡各种关系、维持日常朝政,发挥调和矛盾、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德宗在位的最后这两年,地方政局似乎比较平稳,或者说处于维持状况,除了西边与吐蕃的关系比较活跃、吐蕃曾派遣一个54人的使团前来朝贡以外,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内地一些重要地区的节度使如汴州韩弘、浙西韩滉、剑南西川韦皋等人在任已久,控制力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稳定,淮南、陈许、荆南、东都畿、西南黔中等地的地方长官虽有替代,情况也基本平稳。沿边一些地方,如南边的安南观察使、北边的盐州(今定边)、丰州(今河套)、潞州(今长治市),贞元十九年春、夏及次年发生过地方将领逐杀朝廷命官的兵乱,也都很快平定,恢复正常。
朝廷内部的政治形势,却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状态。首先是内廷的宦官势力加强了对中央军队的控制,贞元十九年六月新任命的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与左中尉杨志廉“皆骄纵招权,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其次是东宫的太子系统开始活跃起来。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等人开始与翰林院、御史台的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聚集在一起,“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品评朝士人物,议论时政得失,划分同志,打击异己,如十九年九月,王叔文怀疑刘伯刍等人议论自己,便找借口远贬之。刘伯刍前已提及,因父亲刘(的缘故,曾为杜佑的幕府部下,关系比较密切。复次,外廷的朝臣队伍因德宗的不信任态度和动则贬放不用做法,力量分散,与宦官、东宫官发展势头相比处于无力状态。由于德宗晚年动则猜忌贬放、贬放则久不量移调迁,“十年无赦”的用人政策,这时的朝臣可用的人才很少,新老交替成为问题,在位的人,如宰相高郢、郑珣瑜等人,均年事已高,加上这时宰相制度的不正常,宰相很少面见议政,这时的朝臣,要想夺回正在丧失中的事权优势,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种势力互相对立又互相利用,关系复杂而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亦年事已高的杜佑,这两年的宰相生涯可以说过得并不轻松。大部分时间可以说都用在解决矛盾,处理协调、平衡各派势力的关系上了。而且处境很为难。其他的事几乎来不及做什么。有两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他难于处事的情景。其一是为相不久即勉为其难,参加年轻的改革派文人的节日聚会,与之周旋交往。刘禹锡在一首写于贞元十九年中和节的诗序里提及,这年中和节,诸友照例节日高会,和诗为贺。在座长者首推杜佑。时与会诸人皆有联句,惟独杜佑没有。年龄悬隔,且向来不擅长吟诗为赋,即使如此仍然前往参加年轻人的活动,杜佑此举,意在平衡、维持关系,确实用心良苦。其二是以后王叔文得势时,贾耽、郑珣瑜等宰相皆因政见不同,看不惯改革派的做法而或告病不出,或愤然而退,惟杜佑忍辱负重,仍坚持上朝当政。韩愈《顺宗实录》记其事: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食于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僚无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韦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告以旧事。
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执谊梭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筋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贾耽以疾归第未起,珣瑜又继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等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焉。”
不过,杜佑性格宽和,与人为善,又见多识广,有洞察力和丰富的处世经验,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这样的性格特点和阅历经验帮了他的忙,使他最终能够平衡各种关系,既不得罪东宫系统,又在朝臣中拥有威望,成为德高望重、山雨欲来的形势下遇事压得住阵、可以调和双方、使双方都感到放心,从而稳定政治发展局势的人物。
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贞元年)正月,德宗病卒,时年63岁。杜佑以德高望重摄冢宰,主持为德宗治丧,同时为册使,即主持时患风病“不能言”的太子李诵(顺宗)的即位仪式。
八月,顺宗病甚,自居太上皇,让帝位于太子李纯(宪宗)。宪宗即位四个月后,元和元年正月,46岁的顺宗病卒,杜佑又以宰相元老复摄冢宰,与礼仪使宰相杜黄裳共同主持治丧。同时宪宗“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为司徒,所司备礼册拜,平章事如故”,即仍拜为宰相。短短一年的时间,皇位两度变化,每次都由于杜佑的居中调和压阵而基本上是平稳过渡,虽然各派势力之间有冲突,但总的局势没有失控。这件事,可以说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紧张政治斗争中起到的上述这种调和矛盾、稳定政局的作用。
又,贞元十九年七月,朝廷以关中饥荒为由,罢当年吏部选举和礼部贡举。《唐会要》记其事:“十九年敕:礼部举人,自春以来,久淅时雨,念其旅食京邑,资用屡空。其礼部举人,今年宜权停”。杜佑三月为相,而且应该说是首相,这次七月罢当年贡举,做出这一决策,杜佑不知是否参与了意见。罢一次贡举也许对整个的官吏队伍建设影响不大,但在其事件背后所反映的,却是一种当政者政治态度的变化。当年知贡举事为太常卿高郢。《旧唐书·高郢传》:“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由这段记载看,为时荒而罢贡举,与朝廷执政者对举子有“浮华”、“朋滥”的看法有关。
高郢后与郑珣瑜同时任命拜相,位在杜佑之下。前引高郢本传评价其人其事时提及其位次关系说,“未几,德宗升遐。时同在相位,杜佑以宿旧居上,而韦执谊由朋党专柄。顺宗风恙方甚,枢机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时政事,王叔文谋议,王伾通导,李忠言宣下,韦执谊奉行。珣瑜自受命,忧形颜色,至是以势不可夺,因称疾不起;郢则因循,竟无所发,以至于罢。物论定此为优劣焉。”
其次是在顺宗即位前在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即贞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永贞元年)这两年里,一边以宰相身份处理国事、主持日常财政,保持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一边以看似外表弱让、其实自有主张的态度,洞察局势,关注王叔文、刘禹锡等人的“永贞革新”政治。关于主持日常财政,值得一提的是做了三件事。其一是对度支财政管理系统进行机构整顿、职能调整,把如营缮、燃料、织造染练等物资供应管理一类不属于度支管理范围的职事归政本司,明确度支系统的施行政令、执行政策的宏观管理权与诸司系统的具体事务管理权的职权划分关系。传称:“德宗崩,佑摄冢宰,寻进位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时王叔文为副使,佑虽总统,而权归叔文。叔文败,又奏李巽为副使,颇有所立。顺宗崩,佑复摄冢宰,寻让金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领颇整,公议多之,朝廷允其议。”从“先是”一句看,这次整顿发生在贞元二十一年顺宗退位以前。其二是建议实行新米和籴政策,以避免京师官军总是吃江南陈米现象,即试图改变旧法,调整京粮供应的输送地区范围及输送方式,对转运使的物资运输管理运作系统进行整顿。但此事因百官在议论时意见分歧而未有结果。《旧唐书·顺宗纪》记其事:“贞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子,度支使杜佑奏:太仓见米八十万石,贮来十五年,东渭桥米四十五万石,支诸军皆不悦。今岁丰阜,请权停北河转运,于滨河州县,和籴二百万石,以救农伤之弊。乃下百僚议,议者同异不决而止。”既然无结果,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京师官军吃不上当年和籴新米,每年只好继续吃陈米。其三是把过去盐铁使向皇室内库的进献收归国库正库。这件事,韩愈《顺宗实录》记载发生在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底,“乙丑,停盐铁使进献。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一助经费。其后,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至贞元末,遂月有献焉,谓之月进。至是乃罢。”三月杜佑为“度支并盐铁使”。但把内廷收入收归国库虽有利于国家,却不利于皇室,王叔文等顺宗近臣可能还不敢如此建议。杜佑既通晓故事,善于财政,“雅有会计之名”,又为宰相首相,这个主意,似应记到杜佑的帐上。
对“永贞革新”政治中的改革派人物持外弱内强态度,表现在这样几件事上。首先是先示弱忍让,在总领度支财政期间,容许王叔文代己处理财政事务。韩愈《顺宗实录》:“(三月丙戌)诏曰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检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盐铁使……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骤使重职,人心不服。籍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王叔文)为副以专之。”这件事发生在贞元二十一年三月。所谓“位重而务自全”,容易控制,其实是王叔文的错误判断。笔者的分析,杜佑在对待改革派人物的问题上,可能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持同情态度,而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只不过因为事态发展还在过程之中,前景不甚明了,而采取了示弱以观变的策略,所以才使王叔文等人得出了他务自全而容易控制的印象。实际上,杜佑最初是采取了忍让态度,但忍让的时间并不很长,充其量也只有两个月。
其次是经验丰富、处事自有主张,以在一些问题、事情的处理上不表态、不置可否的办法,冷静对待王叔文对自己的利用拉拢。例如,在早立宪宗为太子问题上,王叔文等人持反对态度,他们不愿意看到另有一个权力中心出现。于是去做杜佑的工作,希望得到支持。但是杜佑没有回应,以不表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使革新人物感到失望。就显得很有经验。史载其事:“叔文欲摇东宫,冀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罢。”
复次是态度逐渐坚决,在局势明了、心中有数之后,利用宦官的不满,渐削改革派权势。表现为同意王叔文为盐铁副使两个月后,先以潘孟阳为盐铁副使代王叔文,使叔文归第,再屡拒王伾的请以叔文为相请求,使王伾也不得不称病退出政坛。在王叔文等人得势的日子里,旧臣及宦官群体逐渐看清了改革派经验不足、不足以当大事的形势,对改革派的态度开始由不信任转向反抗。这年五月,宦官首先发难,奏去王叔文翰林学士职,专任户部侍郎,以断其入内廷议大政之路。此举是第一次打击。韩愈《顺宗实录》写道:“初,叔文(为户侍)欲依前带翰林学士。宦官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
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即无因而至矣。王伾曰诺,即疏请,不从再疏,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学士号。……由此始惧”,不久即以母丧为由告退归第。王叔文告退后,朝廷宣布了以权知户部侍郎潘孟阳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任命。时杜佑仍为总领度支、盐铁、转运事,潘孟阳为副使,应该有杜佑的同意甚至选择安排成分在内。《新唐书·潘孟阳传》“贞元末,王绍以恩悻进,数称孟阳才,权知户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此前,王叔文归第,王伾因预感势头不妙,“日诣中人,并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得,请以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戊子,以礼部侍郎权德舆为户部侍郎、以仓部郎中判度支陈谏为河中少尹,王伾、叔文之党始去。”伾最初每天见劝杜佑而无功,既而“疏三上不报”,诈病归家,杜佑对改革派的不合作态度逐渐坚决起来于此可见。权德舆曾为杜佑部下,有《杜公淮南遗爱碑》之作,对杜佑推崇备至。陈谏为改革派人物,“佑既以宰相不亲事,叔文遂专权,后叔文以母丧还第,佑有所按决。郎中陈谏请须叔文。佑曰:使不可专耶!乃出谏为河中少尹。”权德舆出任户部,改革派陈谏外放河中,意味着此时的朝廷局势,在杜佑为首的态度逐渐坚决的朝臣努力下,已逐步逆转,向着不利于改革派的方向发展。总之,史料反映出,杜佑在永贞革新问题上,立场与改革派人物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立的。他关注改革派党人,更多的可能不是同情,而是观察动静,判断形势,寻找机会,实现年长朝臣群体对朝政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