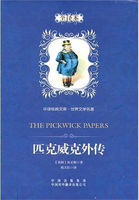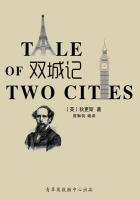楔子
2001年8月的一个晚上,加拿大温哥华市的格利警官在阿比斯特街区例行巡逻。车上的微型电视正在转播纳特贝利体育场里1500米决赛的实况,那儿正举行世界田径锦标赛。格利警官是个田径迷,他一边开车,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屏幕。忽然电话响了,是局里通知他立即赶往邓巴尔街的洛基旅馆。那儿刚打来一个报警电话,是一名女子的微弱声音,话未说完声音就断了,但电话中能听到她微弱的喘息声,很可能这会儿她的生命垂危。格利警官立即关了电视,打开警灯,警车一路怪叫着驶过去,7分钟后在那个旅馆门口停下。
洛基旅馆门面很小,透过玻璃门,看见几个旅客在门厅里闲聊,有的在看田径比赛的实况转播。柜台经理阿瓦迪听见了警笛,紧张地注视着门外。格利匆匆进去,向他出示了警徽,说:
“212号房间有人报警。”
阿瓦迪立即领他上到2楼,格利掏出手枪,侧身敲敲门,没有动静,经理忙用钥匙打开房门。格利警官闪身进去,一眼就看见一名浑身赤裸的黑人女子,半边身子露在床外,电话筒还在床柜半腰晃荡着。屋内有浓烈的血腥气,那女子的下体浸泡在血泊中。格利在卫生间搜索一遍,未发现其他人。他摸摸女子的脉搏,还好,她没有死,便立即让柜台经理唤来救护车。
他用被单裹住女子的身体,发现她的上半身满是伤痕,像是抓伤和咬伤。在喉咙处……竟然是两排深深的牙印!女子送走后,他仔细检查了屋内,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地毯上丢着女子的T恤,皮短裙,黑色的长筒袜和透明的内裤,床柜上放着一百美元。卫生间里的一次性小物品仍保持原状,没人使用过。
柜台经理阿瓦迪告诉他,这名黑人女子是半小时前和一名高个男人一块来的,那个男人10分钟前已走了,“是个黄种人,身高约6英尺2英寸,身材很漂亮,动作富有弹性。他留的名字是麦吉·哈德逊,当然可能不是真名。”
“他是使用信用卡还是现款?”
“现款,是美元。”
这些年温哥华的华人日渐增多,华人黑社会也逐渐在温哥华扎根,这是警方很头痛的事。他问:“这个黄种人是不是华人?”
经理迟疑地摇头:“我不知道,但我看他很像是。”
格利点点头,不再追问。这桩案子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一名不幸的妓女遇见有虐待狂的嫖客,这种情况他不是第一次遇上。3年前,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四星级饭店里,一名颇有身份的嫖客(在此之前,格利常在报上或电视上见到他的名字)把一名妓女咬得遍体鳞伤。另一次则正好相反,一名嫖客央求妓女用长筒丝袜把他的双手捆上,再用皮带狠狠抽他。这些怪癖令人厌恶,但另一个案犯的行为甚至不能用“怪癖”来描述,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兽行。在这个案例中,一家人全部被害,4岁的孩子失踪(后来在下水道里找到她的尸体),女主人被杀死后还被割去乳房,性器官也被割开。3个月后警方抓到凶犯,是一个骨瘦如柴、眼神恍惚的精神病患者。他没有被判刑,只是关到疯人院了。
当警察时间长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案件都能遇上。妻子南希是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对丈夫讲述的这些奇怪行为十分不解,总是皱着眉头问: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格利调侃地说:“这证明达尔文学说是正确的。人是从兽类进化而来的,因此人类的某一部分(或是正常人在某种程度上),仍保存着几百万年前的兽性,在适当的环境下,这些兽性就会复苏。”南希很生气,不许他说这些“亵渎上帝”的话。但格利认为,如果抛开调侃的成分,那么自己说的并不为错。确实,他所了解的很多罪行并不是因为“理智上的邪恶”,而完全是基于“兽性的本能”。
第二天早上他赶到医院,医生告诉他,那名女子早就醒了,伤势并不重,失血也不算太多,主要是因极度惊恐而导致晕厥。格利走进病房时,那名女子斜倚在床头,雪白的毛巾被拥到下巴,脸上还凝结着昨晚的恐惧。听见门响,她惊慌地盯着来人。格利把一个塑料袋递过去,“这是你的衣服和你的100美元。我是警官格利,昨晚是我把你送到医院的。”
黑人女子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谢谢你。”她的声音很低,显得嘶哑干涩。格利在她的床边坐下:“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地址?”
女子低声说:“我叫萨拉,是美国加州人,5天前来加拿大。”
格利点点头,知道这个黑人妓女是那种“候鸟”,随着各国运动员、记者和观众云集温哥华,她们也成群结队飞到这里淘金来了。他问下去,“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请你尽量回忆一下。”
萨拉脸上又浮现出恐惧的表情,脱口喊到:“他……就像是野兽,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是吗?请慢慢讲。”
女子心有余悸地说:“我们是在街头谈好的,那时他满身酒气,答应付我100美元。一到房间,不容我洗浴,他就把我扑到床上,后来……我受不了,央求他放开我,也不要他付钱。那个人忽然暴怒起来,用力扇我的耳光,咬我,掐我的脖子。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格利看看她,“恐怕不是用手掐你,据我看他是用牙齿,昨晚我就在你颈上发现两排牙印。”
女子打个寒战,用手摸摸脖子,把要说的话冻结在喉咙里。格利继续问道:“还是请你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辨认他的身份?”
女子从恐惧中回过神来,回忆道:“他像是个运动员……”
“为什么?”
“他把我扑到床上后,又突然下床打开电视,电视中是田径世锦赛的实况转播。此后他似乎一直拿一只眼睛盯着屏幕。还有,他的身材!完全是运动员的体型,匀称健美,肌肉发达,老实说,当他在街头开始与我搭话时,我还在庆幸今晚的幸运呢。我没想到……”
“他是哪国人?你知道吗?”
萨拉毫不迟疑地说:“中国人。”
“为什么?柜台经理告诉我他是黄种人,但为什么不会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越南人?”
萨拉肯定地说:“他是中国人。他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但在性高潮时说的是中国话。我在旧金山华人区附近长大,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我能听懂。”
“那么,他也有可能是在华人区长大的华裔美国人?”
萨拉犹豫地同意了:“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他似乎是把中国话作为母语。”
“他说的什么?”
“是一些不连贯的单词。什么100米、200米、刘易斯和贝利等。”
“你知道刘易斯和贝利是谁吗?”
萨拉点点头。现在,格利已经不怀疑萨拉所说的“他是个运动员”的结论了。贝利和刘易斯是几年前世界上有名的短跑运动员。只有那些全身心投入田径运动的人,才会在性高潮中还呼唤他们的名字。格利立即想到3天前看到的100米决赛情况。起跑线上的8个运动员,有5名黑人,两名白人,只有一名黄种人,是中国的田延豹。这也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杀入决赛的黄种人选手。田延豹是个老选手,已经35岁,很可能这是他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次拼搏。他在起跑线上来回走动时,格利几乎能触摸到他的紧张。事实证明格利并没有看错。发令枪响后,牙买加的奥利抢跑,裁判鸣枪停止。但是田延豹竟然直跑到50米后才听见第二次鸣枪。等他终于收住脚步,离终点线只有20米了。他目光忧郁,慢慢地走回起跑线,走得如此缓慢,返回的时间足够他跑5次100米了。
那时格利就知道,这位不幸的中国人体力消耗和心理干扰太大,肯定与胜利无缘了。再次各就各位时,田延豹恶狠狠地瞪着那位牙买加选手。很可能,因为这名黑人选手的一次失误,耽误了另一名选手的一生!
那次决赛田延豹是最后一名,而且这还不是不幸的终结。冲过终点线他就栽倒在地上,中国队的队医和教练急忙把他抬下场。刚才他榨尽了最后一滴潜力以求最后一搏,不幸把腿肌拉伤了。
这样,两天后,也就是昨天晚上的200米决赛他不得不弃权。可是按他过去的成绩来看,他在200米比赛中的把握更大一些。在电视中看到这些情况时,格利十分同情和怜悯这个倒霉的中国人,但此刻却不由自主地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他。按体育频道主持人的介绍,田延豹恰是6英尺2英寸的身材,体型十分匀称彪悍。也许,一个在赛场上遭受毁灭的男人会怀着一腔怒火去毁灭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他问萨拉:
“那人大约有多大岁数?面部有什么特征?”
“大约不到30岁,圆脸,短发,至于别的特征……我回忆不起来。”
“你能确定他不足30岁吗?”
萨拉迟疑地摇摇头:“我不能,他没有给我足够的观察时间。”
“他走路是否稍有些瘸拐?”
“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妓女迟疑地说:“他的精神……好像不大正常。他不能控制自己。”
“是吗?”
“他的表情一直很阴沉,说话很少,像是有很重的心事。他带我上车,为我开关车门,完全是一个有教养的绅士,可是后来……”
格利完全同意她的判断。他问:“如果看到他的照片,你能认出来吗?”
“我想可以。”
格利站起身,“那好,你休息吧,我下午再过来。”
他立即动身到温哥华电视台借来了前天晚上决赛的光盘,但在返回途中已经后悔了。冷静地想想,他的推测纯属臆断,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且……即使罪犯真的是那个可怜的中国运动员,他也是在一时的神经崩溃的状态下做出的,很可能这会儿已经后悔了,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何必毁掉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生?
等他迟疑不决地回到医院,那个女人已经失踪。她趁护士不注意,穿上自己的衣裙溜走了,还带走了属于自己的100美元。这不奇怪,哪个人喜欢到警察局抛头露面。于是,格利警官心安理得地还了光盘,把这件事抛到脑后。
3年后,在雅典奥运会,一件震惊世界的连环杀人案披露于世,几乎每家报纸、每家电台都频繁播送着两个死者(一个男人,一个姑娘)的头像。后一个凶手也是中国人,加拿大温哥华市皇家骑警队的格利警官马上在屏幕上认出他。以后,随着雅典一案的逐层剥露,他才知道洛基旅馆那件小小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它的下面,隐藏着让全世界都瞠目的人类剧变。
一
中航波音777客机正飞在北京一雅典的航线上,高度15000米。从舷窗望去,外边是一片淡蓝色的晴空,脚下很远的地方是凝固的云海,云眼中镶嵌着深蓝色的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