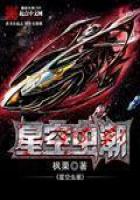概括地说,考试制度和评分制度相结合的教育实践,进一步加强了学科建制对人格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种教育实践“作出经常性的监视和计算评断,对学习者强加一种新的‘规训性’权力”。在此权力的作用下,新的学习者养成自我规训、自我约束的被动式人格,养成“惧怕失败、永远追求奖赏”的人格。第二,通过考试、评分制度的实践,新的学习者发现一种新的知识———权力,即反照权力(mirrorPower),“一种对思想问题经常作出审核、评价、估量的力量”,②由此形成的是主动式的人格。他们是从已有的规训制度中走出来,继而又创立了新的学科和新的规训,生产出新的知识形式。他们自己也成为新的自我,有了新的人格认同。当然,这种人格认同与学科建制又可能成为另一种规训。
①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第184页。
②同上,第47—48页。
总的来说,现代的学科建制已经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不断生产出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格,它们相互依赖,互相支持。一方面,这个制度培养出更多的平民化人格;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助长了这个学科系统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力与作用力。不过,总体上,现代学科建制在中国的确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其消极作用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界也有不少的显现。
二、平民教育与平民化人格
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平民教育运动影响深远。我们对平民教育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陶行知等人的平民教育运动,而应从广义上理解,把那些鼓励教育的平民化、平等化、普及化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实践都视为平民教育。这里,我们简要讨论两个内容,一是平民教育(包括乡村教育)运动与制度;二是男女同校制度,试图说明平民教育和男女同校制度的建设对现代平民化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们先看平民教育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有几支,如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教总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实验等。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积极探索平民教育的制度与理论建设,提出了乡村师范教育建设的具体制度,主张“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①他亲自制订课程计划、学校规划、考试制度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形成了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这是在吸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与认识中国的教育现状和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论创新。②
①《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第646页。
②参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62—309页。
在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经过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得到迅猛发展,使得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在此语境下,教育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掌握关于世界的知识,形成科学的世界观。这样,受教育、学习新知识不再是精英们的权利。平民教育运动把识字教育、学科教育从城市推广到乡村,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这体现教育上的平民化倾向。这种平民化的建制本身是以学习者的人格平等为基础的。因为人格平等,所以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应该均等。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平民化的、普及化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平民化的高尚人格以及各种社会建设的人才。平民教育制度无疑为实现这一教育目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韦伯指出,在教育领域,存在着关于教育目的的争论,一种观点说教育目的是培养有学养的人,即有高尚人格的人;另一种观点说教育培养的是专家,即有专业技术的人。韦伯所说的有学养的人是这样的人:“它主要是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具备那些显得‘有学养’的言行品性,而非为训练人掌握专门技能。‘有学养’的人格是教育的理想目标,它为社会的统治架构所认许,也是成为统治阶层成员的必备社会条件。这种教育志在培养武士,修行者,或文学家;又或者像希腊那些学院派人文学者;又或者像英国的传统绅士。这些统治阶层的资历‘更多’地依据文化素质,而非‘更多’的专门知识。”①韦伯的这一观点多少带有精英主义的趋向。在精英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教育家们主张区分两类精英范畴,一指精神上的高尚品格,二指少数的绅士或统治阶级。他们不赞成后者,赞成前者,主张教育培养的“有学养的人”首先是一种平民化的人格。现代中国的平民教育制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教育家更倾向于把平民教育目的看作是“有学养”的人与专家的结合。像陶行知所说:“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②农夫身手和科学头脑是“专家”的素质,改造社会精神是“有学养”的表现。
①参见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第161—162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第646页。
当时在中国访问的杜威也对平民教育的推动作出过贡献。他在南京讲演“平民主义教育”时谈到,目前中国受教育者大多为有势力的贵族子弟,又偏重男子教育,“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上个人的才智与精神”,养成普通民众“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①平民教育制度试图培养的是平民化的人格,“有知识”、“有才能”展示人格的才智维度,“自动”、“自思”、“自立”展示人格的精神维度,两者的结合是专家与“有学养”的人的结合。
当然,平民化人格的培育最终是为了救国,振兴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这就把人格的培养与国家、民族等宏大主题联系起来。陶行知指出:“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目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必得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赶紧的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要为国家鞠躬尽瘁。”②陶行知的说法强调了平民化人格的社会责任,显示出平民教育制度上意识形态话语的烙印。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平民教育内容是关于男女同校制。男女同校制背后的一个理论假设是把男女视为具有平等人格的人,同视为平民,而不是视为有等级界限的贵族和奴仆。
胡适是倡导男女同校制的一个积极分子。1919年胡适写一篇《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旁听生,以此作为正式招女学生的过渡。在他的建议下,第二年春北大就招女旁听生,几个月后就招收正式女学生。由此,全国范围内的男女同校制度被推广开来。
前面已经说过,制度与人格有多重关系。在男女同校制度上,胡适更多注意到该制度之于人格培养的优点。他认为,这个制度给现代平民化人格建设带来了几个新的观念。
①《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第438、439页。
②《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第56页。
第一,都是“人”的观念。男女同学在一个教室学习、一个操场打球,“只觉得都是同学,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渐渐的把男女的界限消灭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记了”。①男女界限消灭是不可能的,但是,都是“人”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表达了男女人格平等的观念。
第二,男女在交往中学会互相尊重。男女之间的共同学习,“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可以增长女子自重的观念,更可以消灭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顺男子的心理”。②男女同校制度在教育上、生活上、人格上都有益处。在教育上,和女子大学相比,这类大学学科齐全,教授的科目多,这样就扩大了女子教育的范围。在生活上,男女之间共同生活,可以积累生活经验,培养为人处事的能力。在人格上,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可以增进个人道德,养成互相帮助的好习惯。③胡适充分肯定男女同校教育制度对于女子人格的培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男女同校教育制度可以培养自立人格精神。这是该制度的最大好处。这和胡适在妇女人格解放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男女同校制度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制度解放对新人格塑造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现代制度也存在着压抑人格的现象,这在前文关于现代教育制度的讨论中就可见出。这种讨论体现了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性人格危机的反思。这是后启蒙话语,即反思型的现代性话语。与此相对照,上一节讨论传统妇女制度对女性人格的压迫,体现了对现代性制度和平民化人格的呼唤,希冀借新人格的力量制订出一整套新制度来,这种希冀体现的恰恰是启蒙的话语,是学习型的现代性话语。
①《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470页。
②③同上,第471页。
五、人格与法权
本章从社会学的视角探究现代平民化人格的可能性话语。上面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制度与人格的相互作用,着重探讨了传统妇女制度和现代教育制度对于平民化人格塑造的正、反面影响。从制度的角度看人格是社会学视角的一个维度。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维度是法权人格,①或人格与权利的关系。从现代法哲学的视角看,制度是权利的保障。因此,讨论权利与人格的关系是对制度与人格关系探究的深化。
在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讨论人格与权利关系比较详细的要数梁启超。他明确指出:“大抵人生之有权利思想也,天赋之良知也”,“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②可见,他把权利观念纳入人格(品格)的范畴,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人格观念,使“人格”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梁启超借用中国古代儒家的一对概念“仁”和“义”来说明中西方人格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喜欢讲“仁”,西方人喜欢讲“义”。但他对“仁”、“义”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作了自己的解释:“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③一方面,他从权利思想的角度对“仁”提出批评。“仁”在儒家哲学中的本来意义指爱人,指人与人之间结成友爱互助的和谐关系,其意义的侧重点在于:指出人具有共同的人文性与道德性。梁启超认为,“仁”的上述主张存在一个弱点:即抑制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意向。虽然“仁”者爱护他人,不可能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但当他施“仁爱”于他人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自由权利给放弃了。放弃自己权利的结果是“使人格日趋于卑下”。④这是最要命的弱点,也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弱点。在政治上,由“仁”出发,孟子推论出“仁政”的社会治理方案。这向来被儒家奉为理想的治国方略。但是,放眼中国历史,梁启超认为,中国历来仁君少而暴君多,暴君鱼肉百姓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类政治惨剧的理论根源即在于儒家的“仁”学,这是鄙视人的权利的学说。正当性的权利意义的缺失正是儒家“仁”学的病根所在。
①197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通知,废止“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陈忠诚在《关于废除“法权”译名的建议》(《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的文章中,提出废除“法权”译名的观点。笔者不从翻译的角度探讨该词,只是在法律的权利等意义上使用该词,与权利意义大致相当。
②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95、89页。
③④同上,第92页。
另一方面,他在批评“仁”的同时,抬高了“义”的地位。他把“义”与权利思想联系起来,赋予“义”以新的内涵。根据“义”的要求,“我”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与利益,也不允许他人侵害我的权利与利益。尽管这一要求是以消极命令的形式提出来的,但它却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注重之点在于:充分肯定“我”的权利。很显然,梁启超拓展了“义”的解释框架:先秦儒家讲“义”还只是讲道德、伦理之“义”,“义”是道德原则,孔子有“君子义以为上”的断语,而梁启超已经突破此点,开始讲权利之“义”,这使得“义”成为了一个具有现代法权意义的观念。换言之,他用传统儒家的“义”这一概念去接引西方的权利思想。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已经走在了张东荪的前面(张东荪的思想将在下文论述),不仅在“时间上”走在前面,而且在“文化融合工作”上走在前面。
从群己之辨来看,梁启超所说的权利可分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和他在道德观上偏重群体责任的立场、在政治观上主张民族主义的立场一致,他将集体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张灏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他将权利看作是人格的一个基本内容,根源在于他认为一个强壮的国民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国家。”①
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对新民人格特征构成中的权利思想的阐述,已经隐含着一个思考范式的突破,那就是现代中国人不仅仅在道德品格的意义上谈论新民人格,还可以在权利、法权的意义上谈论新民人格。
①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139页。
“五四”时期,在梁启超的“新民”人格思想影响下,也有一些思想家谈论权利问题。例如,陈独秀同样强调人格的权利维度。他称权利为人权。“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①他讲权利主要指平等和自由。平等不仅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主要是指人格之间的平等。自由不仅指言论、信仰等自由,更主要是指人格上的自作主宰、自主处置。而且,他讲平等和自由都是有所谓的。平等针对的是封建等级制度,自由针对的是礼教的束缚。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表征出圣贤人格的没落与平民化人格的现代特征。陈独秀对权利内容的解释比梁启超更加具体。
陈独秀之后,张东荪对权利与人格关系的阐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有专文(《人性与人格》,收入《理性与民主》第三章)加以讨论,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来探讨西方人格观念的本质。尽管此文的历史叙述多于理论阐发,但就人格问题的研究来说,这仍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我们下面的分析主要依据于这篇文章。笔者认为,张东荪此文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辨析了两类人格观念,论析了西方法权人格概念的源起及理论基础,同时也指出了中国人格观念的局限与突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