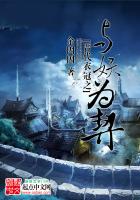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的位置既确定又不确定,可以互相转化。“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②主子和奴才,是一物之两面,有时主子成奴才,有时奴才成主子,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无特操”。表面上,他们起劲地宣传着什么,保存国故、维持公理、讲究仁义等等,其实在背后,他们什么也不信,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讲面子,“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③面子只是装饰的门面,虚有其表,他们本质上毫无道德操守可言。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是从消极意义上阐发平民化人格的个性内涵。
鲁迅不仅从消极意义上,而且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个性原则。他认为,旧的社会秩序由寇盗、奴才等组成,国民劣根性是这种秩序的产物。要彻底改革国民性,就要变革这种旧的社会秩序,就要有新的革新者的努力。鲁迅也称革新者为先驱或觉悟的智识者,他们和寇盗、奴才是两类人,是新社会的新人,是平民化理想人格的典范。鲁迅描述这些先驱的特征是:“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④这段话是鲁迅对于平民化理想人格的经典概括。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①《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88页。
②同上,第542页。
③《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32页。
④《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02页。
第一,平民化理想人格兼具独立和责任两种品格。他不骗人,表明他对他人或群体负责任,待人真诚,与人为善,不会心口不一地做戏,扫荡了寇盗心;不迎合,表明他有独立的人格,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惟命是从,清除了奴才气。有清醒的理智才能去研究,去思索,有坚强的意志才有决断和毅力。清醒的理智与坚强的意志保证了人格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鲁迅关于平民化理想人格中个性原则的设想是对重独立品格与重责任品格两种思路的统一。
第二,平民化理想人格的个性不仅有独立与责任的品格,而且有创造的品格。鲁迅认为理想自我必须是研究型的人才,他们“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富有创造精神。“人必须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唯此自性,即造物主。”①有创造力才显出有个性,有个性的人也必定是有创造性的。
第三,从群体和个体的关系看,鲁迅认为先驱者是有个性的革新者,但也不能脱离大众,始终是群众的一员,也只有融入其中,才能做一番群众的大事业。他不看轻自己,是自尊的表现;他不看轻别人,是尊重他人的表现。自尊与尊他、个体与群体是统一的。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等量齐观,而是有侧重的统一。相对而言,鲁迅倾向于群体对个性发展的辅佐作用。这从他对天才与民众关系的论述中可见出。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②这里讲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有个性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杰出个体的产生离不开集体的帮助和抚育,而且集体必须是一个真实的集体,有了真实的集体才会有天才式的杰出人物。如果说真实集体是泥土的话,那么杰出人物好比是花木。花木的生长如果离了土壤的养育,必然枯萎。“所以土实在比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这里,对集体原则的强调并不导向现代新儒家偏重责任品格的思路,因为它是以个性原则与集体原则统一为基础的。
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51页。
②同上,第166页。
鲁迅在个性原则与集体原则统一基础上讲个性的独立、责任与创造品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的思路。李大钊讲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统一,毛泽东讲个性发展和集体主义的统一,与鲁迅的思路有相近的一面。
“五四”时期,李大钊主张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到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立起来,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往往与个性的自由发展、独立人格、自我实现等内涵联系在一起。以集体主义排拒个人主义,似乎存在忽视和扼杀个性发展的倾向。当时也有不少人心存疑虑。毛泽东在理论上作了一个区分,认为个性发展与个人主义是两回事。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个人主义者追逐个人利益,置个人利益于群体利益之上,只顾一己之私。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①这和个性的发展有较大的距离。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必然包含个性的发展与解放,他们之间具有一致性。刘少奇指出,党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同时,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的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②这就把个性原则从个人主义中剥离出来,在集体主义的框架内承认个性原则。
①《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第139页。
②同上,第135页。
毛泽东不仅讲个性的发展,体现个体的独立品格与个性的量变特征,而且讲个性的解放,体现个体的创造性与个性的质变特征。所以,个性的演变不仅是个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也是个飞跃式的质变过程。 “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②毛泽东肯定个性发展和解放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主题,也是一个完善人格的组成成分。个性的发展和解放正体现了平民化理想人格的独立品格与创造品格的统一。
尽管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区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以前者对抗后者时,充分肯定个性原则,但是,在理论与实践中仍然暴露出忽视个性等局限,这在瞿秋白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有明显体现。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瞿秋白认为个人只是历史(社会)的工具。“每一个伟人不过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里的历史工具。历史的演化有客观的社会关系,做他的原动力,伟人不过在有意无意之间执行一部分的历史使命罢了。”③从理论上看,理想个体的发展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在历史中每个人既是目的又是工具。追求个性的完善、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的内在价值的集中体现。当然,人也有其外在价值即工具价值,成为实现某一个历史任务或别人的工具,把人当作物,具有手段价值。瞿秋白的上述说法割裂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以工具价值遮蔽内在价值,忽视人本身是目的,从而忽视人作为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能起的能动作用。
瞿秋白忽视个人的目的价值,重视个人之于群体的手段价值,因而,他虽然强调个性的发展,但是他更强调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强调个人对群体的服从。也就是说,他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看作是矛盾的,要求用集体主义来克服个人主义,依靠群众来和自己的个人主义作斗争。这一要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其现实的理由。但是,从理论上分析,它有过分突出集体主义而遮蔽个性发展的理论局限,过分突出个人对社会的工具价值而遮蔽个性自由的价值。从平民化理想人格的构成上看,瞿秋白的个性工具论突出了对集体对历史负责的责任品格,甚至存在以责任品格压倒独立与创造品格的致思趋向。这一趋向在3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很长一段时期内,李大钊、毛泽东关于独立个性与创造个性的观点被一度遗忘,给革命实践带来一定的危害。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83。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0页。
③《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感,即个人对社会负责,相对忽视自我责任感,即自己对自己负责。自我责任倒是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得到了肯定。在加强自我责任感方面,传统有较多的资源可供吸取,但是传统讲自我负责侧重在道德修养上,现代人讲自我负责不仅讲道德上的自我约束,更要讲一般行为规范上的自我约束,如在行为上对规则的遵守,思想上对规则的尊重等等。
四、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
在上文对个性的理解上,独立品格与责任品格、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彼此交织着。这里想检讨一下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主流思想家关于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的思想。
关于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的含义,前文已经阐述过,这里不再重复。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的区分为我们深化个性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历史上看,“五四”主流思想家在消极个性的阐发上比梁启超等前一代思想家更深刻,触动面也更广,因此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积极个性的建构方面自然也比前一代思想家更深入。但是,仔细辨析,我们发现“五四”主流思想家对个性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稍加引申。
第一,“五四”主流思想家并没有在理论上对消极个性与积极个性作出审慎区分。对宗法性和奴性的拒斥与积极个性的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至使人常常混淆,并导致对消极个性另一层现代性内涵的忽视。在现代社会,消极个性还意味着个性的展示只能在社会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其发挥是有一定范围制约的。这里我们鉴别出两种消极个性,消极个性1指对社会种种压抑条件的解脱,消极个性2指一种在一定秩序下的有限度的个性。相对而言,陈独秀和胡适等哲学家更关注消极个性1,而相对忽视消极个性2的现代性意蕴。
第二,“五四”主流思想家建构的个性观带有一种理性化的色彩。认识论上理性主体的确立为理性化的个性观念的张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肯认理性主体,而在于他们所谈的理性更多指的是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的工具价值,相对忽视科学理性的目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们所理解的积极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工具理性的色彩。个性的建构主要不是为了自我的尊严和权益,不是为了自我发展与完善,不是立足于人是目的这样的理论基石,而主要是挽救国家危机和救国救民的一种有效手段。像胡适更多是把个性当作反抗传统宗法社会的有利工具,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建立个性价值至上性的理念。个性的设计和建塑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更高的目的,近期的目标是救国和建国,远期的目标是社会大同理想。由此可见,积极个性的彰显多少带有功利性质。
第三,与对科学理性的尊崇相关的是对一种理性力量的崇拜和乐观,因此,“五四”主流思想家所把握的个性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个性观。我们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很浓郁的乐观氛围,大多数个性是属于奋进型、乐观型的。李大钊就指出:“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①胡适也有保持“悲观声浪里的乐观”这样的主张。对个性建构过于乐观,往往认识不到个性的有限性与不完满性,认识不到人其实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如果对个性的欠缺性与易错性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在个性的塑造过程中就不会太过乐观,相反会经常保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当然,现代中国人是有悲观意识的,但这种悲观意识主要不是基于对人性的内在缺陷的认识,而是基于对现实困境的担忧或对未来可能发生种种危机的忧虑。“五四”主流思想家的乐观主义立场多少限制了对个性观的全面把握。
①《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393页。
第四,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看,“五四”时期个性的建构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主体性”范式向“主体间”范式的转换。真正的个性是在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基础上形成的。“五四”主流思想家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仍然在“主体性”范式下谈论个性。例如胡适用“小我”和“大我”之辨来表示个人和社会之辨,他把社会理解成“大我”。从理论上看,不管“大我”还是“小我”,两者都纠缠于“我”,区别只在于“大”“小”(对立或高低)阶位不同,这表明胡适还执着于对个性与社会作“主体性”(“我”)范式的理解,没有进到“主体间”范式的理解。
第五,为把对个性观的讨论引向深入,我们还可以从“在场”与“不在场”的角度作分析。个性的在场与呈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被许多不在场的东西所支撑或构成,可是,这一层意思常常被忽略。某一方面个性的在场(表现于外)往往被定格,被实体化或绝对化。“五四”主流思想家讲个性解放多少有把积极个性塑造绝对化的倾向,这与对科学之道的崇拜是相一致的。他们往往先设想一个理想的、思辨的个性,然后鼓励民众朝这个方向实践。实际上,个性的建构是一个在场不断隐去、不在场不断显现的过程,是一个日益生成的过程。对于主体来说,外在的表面上的差异是可见的,内在的自我之间差异是不可见的,真正的个性生成是一个由外而入内、由内而入外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从实体化的视角来看,个性建构就容易导致个性的固定化、单一化和模式化,遮蔽了个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事实上,“五四”主流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平民化、个性化人格建构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开放的、需要每个时代的思想家不断参与对话的话题。
四、人格与平等、自由
近现代平民化人格理想体现在群己之辨上,不仅表现为人格构成中个性原则与集体原则的关系,而且表现为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