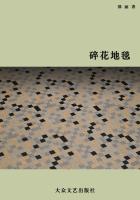我赤裸着躺在新铺就的大毛巾上。翔哥说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不用蜂蜜。翔哥说这一次他为蝶,蝶采蜜。翔哥分开我的双腿,我闭上眼睛,有一种极其温柔亲昵的吻突然间就落在那个地方,地动山摇。有一股源泉突然从那个地方喷发着流出来。
似岩浆的猛烈燃烧。
翔哥用他的嘴婴儿般吸吮着由我的体内流出来的液体。翔哥不断地吞吃着我的体液。一种不可抑制的刺激使我感到虚无缥缈。四周的一切渐渐模糊,我处在另一个世界。我的爱人是我腿下的一只小动物,好比我喜欢的小狗。翔哥吸吮吞吃的声音越大我越兴奋。我要流尽我体内的源泉我愿意流尽我体内的源泉而死去。
颠覆中我记得我发出的那一声尖叫。
我睁开双眼的时候翔哥告诉我他还是第一次令女人在爱抚中丢失。高潮是一种境界,超越高潮是无止境,翔哥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翔哥说最好的比喻就是丢失。
丢失的那一个瞬间我真的死掉过。享受过高潮,享受过丢失,最令我倍感刺激的却是翔哥吞吃我的体液时的感觉。快乐的极限是穿过这个过程而来的。过程是翔哥的技巧,快乐是我的身体达到的目标。我第一次怀疑我或者就是变态的那一种人。我同时怀疑我在骨子里或者就是鄙视男人的女人。我爱翔哥,但是我喜欢翔哥像一只小动物一样地吻我舔我吃我体内排出的液体。我喜欢翔哥满头满身甚至连嘴里都是我体内的液体的那一种味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令我觉得对不起翔哥。我觉得翔哥有一点儿可怜,又爱又怜。我对怜爱一词有一种新的认识。怜爱与男人相拥。再高大再优秀的男人在爱他的女人那里都是怜爱的对象。
我是变态的吗?或者至少可以说我是喜欢变态的。我开始喜欢将翔哥小动物般地玩弄。翔哥不知道他正在塑造另一个我。
流干了体内的液体,我身体轻得像天上的云。我感到我的身体内部有从来没有过的洁净,破戒后的那种坦诚与自然。我知道在做爱这一点上,翔哥是在尽力让我感到性的欢愉,但是我和翔哥只是一对情人,我们不会相伴到黎明。我们之间没有说早安和晚安的机会。说到底,我如成语所说不过被翔哥藏在金屋罢了。我和翔哥的关系在实质上同嫖与被嫖没有太大的区别。
十几年前在大陆文人间产生过热潮的米兰·昆德拉,他的那本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两个世界的拼合,双重曝光。真难相信,穿过浪子托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
我没有法律上的男人没有小孩子,我只要爱而可以什么都不在乎。
身边正搂着我的翔哥有托马斯般的容颜。
为了不要翔哥感到我问这个问题的无聊,我有意若无其事地问翔哥。
我说:“翔哥,你想过你太太的感受吗?”
“喝了茶再聊这个话题或者我们不谈这个话题好不好?”
翔哥起身冲茶,他挑了一只大杯装满茶水。
翔哥说:“让我们用同一只杯子喝茶好了。”
我不动,被子盖到我的肩头,我依然裸着身子。
我对翔哥说:“我除了写小说之外,我不会在这个时间喝茶,我会睡不着觉。”
翔哥一个人喝过茶又躺回我的身边。翔哥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看着天井。
“说出来好像男人常用的小把戏,我正在办协议离婚。”
“是因为我吗?”
“与你没有关系。”
我不再问。我心里很乱,很多东西不知道应该如何整理。如果翔哥当真在办离婚的话,翔哥应该不在乎留在我这里伴我到黎明。要么真的是翔哥的小把戏,要么是翔哥刚刚与他的太太吵过架。
我的沉默无语大概令翔哥误会我是接受了他所说的话。翔哥侧身抱着我。
翔哥说:“你知道每一个男人自童年时就有他理想中的女人。男人头脑中的理想的女人通常接近他的母亲。我喜欢你的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安静苦恼,你紧张克制,你温柔野性,你单纯复杂。你的性格不是形象是一种复杂的味道,多重的。我喜欢你的这种说不清的味道。”
我不知道翔哥在说什么。但是我感知到翔哥真的是在欣赏我在爱我,好像初情悲恋,而我已经二十八岁,我风华正茂。
“算命的说我命中还有一个儿子。我想我和你之间也许会有可能生一个小孩子。”
翔哥说这话的时候我听到窗外有沙沙的雨声。没有例外。在上帝预定的时间和地点,答案如期而至。
“下雨了。”我说。
翔哥钻出被窝开始穿衣服,我送翔哥到大门口。翔哥穿好鞋,突然转过身面对面地看着我。
翔哥用他的手指在我正感到心痛的地方用劲儿戳了一下。
翔哥对我说:“你记住,我一定会送给你一枚戒指,戒指上刻着‘永远的爱人’五个字。”
翔哥戳我的时候,翔哥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所镶着的绿色翠玉冰凉地触到我裸着的胸部。一股寒冷的气流浸透我的全部神经。
我打了一个强烈的哆嗦。
翔哥离去很久我依然站在大门口不动。翔哥戳过的地方痛得像一个伤口,我捂着那个伤口,想起在大学时代读过的霍桑的小说“红字”。放荡女人的象征的那一个红字突然间烙在我的心脏上。对于小说里的那个放荡的女人来说,红字是她纯洁无比的爱情,是男人和女人,是罪与罚,是爱与恶,是通向未来爱情的无止境的黑暗。
我站了很久很久直到我感到鸡皮疙瘩从我的皮肤上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