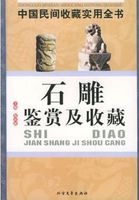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必须高度重视它的可视性。否则,观众在一种颇为自由的、选择性极强的时空条件下进行鉴赏,审美心理一旦受到阻隔,便势必要改换或关闭电视频道。早在1988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率先进行室内剧的创作尝试,成功地拍摄出八集电视剧《家教》(荣获1988年度第九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二等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剧创作以《渴望》(荣获1990年度第十一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为发端,北呼南应,接二连三地在荧屏上出现了《上海一家人》(荣获1991年度第十二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编辑部的故事》(荣获1991年度第十二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半边楼》(荣获1992年度第十三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风雨丽人》(荣获1992年度第十三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等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长篇室内剧。
今天看来,《渴望》虽称不上是艺术精品,但它所引发的全社会性的“《渴望》热”现象却发人深思,其意义66超过了《渴望》本身。个中缘由,大致有三:第一,《渴望》准确地拨动了中国当代观众群体性的审美神经,触及了人民大众审美心理的兴奋点和共鸣区,强烈地感应了社会心理中蕴含的那股强大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自尊自强的热流;第二,《渴望》及时地顺应了中国当代观众对现实主义艺术的深情呼唤,它以真实、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再现了近20年来中国人民所熟悉的时代风云和平凡人物,从而激起了广大观众强烈的精神共鸣;第三,《渴望》还真实地表达了中国当代观众对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以奉献、宽厚、真诚为核心的人间至情的崇尚和追求。它通过屏幕上的刘慧芳、宋大成、罗刚等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塑造呼唤真诚,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迫切愿望,同时也蕴含着对不合国情的五花八门的利己主义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的有力鞭挞。
《上海一家人》和《编辑部的故事》在中国电视剧室内剧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前者的特点是通俗而不媚俗、可视性强而又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内蕴。它在情节的丰富性即“莎士比亚化”的程度上颇见功力,透过对女主人公若男一生在事业与爱情上的追求、遭际的细腻描绘,展示出上海自五卅运动以来至新中国诞生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因此,《上海一家人》不失为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进行中国现代史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编辑部的故事》的题材意义在于填补了中国电视室内系列喜剧的空白,为向来较为乏味和呆板的电视剧人物语言注入了一种新鲜的幽默感,所以播出时令人耳目一新。但须指出,这部系列喜剧各集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上乘之集叫人捧腹之余回味无穷,咀嚼出对人生和社会的新的认识;而下乘之集则有贫嘴过度、失之于油滑之嫌,且主要人物大体上都是一个腔调、一种味道,长此以往,势必要倒观众的胃口。
五、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成功范例
电视剧与文学结缘,一方面固然提高了电视剧这门新崛起的艺术样式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也为文学名著的广泛普及和传播找到了新的现代化媒介。把小说搬上屏幕,显然要比把小说搬上银幕能赢得更多的观众,这里的前提,自然是要“搬”得成功。20世纪80年代,老舍的著名小说《四世同堂》被成功地搬上荧屏,荣获1985年第六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屏幕上,又出现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和《南行记》,标志着中国电视剧在自觉吸收文学营养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这两部作品,均忠实于对文学原著的正确理解,但前者基本循着小说的布局结构,充分发挥高超的文学语言的独特优势并尽量使之转化为成功的视听语言;而后者则打破原著的文学思维结构,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时空优势以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先说《围城》。钱钟书先生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一生所写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所达到的文学品位和审美品位极为引人注目。正如他自己在那部绝妙精深的《谈艺录》里所言,凡艺术品,大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起码的层次,曰“事之法天”,即艺术家对客观世界处于被动效法的状态,追求的是“真”;二是中间的层次,曰“定之胜天”,即艺术家在“事之法天”的基础上进而对客观世界采取主动战胜和超越的态势,注入了主体的一种褒贬鲜明的道德评判,追求的是“善”;三是高级的层次,曰“心之通天”,即艺术家在“事之法天”和“定之胜天”的基础上,再进而以其心灵的感悟与客观世界契然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追求的是包容和沟通了“真”与“善”的“美”。这当然是对艺术品的审美化程度的精辟分析。而《围城》,就不妨看作是钱先生身体力行“心之通天”的美学理论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且看流贯于小说全篇的“魂”,确实乃是作家心灵对人生的一种独特、深刻的体验和感悟———爱情、婚姻、事业乃至人生万事,都如“围城”一般,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逃出来。杨绛女士对小说灵魂的点化,实在是一语中的。整部小说的故事,不过是这种人生感悟得以表达的载体。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电视剧在审美化程度上真正升腾到“心之通天”的精品确实不多,要想成功地把小说《围城》搬上荧屏,缺少胆识和才气都是不行的。10集电视连续剧《围城》,以严谨的手法,整齐的演员阵容,忠实于原著“心之通天”的“魂”,在屏幕上颇为成功地传达出小说对人生的那种独特体验和感悟。尽管小说的结构原则是时间,它往往采取假定的空间,以错综的时间顺序来形成其叙述,而电视的结构原则却是空间,它往往采取假定的时间,靠空间的穿插安排来形成其叙述,但导演黄蜀芹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由文学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化。
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在《从小说到电影》中说:“最电影化的东西和最小说化的东西,除非各自遭到彻底的毁坏,是不可能彼此转换的。”从小说改编成电影如是,从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亦如是。更何况像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型语言大师,将其具有熔西方幽默与东方幽默于一炉的精致的小说语言转化为视听语言,绝非易事。
电视剧《围城》的题材意义还在于,为中国电视剧理应普遍重视文学剧作的基础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众所周知,小说《围城》以其熔西方幽默与东方幽默于一炉的精致文学语言著称于世,电视剧《围城》创作的难度在此,而受益亦在于此。荧屏上的方鸿渐、赵辛楣、孙柔嘉、苏文纨、曹元郎、李梅亭、高松年......一个个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都得益于小说提供的文学基础。电视剧《围城》给中国荧屏带来的人物语言上的机智感与幽默感,与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所具有的人物语言的机智感与幽默感,虽然各有千秋,都具有价值,但究其文化品位而论,却有高低、文野之分。前者的文学性,个性化程度,恐怕都是后者难于比拟和企及的。为着意于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平和精神素质的久远大计,我们理应更着重于前者。
再说《南行记》。如果说,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围城》是汲取文学的戏剧结构和语言艺术营养的成功范例;那么,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南行记》,则主要是汲取文学的诗化意境营养的成功范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艾芜是一位以散文化小说独树一帜的名家。他的小说往往以诗化的意境取胜,这给搬上荧屏带来的特殊难度也就可想而知。导演潘小扬是一位颇具才气的锐意创新的斗士。倘他只是循着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围城》的成功经验走,那么本身缺乏引人入胜的跌宕起伏的戏剧结构的《南行记》恐怕就很难搬上荧屏。可贵的是,他另辟蹊径,大胆打破了小说的原结构,精心设计了三个时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首次南行的时空;60年代“我”再次南行的时空;90年代已87岁高龄的作家艾芜与饰演“我”的演员共同探讨人生的时空。三个时空,交错进行,取得了较好的审美效应。第一,加深了原著所叙故事的历史感,拓展了有限荧屏时空的社会内涵,使历史与现实在荧屏上得到巧妙的沟通;第二,请出文坛宿将艾芜先生作为智慧老人,在荧屏上与当代青年探讨人生的真谛与意义,不仅吸引了文艺界同仁的极大兴趣,而且调动了广大观众的参与感;第三,艺术形式的新颖也给人们以新鲜的审美享受。于是,在两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漂泊奇遇》与《南行记》之后,电视剧《南行记》后发制人,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反响,先后荣获“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的“金熊猫大奖”和“飞天奖”的桂冠。
电视剧《南行记》的又一题材意义,是在营造荧屏意境上的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中国电视剧不少作品在制作上显得粗糙,因而引起观众的不满。《南行记》从摄像、用光到画面、造型,都得到了国内外行家的一致好评。
从《红楼梦》到《水浒》,四部古典文学名著搬上荧屏,堪称我国当代电视文化建设的名垂史册的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这对于普及古典文学名著,功不可没。众所周知,近十余年来,电视文化的崛起,令历史悠长的书籍文化已失去了昔日在文坛的显赫的地位。一部引起轰动性社会效应的电视剧,一播出即可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电视剧《红楼梦》播放后,新华书店的《红楼梦》被抢购一空,甚至使出版社一版再版。《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利用现代化的电子传播媒介,将古典文学名著送进亿万寻常百姓家。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这批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在中华大地乃至东南亚地区刮起了蔚为壮观的“红楼风”“西游热”“三国潮”和“水浒浪”。
其次,这对于提高电视剧的文化品位和美学品位,成效显著。年轻的中国电视剧艺术,亟须向戏剧、电影等姊妹艺术汲取营养,尤须向46流长的文学汲取营养,以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和美学品位。实践证明:将古典文学名著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实乃明智之举。它不仅有效地丰富了年轻的电视剧艺术的文化意蕴,升华了荧屏视听艺术形象的美学品位,而且在实现从文学思维向视听思维转化的过程中,有效地促进了电视剧语言形态的完善及其审美表现能力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电视剧《红楼梦》到《水浒》,确实也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中国电视剧艺术日趋成熟的发展历程。
六、再现历史氛围及其伟人形象的力作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一直是电视剧艺术家们十分关注的领域之一。《努尔哈赤》(荣获1986年度第七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末代皇帝》(荣获1988年度第九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唐明皇》(荣获1992年度第十三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雍正王朝》(荣获1998年度第十九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荣获1990年度第十一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巨人的握手》(荣获1991年度第十二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三等奖)、《豫东之战》(荣获1993年度第十四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雪震》(荣获1994年度第十五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荣获1995年度第十六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上海风暴》(荣获1995年度第十六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二等奖)、《西藏风云》《中国命运的决战》和《开国领袖毛泽东》(均为1999年度获“飞天奖”电视剧)等,便成了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潘霞导演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因其出色地塑造了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性和艺术地展示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而成为了这一创作题材领域里的一个成功范例。
众所周知,要塑造像宋庆龄这样一位当代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熟悉和敬仰的艺术形象,十分不易。因为演员只能通过自己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去努力逼近那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上的真实伟人。这种逼近的程度愈高,则当代观众认同的可能性愈大。这与演员塑造那些艺术虚构的非历史真实人物形象自由驰骋的创作天地相比显然要有限得多。《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的最突出的成就,便是由李羚饰演的宋庆龄,被公认为是近年来荧屏上最出色的“国母”形象。这部作品的主要题材意义在于,一是正确处理了塑造伟人与再现伟人所活动于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了展现伟人的政治气质和色彩与刻画伟人的丰富人性和人情的关系。前几年,文艺理论批评界少数人东施效颦、生搬硬套西方的某些时髦观念,说什么要塑造好历史伟人形象,就必须淡化伟人所活动于其间的历史事件,这样才能表现伟人的“超越历史”;要刻画好历史伟人的丰富人性和人情,就必须淡化乃至消解伟人的政治气质和色彩,这样才能写出伟人的“永恒价值”。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文艺思潮影响下,确有一些为重要历史人物立传的电视剧创作,一度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非历史主义、非政治化倾向。这实质上正是这些作品失败的重要缘由之一。《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以成功的艺术实践,无可辩驳地纠正了这种非历史主义、非政治化的创作倾向。因为屏幕上的“国母”形象,正是通过正面对从辛亥革命到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宋庆龄活跃于其间的重要历史事件(例如四一二事变、西安事变、奉安大典等等)的艺术再现,而成功地塑造出来的;且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女性的那种感人至深的丰富人性和人情,也正恰恰最浓烈地体现在宋庆龄政治气质最坚定、政治色彩最鲜明之处。这两者的辩证、和谐,乃至较为完美的统一,无疑为当前的重要人物传记片创作克服那种危害匪浅的非历史主义非政治化的错误倾向,树起了一种醒目的典范。
1999年,喜逢建国50周年。由杨光6导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王进导演的《中国命运的决战》、翟俊杰导演的《西藏风云》,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开国领袖毛泽东》对丰富的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辨析,从纵向上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总结、尤其是近百年奋斗史的高度来再现新中国开国的伟大历史创举,从横向上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来展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代表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具有一种真实、深厚而又宏大的历史品格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感,也更有力地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形象,由内向外,由神出形,达到了以神似统摄形似的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领袖风采、人格魅力及其对历史的独特而深刻的人生感悟。《中国命运的决战》立意高远,气势宏大,文戏详、武戏略,高层决策详、战场实施略,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败蒋家王朝、抵制美国帝国主义干涉、创建新中国的这一段辉煌历史。这两部作品的成功经验,不仅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而且对同类题材的电影、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