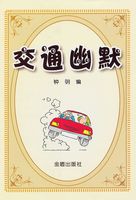余烈雪有病,他的病虽然如今对自己的身体机能没有丝毫影响,可再如何也难活过弱冠,自己老师鬼医的话又怎么可能有错?
如今的他已经十四岁了,可盼的日子也将走到尽头,他也曾自行试图切脉理针,可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找不出自己身上出现的端倪,唯是发现自己心口竟有一块乌云,但奇怪的是那朵乌云竟越来越暗淡,怕是消失不见的那瞬息自己也便魂断红尘。
他有太多不甘与后怕,于是,他逃了,逃下了山,避开了竺茉的微笑,只为争一丝希望。因此做了三年军侍,历经生死洗礼。
而在凉夏遇到的那名算命老道却又令他心生希望,他欲去逆,逆别人的命,可对自己的命却无计可施,况且逆别人的命也没有真正的圆满…
他觉得自己很可笑,可他只能如此。
他沏了口茶,方才抿了两口,书馆的门便开了。
“莫老头,还书喽…”
一个声音在高叫,但声音的主人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脸。
“董忌你能小声点吗?不知道这是国院书馆吗?”
又一个声音闯进书馆,零零碎碎的步履可以听见来人不止一个。
书馆清幽昏黄的明火在微风中徐徐跳动,就宛若暗氲在深邃死寂里的希望之辉令人顿感阳光。
一瞬之隔,书馆里迎来了三五少年,这些少年各个都是受教的学子,这些人打量着书馆里新来的书官而书官也在一一打量着他们。
五个少年各个穿着象征荣耀的学子常服,其中三名披着青衣,两名竟是身着紫袍的国院学子,各个气宇不凡、星目剑眉。
啪!
藏卷厚实地落在桌案上。
董忌满脸鄙夷地盯着余烈雪,他的声音很大震得书馆荡起几声回响,“咿,三年了第一次见到新来的书官,嘿,别说,还挺道貌岸然的,一身红袍该不会是偷了莫老的衣服吧?”
然而他看着余烈雪,余烈雪却并没有应他。
董忌一副不死不休的样子,他的手扶在桌案上,“喂,问你话呢。”
这若是放在战事前线,余烈雪是万难给面前的人任何脸色的,可如今寄人篱下,他也只好陪着笑意道,“公子,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董忌顿觉好笑,他嚣张惯了,但不得不承认余烈雪此番的话他偏爱听,“嘿,不错嘛。不过你怕是不知道,这是在国院,其一公子是万不能说的,其二你大概不知道吧。红袍最初是给见习学子的,或许也只有莫老那样的奇葩才会选择穿这红袍,至于你究竟为何会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该不会是走后门的吧?”
余烈雪万没想到面前这看似魁勇不凡的少年思想却是天马行空。
“怎么?不会说话了?不懂说话了?莫老那小老头还得喊我一声董师兄,你难道不会有样学样?”
“董忌,有完没完?该还的书不会自己去放一放?屁话那么多。”
“切!”董忌看了看身后的那名紫袍,“你管我。”
“我才懒得管你…你不还就别碍着我…”
董忌身后的那名少年一把推开他,朝着余烈雪点头示意,“凝魂册、点络经,我的名字在借录册上有,你找找看,我叫晏飞沙。”
余烈雪对董忌的话并未生出厌意,他果真在录册上找到了前者的名字,两本藏卷。那叫晏飞沙的紫袍学子也不多话,自行去置书,余烈雪也顺势抹去了录册上的记录。
“喂,小子,我都这么随和了你是什么意思?叫你喊句师兄有错?何必搞得像欠你一条命似的?”董忌发现余烈雪比想象中冰冷得多。
余烈雪随意看了看桌案上的藏卷,随即在录册上翻找不多时便也找到了董忌这个名讳,看藏卷完好他也不多话,随意拿起朝着书馆深处走去。
“什么人呐。”
董忌站在书馆门边的桌案旁,若不是后面跟着几个跟班他恨不得把面前的桌案拍烂。
经过一天的劳务余烈雪也逐渐适应了书馆书官的职作,一天光景他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国院学子,有男有女,这些学子或许是因为寂寞惯了,所以也不乏如董忌那样寻他玩笑的存在…
夜风就如多情的浪子,肆意调拨着书馆大门前的花园,百花在劲风中飘扬招展。
一天转瞬即逝,余烈雪成天不曾见到红袍老道,当他回到自己休憩的兑院,却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故。
左晨令人送来的饭食竟已被收刮一空,若不是他推门瞬息踉跄分毫,怕也已然身死魂消。
偌大的兑院显得分外冷寂,自己平时休息的屋舍竟会有人,无名的锋刃在门桅上撕出一道柔光,一道柔美的乌影立在黑暗中。
接着一声冰冷的声音莫名响起,“你是什么人,为何来到我的院落鬼鬼祟祟?若道不出所以然就受死吧!”
昏黑中的言辞就宛若寒冰般刺骨,月辉下的白芒是一柄通身银光的剑,那溢出的流彩就好如一座绵延万丈的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三年的军侍生涯,令余烈雪能够瞬息感觉杀机。
倒不是说那跌宕着神元的力魄存在杀机,只是那份冰冻杀机重重。
余烈雪落在方桌旁显得木讷与迷惘,他从来就不曾感受过如此凌人的怒意,这里是国院也没有谁可以胡乱杀人。
可那柄银光闪烁的剑远比卓衡师弟的剑锐利得多,否则也万不会撕出一道柔光,他知道自己若真无法圆语,怕也就是一剑封喉,身首异处。
怎么说呢,新来的书官?亦或兑院新的主人?这女子怕就是教宫里的教头吧?
这兑院原本的主人既然是教头,那怕是以任何理由都难以搪塞的存在吧。人家是前主自己是后客,说不清也解释不妥。
女人如虎,说的是步入中年的女人。
下山以后余烈雪也见过不少女人,从军之后倒是没有,若柳慈、木素却也不会这般随意视性命于粪土。
听着暗幕里的声音,似乎年纪不大,甚至动听得宛若青莺之音。
余烈雪立在门口,不敢乱动,当然心底还是装着泰然自若的样子道,“我是新来的书官,左副院安排我住在这里。”
银光长剑的主人似乎并不相信,“哼,左晨吗?别拿他来搪塞我,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他分明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凭什么把你安排进来?我又没有说我不再住这?况且,我的东西也完全没有带走。”
柔光下那柄三尺三寸的剑就好像欲舔真血的凶魔,露出扎眼的寒,女子举剑伸出明亮。
忽而,那女人模样的乌影顿了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要骗我。”
她站在暗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门外凝起一丝冰凉的晚风,吹在余烈雪的脊背生起阵阵阴冷。
他有口难辩一阵汗颜,他来到国院,没有见到该见的人,倒是遇见了许多怪异的存在。
“左副院就住艮院,我去寻他与你细说吧。”
只见寒芒一抖,余烈雪身旁的门桅又是落下了一道浓烈的剑痕。
那隐在墨光里的女人却是不耐烦起来,“怎么,想逃?就算是当面对质你也没有资格,你凭什么以为我会给你机会?”
如此残暴?
当然余烈雪也不敢这样想,或许国院教头浑然天成的气质就是如此,想一想董忌他又释然了。学生如此,先生又会好得到哪里出。
他痴痴杵在光下,逆着光迹穿不透屋舍里的昏黑,“当日时间仓促,左大人说这里已经没有人住了,所以才会安排我住进来,你若是不愿意,我大可以现在离开。若你要是觉得我鲁莽了,我向你道歉。”
浮指动,昏暗的屋舍瞬息怦亮又顷刻被掐灭,就好像女子此刻的心情。
“道歉?听你的口气万没有半分道歉的诚意,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反倒成了我的过错?纵然是有人允许你住了,难道就可以肆意妄为吗?又是谁许你动我的书?盖我最喜爱的被褥。”
借着微薄的光,余烈雪只能依稀看到女子朦胧的身容,她披着纱装高挑曼妙,皓齿朱唇黛如远山,明晃晃的蓝眸精妙无双,面额上有一点桃痣,纱装臂膀的位置嵌着一朵金色的小花,那朵花似胜过银剑的耀眼。
他从来就不曾见过如此清新出尘的瑰丽,胸口好似窒息。如果说竺茉是小鸟依人,那面前的女子就是端庄娇柔,谈不上艳丽但却给人一种倾城典雅的感觉,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惶惶不安左右思量,听完女子的话险些喷出一口老血,第一次住进兑院他也感受到了被褥上的一抹芬芳,这一次一脚闯入屋舍,似乎被人拿了个人赃俱获。
余烈雪蹙了蹙眉挪步走向窗扉旁的桌案上,他甚至能够嗅到旧被上曾几何时残留的气息。他也不说话,徐徐收起自己当时随身携带的物品就欲离开,他并非害怕面前女子的绝美,他只是畏惧那柄摄人心魄的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