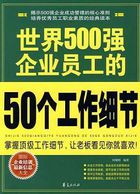逢天下乱世,
审世间腐朽,
择退而保身,
待破而后立。
这是安家的一条组训,也是安家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清末时节,世间已腐朽不堪,战乱四起,安家家主遵古训举族归隐,入深山祖地,修养百年。
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世间似乎走上了一条奇怪的轨道,每次外出而归的安家子孙,无论怎么翻找祖书,也看不到类似的情形,更没有办法去判断世间走向,哪家为王。在那些所谓的枪炮、坦克之类的东西中,安家依然与世间若即若离的保持了几十年的距离。直到某一天安家当时的族长再也按耐不住深山之中的清幽岁月,亲自外出游历之后,发现这天已经变了。
人们穿着或灰或绿的衣裳,高声着“翻身农奴把歌唱”,一辆辆听说叫做汽车的东西在可供十几匹马并行的路上飞驰而去,当安家族长吃掉了最后一块干粮,拿出一些碎银子想买馒头的时候,发现身上没有那种叫做粮票的东西,好心憨厚的老板报了警,安家族长进了号子。
由于是解放初期,这类人似乎并不少见,在安族长阐述了自己的来意后,警察向上级汇报,就这样竟然逐级审查分析,安族长来到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地方,对一些人阐述了自己的来历与来意。
多年战争之后,是个过度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这样一个保有祖先千年文学精髓的大族凭空出现,无疑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义仁,便是将安家带出深山,带向新文明的族长。
就在安义仁以为可以大展身手,振兴安族的时候,那场十年浩劫的到来彻底的摧毁了一个传承千年的荣耀,全族上下老弱妇孺青壮年幼共计千人有余,再次置身于乱世,然而这次来的太过突然,太过猛烈,更何况这是一场针对文化的战争、历史的革命,安家顿时如暴风雨下的一叶小舟,顷刻即将被时代的巨浪吞没湮灭。
在革命的初期,局面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安义仁连夜召集了所有族人,一个类似学校礼堂的地方,平静安详的夜晚,月光透过玻璃窗如轻纱般落下,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大礼堂里面没有开灯,朦胧的月光之中只有礼台那里有一点灯火,只有台上安义仁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盏油灯,微弱的火苗摇曳欲熄,却总是在最后一刻有倔强的再次燃起放出一瞬间的光芒,又再次的慢慢变小,变弱,周而复始仿若希望。
安义仁出神的看着台子上的油灯沉默无语,礼堂下近千人,偶有孩童的一两声啼哭马上就被身边的母亲婶姨安抚下去,除此之外只能听到众人略显紧张或急促的呼吸声,众人都在等,等族长发话,在场的除了孩童没有不明白外面的世道发生了什么,继续下去将要发生什么,所有人都明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人心中需要一个指引,面对每天的折辱,骚扰甚至殴打,他们不敢想下面等着他们的会是什么,身为文人的那一身文心傲骨早已出现裂痕残缺,最近听说在太平湖已经有一位大家孑然殉义了。
一声咳嗽打破了所有人的沉思,安义仁抬起头看着台下,透过面前的烛光慢慢说道。
“祖先在上,不孝子孙安义仁在此请罪。先祖训诫——乱世当隐忍,安义仁虽履族长之责却未尽族长之能,拖累全族上下九百七十七人至如今绝境,罪当死,死后姓名剔除安家族谱,后人提其名讳应唾之,同辈亲友当疏远避之。
然安家自古至今传承一千四百余年,我自四十年前担任族长之位,至今也在世九十于载,安家如今尚属我辈分最高,加之尚在族长之位,今天我要最后一次行族长之权,安家全族听令!”
令字一出,肃然之感弥漫,鸦雀无声,人们虽面有哀色却目光坚毅,一起望向了台上。
“安家上下,即日起……逃,各房各支……逃,隐姓埋名从商、务农、行工职、履仕途皆可,然不得提及与安家有关之过往,不得口诛笔伐当今之事之实,安家传承藏于心而不宣于口,以百姓之心将安家活下去,从此乱世之中安家一脉与尔等毫无瓜葛,不得称安家之后,不得亲安家之后,只要你们在,安家便在!”
最后的两句话,老人眼中含着泪硬声说道,台下众人听闻纷纷下跪,众人之中或强忍哽咽或以泣不成声,哀伤之意弥漫。
“长房一脉听令!”
安义仁收复心思,不理台下族人哀声,严声喊道,靠近最左边的百余人同时抬头望向他们的族长他们的家长。
“长房一脉自今日起,恪守祖训,安家一脉自古至今乃名族望门,如今虽人丁凋零又逢天择之时,但安家之人从来都是来傲骨傍身,安家自古都是挺直了活,站直了死!长房一脉……依然从文育人,以保安家千年传承之铿锵。”
说完这番话,老人紧闭双眼,浑身上下似乎都在颤抖,这一番话似乎用掉了老人所有的力气与勇气,本来精神矍铄的老者瞬间苍老了许多。除了最左边的长房一脉其他各房各支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般,吧嗒吧嗒的掉在地上,那股子委屈的倔劲透过泪珠似要在这不不平的地上砸出个所以然来,在场的人都知道,长房是要扛着安家的荣耀站到最后的一批人,这种行为更类似于殉道等死,最左面一排最前面站着一个小男孩,名叫安全,今年八岁,长房长子长孙。
从此之后,浩劫十年。
十年之后,长房一脉尚存三人,前安家族长安义仁,现安家族长安享,安家直系唯一的后人安全,一年后安义仁见浩劫已去,安家尚存两人,一边大笑一边痛哭就此辞世,享年一百零六岁。
十年之间观一百三十六位后辈相继含冤受辱而死,百年之间观世间战乱三朝更替大族兴衰,他以百岁之躯熬活至今,含恨忍辱苟且而活,只为对祖先有一个交代,去下边面对祖先的时候可以告诉祖先安家直系血脉尚有两人,安家分支旁系尚存一千一百余人,安家尚在……
一个文道之人的一生就此结束,一个名门大族的故事就此结束。
安全二十出头,一所大学的史学老师,对历史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刚刚开放的那几年,他的先进文学思想赢得了学生和学院的认可,破格以毕业生的身份成为大学教师,当时颇受关注,而他选修的考古学也让他在相关领域有了小小的造诣,凭借着过人的才华独特的思想尚未而立便成为知名大学的重点培养对象,直到他认识了那个命中注定的女孩。
乐花名,属于红三代富二代,在那个年代,乐花名的父亲乐建新是最早下海经商的那批人,没有改革开放之前便靠着家里的关系做着一些私下的生意,之后名正言顺的时候,更是如蛰伏千年的巨蟒般吞食了一切可以为他给养的产业。
然而发展几年之后乐家突然销声匿迹,随之而来的各个小型中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滋生而出,当年的那些企业有的消逝于竞争的长河中,有的成为如今世界百强的企业,但都没有乐家的身影,而对于太多的早期下海并成功的商人来说,乐家是一个神话,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神话。
乐花名四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家人去京城郊外的荒地给一些不知名的人上坟,如瓷娃娃般的小女孩对眼前一个个土堆毫无感觉,自己在一旁的树下老实的坐着,看着远处的父亲爷爷等人在那里拜祭着。
回头的时候看到路口走进来几个人,一个发须如雪整理的一丝不苟的老人在前带路步伐稳健,然而目光中似有大坚忍大抱负又好像有大冤屈大悲伤,后面跟着一个嘻嘻哈哈的中年人,一个少年,中年人和少年抬着一个卷着的席子在后面走着,除了少年偶尔空出手抹一把眼睛,另外两个人脸上都没有怎么悲伤的情绪。
尤其中间那个中年人,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反倒有点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小花名被这看似祖孙三代的奇怪组合吸引了,看着他们慢慢的走到自家长辈拜祭的土堆旁边把席子放在地上,看着平时走路生风的爷爷来到那三人组的老者面前,竟然放低身段似在自责着什么,老人拍拍他的肩聊示安慰。
老人身后面的少年不声不语的拿过老人手中的铁铲去一旁边自顾自的挖坑去了,放佛挖过很多次似的,下铲掀土,一铲一铲的没有犹豫和稚嫩,却像带了一股倔强劲般不停的挖着,少年突然停下来。
走到花名爸爸的面前,又看了看不远处停着的汽车,不理周围几个大人诧异的目光,跪了下来,平静的脸庞上还带着泪痕,对着乐建新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的两位老人低头唏嘘,旁边坐在土堆上的安享那笑嘻嘻的神情中也夹杂着深深的苦涩与思念,乐建新看了面前下跪的少年一眼,低头转身就朝汽车走去,车子开走了,小花名看的莫名其妙。
少年起身回头继续挖土,谁也没理,安享懒洋洋的拿着另一只铁铲晃晃悠悠的走向儿子身边,路过安全身边的时候把一只沾满土的手在自己屁股上胡乱拍打了两下,随即拨了拨儿子的头发。
儿子看到是父亲,挤出了一个笑容。
安享砸吧一下嘴,说道“别笑了,比哭都难看。”
安全听闻又转身接着挖坑,父子二人没一会就挖完了六尺见方左右的一个深坑,便坐在那休息。
小花名慢慢的走过去,乐家的老者看到小孙女来了,眉宇之间有了一丝缓和,对这个玲珑剔透的小女孩招招手,小花名跑到爷爷身边,抱着爷爷的腿小脑袋歪看着几步远外,坐着的安家父子。
乐安赐,这个老者的名字,对着安义仁说道。
“这就是我家那孙女,小花这是安爷爷。”
“爷爷好。”
四岁的小女孩没有该有的奶声奶气,声音虽然稚嫩却平静清晰。
安义仁着点头笑着应道,仔细看了看眼前的小女孩,眼睛一亮,忍不住点头赞许。
“好女娃,好女娃。”
小花名没有理会二老的对话,径直来到了安全面前,小女孩看着卷着的席子里面露出了一双不大不小很好看的脚,穿着干干净净的布鞋,小花名转头看着安全问道。
“这是谁?”
“我娘。”
安全头也没抬的答道,小花名又看了看旁边面带笑容同样看着她的安享,转头又问安全。
“那你不哭?”
短暂的沉默后。
“哭过了,我爹说她不用再受气受累了,挺好。”
听罢小花名转身离开了,小小的心中有种难言的酸涩,自己又坐回了不远的大树下面,安全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过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那里低着头嘴里喃喃自语着一句话。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
不多时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