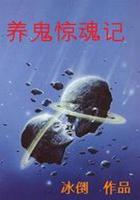在斯皮尔罗斯公司办事处门口,萨特思韦特先生询问奥利弗·曼德斯先生在哪儿,并递上他的名片。
他很快就被引进一间小屋子里。奥利弗正坐写字台前。年轻人站起来跟他握手。
“你好,先生,能来这儿看我。”他说。
他那语气流露出的潜台词是:
“我只能这样说。实际上真他妈烦死人。”
不管怎么说,萨特思韦特先生好不容易才脱掉外衣坐了下来。他若有所思地擤了擤鼻子,一边端详着他的手绢。
“看到今天上午的新闻了吧?”
“你说的是新的金融行情,呃?美元……”
“不是美元。”萨特思韦特先生说,“是死亡。是鲁茅斯的尸检结果。巴宾顿被人毒死了——用的是尼古丁。”
“哦,是这件事。我读了。我们热情的蛋蛋姑娘一定会很开心。她总是坚持说那是谋杀。”“你自己不感兴趣吗?”
“我的兴致不至于这样粗俗。毕竟,谋杀不是……”他耸耸肩头说,“不是什么好玩的。”
“并不全是这样。”萨特思韦特先生说。
“那要看是谁在行凶。如果是你,我相信,就会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去进行谋杀。”
“谢谢你这样说我,奥利弗。”
“说句老实话,亲爱的小伙子,我对你有意制造的事故还没有想得太多。
我认为,警察也一样。”
屋里出现了一阵沉默。有一枝笔掉到了地板上。
奥利弗说:“对不起,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你在梅尔福特修道院缺乏艺术的表演。我感兴趣的倒是你为什么要那样干?”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奥利弗说:“你说警察……怀疑吗?”
萨特思韦特先生点点头。
“那事看起来有点儿让人怀疑,你不这样想吗?”他友善地问道,“不过,你也许会做出最好的解释。”
“我可以解释。”奥利弗慢慢地说,“至于是好是坏,反正我不知道。”
“说出来让我听听。”
停了一会儿,奥利弗说:“我是遵照巴塞罗缪爵土的建议,用我的那种方式到那儿去的。”“什么?”萨特思韦特先生感到很惊讶。
“有点奇怪,是吗?但这是事实。我接到他的一封信,建议我假装出一次事故,并请求修道院接待。他说他不能在信上写下原因,但他会在见面后向我解释清楚。”
“后来他解释了吗?”
“不,他没有……我在宴会前到了那儿。我看见他不是一个人在一处。宴会还没结束他就死了。”
奥利弗显得很疲惫。他的黑眼睛盯着萨特思韦特先生。他似乎在认真观察他的话引起的反应。“你还保存着这封信吗?”“不。我把它撕掉了。”
“真可惜。”萨特思韦特先生冷淡地说,“你没有报告警察吗?”
“没有,一切都……难以置信。”
“是难以置信。”萨特思韦特先生摇摇头。巴塞罗缪爵士到底写过这封信没有?这事看起来非常不合情理。简直是在虚张声势,很不符合这位医生快活的性格。
他抬头看看年轻人。奥利弗还在注视着他。萨特思韦特先生心想,“他在看我是不是已经相信了这个故事。”
他说:“巴塞罗缪爵土对你一点也没说明这样要求的原因吗?”
“一点也没有。”
“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奥利弗不再说话了。“你竟然听从了吩咐。”
奥利弗又一次显得疲惫不堪。
“是的,这事令人精神振奋,能解脱一点我的无聊生活。
坦白地说,我当时很好奇。”
“还有呢?”萨特思韦特先生问道。
“还有呢?你这是什么意思?”
萨特思韦特先生的确不清楚他自己的意思。说这话是出自某种朦胧的本能。
“我是说,”他说,“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跟你有关的?”
停了一会儿,年轻人耸耸肩膀说:“我想我还是统统说了吧。那女人多半不会守口如瓶的。”
萨特思韦特先生疑惑地看着他。
“那是在谋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正在与那位安东尼·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妇女谈话。我从皮夹里拿出笔记本时,有件东西掉落在地上。她把它捡起来递给我。”
“是什么东西呢?”
“不巧得很,她交给我以前看了它一眼。那是有关尼古丁的一张剪报——就是尼古丁多么致命等等。”“你怎么会对这件事发生兴趣?”
“我没有。我想我肯定是什么时候把那张剪报放进了皮包,可是我也忘了。真是狼狈,呃?”
萨特思韦特先生想道:“平淡无奇的故事。”
“我想,”奥利弗继续说道,“她后来去警察局报告了这事儿。”
萨特思韦特先生摇摇头。
“我想她不会。我认为她是一个守口如瓶的女人。她知识广博……”
奥利弗突然俯身向前。
“我是清白的,先生,我绝对清白。”
“我没有说你是有罪的呀。”萨特思韦特先生轻言细语地说。
“但是有人……有人一定认为我有罪。有人已经去警察局告了我。”
萨特思韦特先生摇了摇头。
“没有,没有。”
“那么你今天为什么来我这儿?”
“部分原因是我自己要作调查,”萨特思韦特先生说话时有一点儿浮夸。
“还有部分原因是遵照一位朋友的吩咐。”“什么朋友?”
“赫尔克里·波洛。”
“那个男人!”奥利弗脱口而出,“他已经回到了英国吗?”“是的。”
“他为什么要回来?”
萨特思韦特先生站起身来。
“狗为什么要打猎?”他反问道。
他离开了房子,对自己的反问感到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