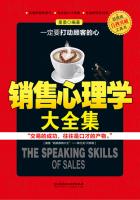1921年3月,我们接手,开始将企业的原则运用于铁路。我们撤掉了设于底特律的管理部门,将行政事宜交由一人负责,给他在货运办公室安排了半张办公桌。法律部门也被一并撤掉——铁路业没理由有那么多诉讼案件。我们摈弃了所有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而员工人数也由2700人精简到1650人。
举目全国,没有哪个例子能像铁路那样更好地说明,服务初衷是怎么被背离的。铁路问题多多,不少专家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对于铁路,人人都是满腹怨言。公众对铁路不满,因为火车票和货运费都太贵了;铁路业的员工不满,他们抱怨薪水微薄,工时过长;铁路所有者也不满,声称投资的钱未得到相应回报。如果一个企业运营良好,应能让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感到满意。如果公众、员工以及所有者,都没能因企业而受益,那么这个企业的运营肯定存在严重的问题。
我完全无意摆出一副铁路方面权威的架子。也许真有铁路方面的权威,但如果铁路知识积累的结果,不过是如今美国铁路提供的那种服务,那我不得不质疑这种知识的有用性。我深信,假如全国铁路都能由积极上进、脚踏实地工作的经营者管理,肯定能做到令人人都满意。但同样我也深知,被一系列环境因素所迫,这些人都退出了管理层。真正懂铁路的人却无法管理运营铁路,这便是引发众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前面关于金融的一章中,我已阐明了恣意借贷集资的危险。如果一个人轻轻松松就能借到钱来掩盖管理不良问题,他自然会选择借贷而不是纠正错误。早在铁路运营之初,操控它的便不是铁路管理人员,而是银行家。因此铁路管理者并没有多少主动权,被迫去借贷。当铁路外债发行量大时,发行浮动利率债券,以及对证券投机,成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不是向公众提供服务。
盈利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用于设施的维修保养。当纯熟的管理带来可观的净收入,足以支付巨额股票红利时,这红利却先被内部投机者利用。他们操控铁路的财务政策,狂炒股票价格,卖出自己所持的股票以获利,再根据信贷额发行债券。当收入降低或被人为抑制时,投机者重新收购股票,一段时间后又炒得股价上涨,然后,他们再把手头的卖出。在美国,没有哪条铁路没经历过至少一次的破产管理。因为铁路的财务收益来自一层又一层的证券发行,而基础又不稳,这样的结构终会倒塌。然后他们接受破产管理,诓骗债券持有人的血汗钱,接着,又开始新一轮这堆金字塔般的游戏。
律师是银行家的天然盟友。对铁路玩的这种把戏,在法律上还需要专家的建议。与银行家一样,律师对企业管理一无所知。他们臆想着,只要企业不违法,或能通过曲解法律来迎合银行家的私利,那企业就是运营良好的了。律师嘛,本就是靠法规条例吃饭的。银行家从管理者手中夺过财政权,委派律师监督,确保铁路以“合法”的形式干违法的勾当。这样,庞大的法律部门便应运而生。铁路运营不以常识为准,不依情况而定,却听命于法律顾问的建议。
组织上下都受法规条例束缚,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纷纷出台各色规章制度。
时至今日,铁路业已被各种名目繁杂的法规制度束缚,举步维艰。内有律师和金融家,外有各种州际委员会,实在难有让管理者发挥主动性的余地。这便是铁路的问题所在:光靠法律难以运营企业。
通过经营底特律-托莱多-艾恩顿铁路,我们有机会证实,摆脱银行家和律师的勾结势力意味着什么。我们买下这条铁路,是因为它妨碍了我们鲁日河工厂的改进计划。我们并不视其为一项投资,或将其作为附属产业,也不是考虑到它的战略位置——似乎在我们接手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这都不是重点。我们当初买下它,是因为它妨碍了我们的发展计划,得对它做点什么。唯一能做的,便是将运用于我们企业每一部门的原则,同样运用于铁路上,将它作为生产性企业来管理。我们并未刻意做什么,也无意将它树立为铁路运营的榜样。虽然,运用原则,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使我们略有盈利,对这条铁路来说,的确前所未有。人们认为它代表了我们所做的变革,是极具革命性的,不适用于普遍的铁路管理。但请记住,这些变革不过是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一小段铁路,与其他大铁路并没什么不同。在工作中我们认识到,只要原则正确,运用于哪个领域则无关宏旨。运用于高地公园大工厂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其他所有厂。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增加到5倍或500倍,都是一样的。说到底,大小只是乘法表的事而已。
底特律-托莱多-艾恩顿铁路的组建是在20多年前。这之后,每隔几年便会经历一次重组。最后一次重组是在1914年。战事爆发,政府控制铁路,打破了这一重组的循环。这条铁路铁轨总长为343英里,拥有52英里的支线,以及45英里其他铁路路线的使用权。它由底特律几乎一路向南,到达俄亥俄河畔的艾恩顿,途经西弗吉尼亚的煤矿区。它还穿过许多铁路干线,从商业角度看,这条铁路理应能盈利。盈利是盈利了,但它似乎只是让银行家赚个盆满钵满。
1913年,这条铁路每英里的净股本达105000美元。而在下一次的破产管理时,这一数额降到了每英里47000美元。我不清楚打着这条铁路的名义,他们之前究竟筹得了多少资本。我只知道,1914年重组时,债券持有人的资产被评估,他们被迫向国库上交了近500万美元——我们购买铁路,付的就是这个数额。
我们为已发行的抵押债券支付60%的现金——虽然在我们购买前,常见的价格只是30%至40%的现金。每支普通股,我们付1美元,优先股则是5美元。考虑到这些债券从未分发过利息,而凭股票分得红利更似遥遥无期,这一价格很是合理了。这条铁路拥有的全部机车包括70个火车头,27节客车车厢,2800节货车车厢。它们的状况都相当糟糕,许多根本无法使用。所有的建筑都肮脏污糟,未经粉刷,摇摇欲坠。路基根本不像个铁路的样子,比一截锈铁好不到哪儿去。维修部门人员过多,却缺乏机器设备。运营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存在着惊人的浪费。此外,管理与行政部门,以及法律部门,也都是人满为患。单是法律部门,一个月的开支便近18000美元。
1921年3月,我们接手,开始将企业的原则运用于铁路。我们撤掉了设于底特律的管理部门,将行政事宜交由一人负责,给他在货运办公室安排了半张办公桌。法律部门也被一并撤掉——铁路业没理由有那么多诉讼案件。我们的人很快便平息了一大堆久而未决的争端,其中有些已拖延多年。如果出现新的争端,他们也很快依据实情将其解决,因此我们每月花在法律事务上的费用很少超过200美元。我们摈弃了所有不必要的账目和繁文缛节,而员工人数也由2700人精简到1650人。遵照我们一贯的原则,除了法定必需的,所有头衔及办公室都一概废除。铁路业通常组织僵化,问题需要经由层层通报,而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有天早上,我早早便去铁路那边看看,发现一辆救援车早已发动,工作人员也都上了车,准备就绪——它像这样“待命”已将近半小时了。不待命令传下来,我们便将车开到事故现场,完成清理——那时我们还没有充分宣扬个人责任观。要摈弃这种“等待命令”的习惯并非易事。起初人们都害怕承担责任。但随着原则的推广运用,他们似乎愈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现在再没人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划死。员工因为一天工作8小时而领报酬,那在这8小时内,他便应该好好工作。假设一名工程师,8小时的工作4小时便完成了,那剩下的4小时,他便可着手其他任何需要做的事。
如果一个人工作超过8小时,并不会有加班费——他下一次可以少工作这些时间,或干脆积起来,积满8小时后一次性带薪休息一天。8小时工作制只是规定一天工作8小时,而不是计算工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