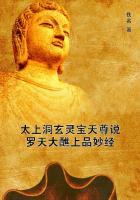随着入夜,匹斯堡的每一条街又被那场从那天起持续不断的大雪完全覆盖。一家家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倒是把街道的一些个角落照亮,但那些没被照亮的角落却显得更黑,而这短短几天里,那些黑暗的角落似乎也越来越多了。在匹斯堡讨生活的人们都在那个半边天被照得通红的夜晚之后,慢慢离开了这座不知见证了中林边境多少故事的城镇,逃回东边。不过,哪怕直到最后一队驻军都走了,匹斯堡西南边的那座监狱也不曾熄灭它每天晚上的灯光,从这儿还归牧族,甚至蛮人管的时候起,匹兹堡监狱便一直没有变化过,好像是这座两百多年来不断发生动荡的城镇里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连墙壁上爬山虎都不曾继续蔓延过。
一丝暖黄的灯光从虚掩的监狱大门里透出来,打到门外的雪地上。早晨难得有人来过的痕迹又立即被大雪盖住了。
“喂,老瞎子,听说中林三省要割回去了是么?”
“你小道消息挺多啊!”被叫做老瞎子的监狱长把身上破烂的羊皮袄裹紧了些,起身锁上了监狱的大门,然后回到一层大厅的桌旁,将桌上那碗刚暖好的烧酒慢慢倒进了自己的喉咙,长长地呼出了一口酒气,然后又把那只旧瓷碗斟满,端着往地下的牢房走去。监狱长身后跟着一个短发的少女,十二三岁的模样,松乱的刘海下面有双不大却清澈的眼睛,眉毛很淡,其余的五官倒是普通得很,若不是身材已经有些玲珑的曲线,被认作男孩子也不会有人意外。好在她早就习惯了监狱长的臭脾气,也知道早上来的几个穿着灰袍的人让老瞎子又多喝了几碗闷酒,便毫不在意他的训斥,双手插在袖中,拖拉着腿随着监狱长一起下了牢房。
老瞎子走在前头,轻车熟路地绕过了楼梯,一直往地牢深处走去。地牢走道倒是被烛火照得通亮,干燥而笔直,站在地牢入口就能将大部分区域一览无余。少女漫无目的地在走道里游荡,时不时走到某个牢房门口向里张望,做个鬼脸,有几个牢房中因为她的作怪传出了一些细微的声响,便逗得她呵呵直笑。
“是要去看那个刚来的家伙?”端着酒的老瞎子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少女于是蹦跳着跟上,笑嘻嘻地问。老瞎子没回答,一直沿着笔直的走道行到了尽头。他的面前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扇门。整座地牢里只有这个牢房的铁门封死了可供探视的窗口,门贴近地面处有些零星的,也不知是否被灰尘堵住的通风孔洞。
监狱长从怀中摸出钥匙,打开铁门,站在后面的少女的眼睛也随着通道里明亮的灯光缓缓透进黑暗的牢房而越来越亮。在确定老瞎子进入牢房后并没有关上铁门,少女低声欢呼了一下,迅速跟进了漆黑的牢房,生怕那位今儿明显心情不佳的监狱长下一秒就反悔了。
牢房里的布置倒是很简单,一把给审讯人坐的椅子,两个烧得火红的炭盆,一张放着简单刑具和纸笔的木桌,刑具种类甚至没一些乡下地主的小地牢里的私货多。唯一起眼的就是牢房中央挂着的那个看不到面容的人。五根成人小臂粗细的铁链锁住那人的四肢与腰腹,将他平行于地面吊起,脖子上又是一根同样粗细的链子巧妙地拴到地面上,让那人能够勉强抬起头,但哪怕腰腹力量再足,也会在成功使上劲前先扭断自己脖子。
多么幸运的人哟!
少女暗想,脸上的笑容一下子绽放开来。
这个被悬挂着的犯人自从白天被运过来后,就没有吭声过,只有那微弱的呼吸表明,这个浑身上下到处是伤的人还是个活物。
老瞎子一步上前,像提酒壶一样提起了犯人的头,少女终于能够勉强看到他的脸,虽然沾满了血污,但还是能分辨出这是一个大不了她几岁的年轻人。年轻的囚犯被老瞎子的动作扯到了胸口的伤,闷哼了一声,却还是没醒过来。
不过接下来老瞎子却松开了手,似乎是站在原地考虑了一下,然后端起酒对躲在他身后不停张望的少女说,“你来”
这两个字让少女愣了一小会儿,虽说近两年她已经代老瞎子审了不少犯人,但那是比较靠外的犯人,至于靠近走廊尽头的几个牢房,她连进都没进去过几次。即便如此,少女现在可是兴奋地很,她小心翼翼地上前端走了老瞎子手中的那碗酒,并递过去了一个确认的眼神。没有回应,但这就是答案了。老瞎子回头走出了牢房,留下了少女一个人,这是匹兹堡城郊监狱里不成文的规定,每次的刑讯官只会有一个人,拷问,笔录,辨别供词的真伪,以及承担犯人的生死。
炭盆里的火安静地跳动着,少女深吸了一口气,慢慢走到昏迷的犯人身前蹲下,轻柔地扶起他的脸,开始细细打量:黑发,眉毛不浓但很直,耳朵背面没有蛮文,没有穿孔,左眼脸上有一道不明显的疤,睁眼的时候应该会因为双眼皮而被掩盖,上唇微薄…下颚处烙着一串数字,看来是个逃出来的兽奴…这些都会被写入最后的审讯档案中,用于最后的评估和归档。短暂的观察后,少女缓缓起身,然后眯着眼睛轻声自语“那么,开始做正事咯”与此同时,那碗在少女手中泛着浓郁香味的酒被缓缓倾倒在囚犯的身上,打湿了他的衣服,他的伤口,他昏迷中那个漆黑的梦。
看着年轻囚犯开始不自觉扭动的身子,和喉咙中不断传出的声音,商心的眼睛渐渐眯得更细。
“幸运的人哟!你好,我叫商心,是你的刑讯官。”
……
剧烈地喘息着,他现在也只能勉强抬起他又开始变得有些昏沉的头,看着少女在边上的一张木桌前,拿笔写着审讯记录。他不知道少女叫什么名字,虽然那个笑起来就会不自觉眯上眼的女孩好像刚刚告知过自己她的名字,但那时才醒过来的他却根本顾不上听少女说了什么。他是被疼醒过来的,很疼,疼到他甚至不愿醒过来,剧烈的刺激让他到现在还会不自觉得抽搐,本来已经凝固的伤口在刚才的挣扎后又崩裂开来,上衣被渗出的血浸湿,贴在伤口,有一种很痒的感觉,却比刚醒过来时的生不如死好太多。
“真是个魔鬼”,他暗暗想着。
商心似乎感受到了从背后飘来的目光,拿起写好的记录,转过来看着重新安静下来的囚犯,用一种意犹未尽的语气对他说:“别这样看着我,等会我核对一下记录,要是有偏差,你还得再被我审一次哦!我可是很专业的!”看到少年明显颤抖了一下,商心愉快地挑了挑她淡淡的眉毛,然后斜靠在桌子上,继续着未完的工作。
“咳咳…姓名:穆桐,16岁,原牧族第二军兽奴,大公历193年8月潜入联盟使团进入匹兹堡…”
“现在是8月了么?”
“诶诶诶,别打断我啊,又看串行了,哪来着?”
“你才刚开始核对…”
“哦,对对对…找到了!话说现在是8月,你也没昏迷多久呀,这就不记得了?也是,第二军三个月前就被削番了,你现在才到匹兹堡,估计逃出来的时候躲地天昏地暗的…额,我们继续…”
核对的时间并不长,原因很简单,这个年轻的囚犯很配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交代的东西实在有些简单,在商心看来,这个年轻的兽奴脑子中就没啥有价值的东西,第一次问话就基本是自己问一句他答一句,核对时除了纠正自己故意说错的一些小细节,连一个眼神交流都没有,商心好几次以为他又昏过去了。
“毕竟只是一个兽奴”商心摸了摸眉毛,觉得有些不痛快,这种感觉只有之前在审讯一些油盐不进的老鸟时才会有。但那些都是刀口舔血几十年的油骨头,而眼前却是个16岁的小子。商心咬着笔头翻了翻记录,估摸着一时半会掏不出啥鲜料了,也就不再打算再折腾这个快死掉的家伙了。
是的,这个年轻人快死了,虽然现在看起来除了虚弱一点外,精神还不错,但那是因为那碗特制的酒激的,等到伤口上的刺激淡了,涌上来的疲劳感会让他体内的暗伤同时发作,尤其是那破损的心脏,要是没有中级以上的神术吊命,能熬过两个晚上就是极限
牢房里一时间只有炭盆里发出的哔啵声。商心最后看了眼叫穆桐的犯人,撇了撇嘴,转身出去了。
“又只有我一个人了么”穆桐其实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体似乎快要到极限了,虽然之前残酷的兽奴生涯也受过无数的伤,但从来没有这次给他的感觉那么糟糕,他隐隐感受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渐渐离开,慢慢带走他的力气与意识,被绑着的他只能不断大口吸着气,把牢房中还未散去的那股特别的酒香吸进肺里,刺痛胸腔里的伤口,不让自己再睡过去。
“又只有我一个人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