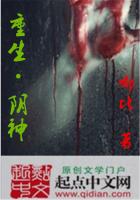唯亭止不住和梁文念叨,说关之茹最近一系列的变化,怎么就突然选择了陈东翰,德晟为嘛不开车了……,她自认为是关之茹的心腹蛔虫,能揣清她的一举一动,而到此她是一点儿也看不明白了。
梁文默语的听。
唯亭纠着脑仁儿揣思没完:“你说人还是逃不了官门世俗,这丫头走一圈儿到了还是跟了陈东翰,门当户对看上去也到合适,不过我怎么觉得有点儿别扭呢?”
半晌,梁文低沉回应一句:“韩坤没死。”
“什么?这是说什么呢!”唯亭惊顿。
梁文点头:“韩坤根本没死,就没这回事。”
唯亭惊诧,睁圆眼睛听他叙述清楚,良久神经凝滞,问:“你怎么会知道?”
这件事关锦赫需要一个帖服可靠的人去办,而听令办事的人正是梁文,至始至终梁文依照他的吩咐搞定事端尾末,除他俩外再无外人知晓。关锦赫自觉做得前后周圆滴水不漏,要把这事永久封存,直到关之茹蛮愤的质问他时,他才知出了纰漏,急怒的质问梁文,问是不是他透了事。
梁文惊讶,矢口否认,到此这俩人揣不清是谁告诉了关之茹?是谁透了口风?
梁文自从办完那事,心里耿耿不畅,憋不住跟他父亲梁晋臣念叨而出,他还记得父亲听完后敲着桌子怒吼:“你这是做的什么事?什么事至于大动干戈的隐匿一个人的名头?这和杀个人有什么不同!怎么能这么诳骗一个人,瞒不住、瞒不住……等到败露那是比背弃更伤人的事!”
梁文揣测难道是父亲透给的关之茹?转念想没可能呀,老爷子身体不健,口齿又不请,每次关之茹来探望他也在身边,也没瞅着有什么言语测漏呀,可梁文还是小心翼翼的开口问了父亲。
梁晋臣皱着老眉头,语齿不清的说:“瞒不住,我说过瞒不住……这世上没什么隐匿一生的事,除非人死了窝在肚肠子里糜烂地底下。”轻儿淡笑:“指不上我费力气,自会有人透了风……这就是来去因果。”哀叹:“凭什么欺骗之茹这孩子,透得好,明白人才做得出,感情这点儿事不需旁人操手,何须那么复杂,人不能总活在葫芦里,得剖个缝见着阳尘,好赖曲折的走一遭经一世,虚假真伪的自然就会明白了。”
唯亭语呆,只睁着眼珠子盯着梁文。
梁文纠思:“不是我父亲,到底是谁?怎么会……。”低语:“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卑鄙,埋汰人的做这事。”
唯亭仍无语。
“想起来心里腌臜,这几年我跟着之茹身边开车,天天面对这人,看她念情着那个人,我心里就没畅快过,这欺侮人的法子根本就不该有。”
唯亭终于说出一句:“你们怎么能……这丫头受刺激了,怪不得……。”
梁文轻叹:“我一直觉得对不住之茹,瞒了她这几年心里就别扭几年,多少次想开口告诉她又忍了回去,唯一安慰的是韩坤那人并不是真情货色,在钱和人面前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钱,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只是没想到之茹专情念旧的死心眼儿,我这心里就更加愧疚,不知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我是背阴里做件龌龊事。”
唯亭眼底一层潮雾,轻抚梁文的手:“俯仰由人,听令做事也是身不由己,你能愧疚也耐得是懂事理的人。”
梁文苦笑:“有个善解人意的人就好受不少,之茹终于知道了,我也算解脱了。”又说:“我一直希望能有个人真心对待之茹,没有为利所图的真心对她,才可以挽回过去的念想,我也就觉得踏实不少。”
“所以你偏袒德晟。”
“是,我是觉得这小子有些性情,能舍出命的担待一个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明白人该懂得就是为了一个情字,那小子羁狂没正行的秉性就是用散堕掩盖性情,用自傲掩盖卑微,就为那点儿自尊不肯说软话的人。”
“哦?你看得这么透,可事实却偏离了方向,之茹却和陈东翰走在了一起。”
梁文无奈:“万事难测,唯有感情最为莫测,也许我想错了,之茹生性敏感多思,经不住伤害,怕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非理性闹性子和陈东翰也是情理中的事,只是陈东翰这人太功利,他关注的点太多,不单纯在关之茹身上,之茹要是跟了他,亏了!”
“不过挺合关锦赫的意,陈东翰像是早就是他的御用女婿了。”
梁文一叹:“商豪名利,什么都需要个筹码,连婚姻也算上,终究还是阿时趋俗,这就是存世规则。”
唯亭无趣一笑:“那个赌局就这么结束了。”
梁文回声:“也许只不过就是个赌局。”忽然转话:“诶,不是限期还没到吗!”
陈东翰几日来心情颇为舒畅,揽到了关之茹往后的前景自不必说,好似已遁入关家门第,再过不久邱山工业区的投标就要开始,这自然信心满满,不在话下。
再一个关之茹换了司机,眼不见那个耨心的德晟,万事顺意,本想着暗地里收拾他一顿,这下也省得多此一举了,依着他现在和关之茹的关系,德晟要是在冒造次,他立可名正言顺的一顿教对。
不多日子进入夏季,柳树轻扬,高阳普照,燥热喧沸。
关之茹与陈东翰同出入各派场合,露脸豪门酒会,相关商体媒介逐出报道,商界巨头关锦赫之女关之茹与惠东实业未来掌门人陈东翰结情眷意,应征了今后珠联璧合的实力趋向。
关之茹常是一身秀雅旗袍,淑饶婉约,面目清丽,淡颜静默,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矜傲,倒也显得气质独韵。陈东翰高体盛宇,威貌堂堂,俩人往一处一站外人眼里绝是门当户对,再合适不过了。
定子和兰芳听闻消息,俩人嘀咕半宿,这关之茹转头就找一个,我们德晟可就插不上手了,多日来德晟闷声不语,也不给关之茹开车了,啥都明白了,这赌局要崩,就是个白扯淡。
嘀咕得越来越气,心急烂肺,我们德晟可是为你关之茹舍命赔本的豁出过命呀,流了那几吨的血呀,咋你个关之茹就没个补偿呢!合着我们德晟一点儿便宜都没沾上,就是你危命时刻挡箭的,就是你当差的司机,合着当个差还有个工薪报酬呢!怎么就没一点人之常情呢?真是商人奸诈,贱人矫情,德晟这么久的工夫算是白费了,不甘呀!
定子揣不清德晟的心思,憋不住问:“关之茹那事就这么结了?赌局那事是不是扯了?”
德晟心烦,懒得搭腔,不言语。
“晟子,这么多时候你都和关之茹耗着,怎么就没捞着一点好?咱付出的代价可不小呀!这人也太不尽人意的了。”
德晟躁郁,脑浆子一派乱乎成泥,就想让那货赶紧闭嘴,可定子越嘀咕越来劲儿。
“晟子,你跟她到底啥程度了?当然我不是说感情,咱和她能动什么感情,没可能的,咱就是对家抛骰子的赌客……我是说那赌局是不是没盼头了?还没到限期呢,还有没有可能的机会?”
德晟不答,定子就越烂嘴:“这要是在钱财上没捞上赢头,在其他方面捞上手也算没白折腾一回。”伸脑袋凑近德晟:“诶,上手了吗?这么久就没个机会?就没干了她玩儿够了找个本儿……。”
“滚!”德晟瞪眼爆出一口。
定子紧忙闭嘴,轻声嘟囔:“我、我就是为你不值。”
撇开那话头不说了,烂嘴不停的又扯别的,说起失恋者联盟,说起初开这事业的大雄大志,又说到至今的萧条,一切都不在他的设想,混沌了他的志向,萎靡了他的意志,抱怨拯救众生的大义之举如何艰难,生意如何平淡,本钱都找补不回来,更别提发财了,只落下聊以糊口维持生计。
德晟扶额自叹:失恋者联盟像就是为那个赌局而生,就为了设在砖塔巷闹着动静等待那个人推开这扇门……
德晟平淡的回一句:“走到日子就算结了。”
定子懵晕,什么日子?什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