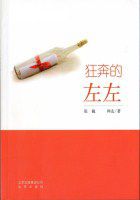“再这么下去可不行,艾尔凯!快叫一个女仆来,飓风对玻璃压得太厉害,必须把护窗板关上!”
太太一叫,女仆便跑到院子中,从屋里看得见她的裙子如何给风吹得乱飘乱飞。可她刚一取掉挂钩,狂风就从她手里刮掉了护窗板,把它猛地一下砸在窗户上,好几块玻璃都碎了,飞溅到了房里,一支蜡烛随即被风刮灭。豪克不得不亲自跑出去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窗板一扇一扇关上。当他们拉开门回房来时,一股风随之窜入,壁橱里的杯盘刀叉叮叮当当响成了一片。在他们头上,屋梁和椽子也颤抖着发出嘎嘎嘎的声音,仿佛狂风要揭掉屋顶似的。可是豪克没有回房里来,艾尔凯听见他走过晒坝,朝马厩去了。
“白马!白马,约翰!快点!”——艾尔凯听见丈夫喊。随后,他走进屋来,头发蓬乱,灰色的眼睛却炯炯发光。“风向转了!”他嚷道,“转成西北风了!狂潮即将到来。这不是一般的暴风——这样的飓风咱们还没经历过!”
艾尔凯脸色苍白:“你还要到坝上去吗?”
豪克抓住她的双手,痉挛地握在自己手中,说:“我必须去,艾尔凯。”
她慢慢抬起黑色的眼睛来望着丈夫,两人相互注视了几秒钟,但这几秒钟叫人感觉长得没完没了。
“是的,豪克,”妻子说,“我明白,你必须去。”这当儿,门外响起了马蹄声,艾尔凯一下搂住丈夫的脖子,在一瞬间仿佛她再也不能放开他似的,但也仅仅是一瞬间。“这是对咱俩的考验!”豪克说,“你们在这儿是安全的,洪水还从来没有哪次涨到过这幢房子跟前。祈祷祈祷上帝,求他也与我在一起!”豪克穿好斗篷。艾尔凯取出一条围巾来,仔仔细细替他围在脖子上。看上去她还想说什么,然而颤抖的嘴唇不听使唤。白马在门外引颈长嘶,在狂风的吼叫中听起来就如声声号角。艾尔凯送丈夫走到院子里,那株老梣树嘎吱嘎吱叫着,快要散架了一样。“上马吧,东家!”长工说,“这畜生像是疯了,缰绳差点儿没挣断!”豪克拥抱了妻子,最后说:
“太阳升起时我就回来啦!”说完他便跃上了马背。只见那白马高举前蹄直立起来,然后就像一匹战马冲向战场似的驮着它的骑手奔下土坡,消失在了黑夜和呼啸的狂风中。“爸爸!爸爸,我的爸爸!”——豪克听见身后传来孩子哭叫的声音。小温凯在黑暗中追着他跑了一百来步,就让土堆给绊倒在了地上。长工伊文·约翰把哭叫着的孩子抱回母亲身边,艾尔凯身子靠在树干上,失魂落魄地瞪着吞没了她丈夫的黑夜。在她头上,树枝让风刮得哗哗哗响。蓦地,一刹那间,风也不再狂吼,海也不再喧嚣,使她浑身不由得一惊。她觉得,仿佛一切都是为了毁掉她的丈夫,一当把他抓住了,便立刻无声无息。她的膝头哆哆嗦嗦,头发散开了,在风中飘来飘去。
“孩子,太太!”长工大声对她喊,“抱住了啊!”同时把小温凯塞进她怀里去。
“孩子?——啊,我把你给忘了,温凯!”她叫道,“上帝宽恕我吧!”同时慈爱地把孩子紧紧搂在胸前,双膝跪到地上,“上帝啊,还有你——耶稣,求求你们,别让我和我的孩子成为寡妇和孤儿吧!仁慈的主啊,请你保护他,要知道只有你和我,才真正了解他啊!”
风暴又起来了。风在怒吼,雷在轰鸣,仿佛整个世界全要在轰隆隆的巨响中垮掉一样。
“进去吧,太太!”约翰劝她,“来!”他边说边扶她俩从地上站起,领着她们回到房中。
堤长豪克·海因骑着他的白马直奔大堤。因为连日大雨没有停过,狭窄的小路已经又滑又软。然而烂泥黏土似乎都阻挡不了白马飞速前进,它仍像急驰在夏天结实的平地上一般跑得飞快。乌云在空中疯狂奔逐,下边的沼泽地黑影憧憧,变成了一片潜藏着不安与恐怖的黑色荒漠,堤外的海啸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可怕,仿佛就要把其他声音统统吞没似的。
“快,白马!”豪克大喝,“这是咱俩最糟糕的一次出行!”突然间,马蹄下迸出一声垂死的惨叫。他勒住缰绳,调头一看,只见一群嘎嘎嘎怪叫着的白色海鸥,一半是飞,一半是受着狂风的驱使,紧贴地面从他旁边窜过,想在陆地上找一个藏身之所。它们中的一只,让乌云之间暂时透过来的一束月光照着,躺在路边,已经被马蹄踩死。骑手恍惚看见,它的脖子上有一条红绸带在轻轻飘动。
“克劳斯!可怜的克劳斯!”豪克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这是他女儿的那只鸟儿吗?它认出了白马和骑手,因而想来寻求他们的保护吗?——这些问题豪克想不清楚。“上!”他又喊道。白马已举起前蹄,准备重新狂奔。可谁知就在这一瞬间,风暴突然停了,四周变得死一般沉寂。这沉寂不过维持了一秒钟,接着狂风便更凶猛地吹刮起来。然而也就在这一秒钟里,豪克耳畔蓦地听见嘈杂的人声和惊慌的狗吠声。他回头一望村子,只见在偷射下来的月光里,一座座土丘上,一幢幢住宅前,人们正在已经装得高高的马车旁边忙来忙去,同时,他看见另一些马车已飞快地驶向高地上的教堂村。一些刚从温暖的厩舍赶出来的牛羊的叫声,也传到了他耳朵里。“感谢上帝!他们在救自己的牲口!”他心里说,可接着,他惊恐地叫出声来:“啊,我的老婆!啊,我的孩子!——不,不,洪水是淹不到咱们坡上去了!”
但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一瞬间,只像一个幻影似的打他眼前一闪而过。一阵可怕的飓风号叫着从海上扑来,迎着它,白马和骑手沿着陡窄的便道直冲上大坝。到了上面,豪克猛地勒住马。可大海在哪儿?耶维尔斯岛在哪儿?堤外的海岸又在哪儿啊?——在他眼前唯有一道高过一道的浪峰,一条深似一条的波谷,争先恐后,前推后拥,向着夜空狂啸,向着陆地猛冲!浪峰的尖头戴着白色的王冠,身体发出千百种怪声,恰似世间的野兽全集合在一起齐声嗥叫。白马用前蹄蹴踢着地面,鼻孔冲喧腾的大海喷着粗气。豪克呢,却突然感到,好像此时此地,人类的力量已化为乌有,黑夜、死亡、毁灭必将统治一切。
他定了定神,想起这是在涨大潮啦,只不过他自己还从未见过它来势如此凶猛罢了。他的老婆,他的孩子,她们都安安稳稳地坐在高高的土丘上,待在自己坚固的房子里。可是他的堤坝——他胸中突然充满了自豪——大伙儿所谓的豪克·海因大堤,眼下它就会向世人证明,堤坝究竟该怎样建造才是!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来到新旧堤坝衔接的地方,发现他派在这儿护堤的那么多人这时一个都不见了!他再往北朝旧堤上看,那儿本也安排了少数人守着,同样一个人影没有。他骑着马走了一段,仍然碰不见任何人,只有风暴的呼啸和大海的咆哮,震得他头脑发昏。他勒转马头,回到新旧堤坝衔接处,视线扫过新堤的外侧。很明显,这儿的波浪要缓慢得多,也不那么凶猛,仿佛面前是另一个大海。
“它会站住的!”豪克低声自语,同时好像笑了。可是当他的目光继续沿着新堤移动,他再也笑不起来:在西北角上,挤着拥着,不停地蠕动着的,那是什么?——毫无疑问,那是一大堆人!可他们想在那儿干吗呢?对他的新堤干什么呢?——不等脑子转完,他已猛刺胯下的坐骑,白马便驮着他疾驰而去。飓风是从侧面刮来的,几次差点儿把他连人带马掀进围地,只不过马和骑手都很有经验,知道如何前进。豪克已经看清楚,有好几十个人在一起拼命干活儿,而且已在新堤上挖出了一道豁口。他猛地一下勒住马,大喝道:“住手!住手!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鬼名堂!”堤长的突然出现,吓得众人停住了手中的工具。由于顺风,他喊的话也给他们听见了。外边的风非常厉害,人经常被刮得踉踉跄跄的,所以工人们全紧紧挤在一起,他们全站在豪克左边,答话的声音给风一刮就散了,他只看见有几个人在拼命地向他打手势,却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想告诉他什么。他的眼睛迅速地打量了一下那道已挖成的豁口,然后再看了看脚下的水位。尽管这儿的堤坡平缓,潮水也涨得离坝顶不远了,激溅起来的水花已经淋到白马和骑手的身上。只需再干十分钟——他看得分明——潮水就会涌过豁口,将这片新围地,豪克·海因围地整个淹没!堤长向一名工人招招手,让他走到马前。“喏,快讲,你们到底想在这儿干什么?”他大声问工人。这人同样拉大嗓门儿冲他喊道:“我们奉命掘开新堤,先生,以免旧堤崩掉!”“你们奉命什么?”
“掘——开——新——堤!”“把围地淹掉?——哪个魔鬼叫你们这样干的?”
“不,先生,不是魔鬼。奥勒·彼得斯委员来过,是他命令咱们干的!”豪克气得眼睛里喷出火来。“你们认识我吗?”他吼道,“有我在,奥勒就没资格发任何命令!快给我离开,回到我派你们的岗位上去!”众人迟疑着,他便驱马冲进他们中间:“快给我滚,要不叫你们见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