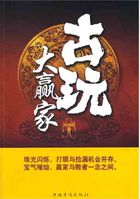接下来的那些日子尽管阳光明媚,对我来说却是黯淡灰暗的。幸好还有哥哥让我替他设计一幢管理大楼的事,把我忙得气都喘不过来。须知要把那些实用方面的要求与我不肯忽视的艺术价值结合起来,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他常常抓起铅笔,在我那绘得十分精美的设计图中央狠心地来上一道,我们争论来,争论去,最后甚至只好把两位女士叫出来作评判。
记得是燕妮走后的第四天,我坐在自己房里干这件工作。可这一天却干得很不顺利,我归罪于手里那支可怜的鸭嘴笔,便站起来,准备去提箱里另取一支。我将箱里的衣服抱了出来,这时便拾到一个小小的纸包。上面写着“燕妮留赠”几个字,包里裹着前不久我才套在她指头上的那枚玳瑁戒指,戒指上还缠着一束黑缎子似的秀发。我的第一感觉是又惊又喜,仿佛自己又到了爱人身边,可紧接着,便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涌上心头。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细看,然而不见任何一点儿字迹或者记号。我企图继续工作,但是不成,便走到下边的客厅里,在那儿碰见哥哥和嫂子正在谈燕妮。
“瞧瞧她那双眼睛!”我进门时听见格蕾特说。她丈夫似乎故意与她唱反调,用玩笑的口吻说:“怎么,你不是认为这双带野性的眼睛不漂亮吗?”“你说带野性!而且不漂亮?——诚然,你是对的,它们太漂亮啦,以至于遭到了别人的非议。而这个嘛……”她欲言又止,同时抬起头来望着自己魁梧的丈夫,嘴角挂着怜悯的笑意。
“这个怎么样,格蕾特?”“并非别的什么,而是反抗的开始。坦白说吧,汉斯,你已经感觉到她对你是危险的了!”
“不错,如果我没有你的话!”“噢,有我也一样。”他笑起来,把双手伸给妻子。
“快抓牢它们,”他说,“这样,再漂亮的魔鬼也别想引诱我了。”然而他妻子不信这一套。“魔鬼在你们男人自己心里!”她说,“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现在总爱找那纯洁无邪的孩子的碴儿,过去你对她可是够有骑士风度的呀?”“过去是的,格蕾特,不错。但她现在变啦!”他沉吟了一会儿,“我几乎说不出口来,可事情千真万确:她身上的商人女儿的本性表现出来了——她已经变得非常之悭吝。”
“悭吝!”格蕾特失声道,“这太可悲了!燕妮,她从前在寄宿学校只是受到严令禁止,才没有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扒下来送人!”
“她如今不再白送人衣服了,”我哥哥回答,“她把它们卖给收破烂儿的,而且我要告诉你,她讨起价来一点儿不含糊。”
我留心地倾听着,没有介入谈话,但听到最后一句突然大吃一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迅速下定决心。
“可以用一用你的马吗,汉斯?”我问。“当然可以,你想上哪儿去?”“进城。”
格蕾特走到了我跟前。
“怎么,已经忍耐不下去了吗,阿弗雷德?”“不,格蕾特!”“喏,代我问候燕妮。或者,把她给咱们领回来更好些!”
我什么也没再讲,只是立即跃上马鞍,一个钟头以后就到了城里,到了燕妮父亲的新居所在的那条街上。这条街我很熟悉,很容易就找到他们的宅子,在几次拉铃以后,漂亮的宅门开了。一个老妇人走出来,我向她打听燕妮小姐,她干巴巴地回答:
“小姐不在这里。”“不在这里?”我重复道。可能是我在听到这个回答时露出了惊愕之色吧,老太太于是反问我叫什么名字。当她得知我是谁和从何处来以后,更是不耐烦地加了一句:
“您怎么还来问我?小姐不是第二天就回你们那儿去了吗?”我不再理睬老太太,迅速穿过一条又一条街,最后到了码头上。夕阳已经西下,港口外的泊船处让晚霞给洒上了一片紫红色的光。前几天那艘双桅帆船曾停在这儿,眼下已经没有一点儿踪影。我设法和闲立在周围的工人们攀谈,从他们口里打听出船和船主的名字,知道三天前船已出海走了,更多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只是把船主的下榻处告诉了我。我立即去那地方,在那儿了解到,有一位黑头发的年轻漂亮的女士也上了船。接着我又赶到船主的账房间,在那儿偶然碰上了他的老会计,可他也帮不了我更多的忙,因为旅客的事完全归船长管。
我回到旅馆,让人备好马。黑马急速地奔驰在回家的路上,超过了我哥哥可能允许的限度。夜色已浓,天空中彤云密布。夜风在黑暗中呼呼地从我身边刮过,我的思绪也风驰云涌。就像幻影一样,我在眼前时时看见那艘载着她远去的帆船,只那么一丁点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飘摇摇,周围是黑沉沉的夜,下边是张着大口的无底深渊。终于,从面前的树影中闪射出了庄园的灯光。
我发现家里人人都伤心难过,惊惶不安。原来燕妮来了封信,从“伊丽莎白”号双桅帆船上发出的。她走了,到大洋彼岸她母亲身边去了,如她曾经对我讲过的。她在信里也写道,她是为了去完成一桩神圣的义务。她以最诚挚、最甜蜜的话语,请求大伙儿原谅她。信里没提到我的名字,但我早已暗中得到了她的问候。她也没有提到她的父亲。
第二天,我和哥哥又一块儿进城去,但只是为了使自己确信,已经没法再赶上“伊丽莎白”号。
我没跟哥哥回家,而是径直去了皮尔蒙特。到那儿不多一会儿,我就站在燕妮的父亲面前,向他报告他女儿出逃的消息。我原想象会看见老头在我面前晕倒,谁知从他的眼睛里却并未流露出悲痛,而是闪电般地射出勃然大怒的火焰。他放在桌子上的拳头攥得紧紧的,青筋毕现,嘴里同时一迭连声地咒骂着自己的女儿。
“让她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好啦!”他吼叫着,“这个贱种是好不了的,真该死,我竟有过妄想!”
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不吭声了,坐下去,把脑袋埋在手里,自言自语似的又说了起来,“我讲些什么哟!她是我的亲骨肉,还有我的罪孽。孩子有什么错!她想要找自己的母亲。”说着,他伸出双臂,眼睛呆视前方,大声喊叫道:“啊,燕妮,我的女儿,我的孩子,我害得你好苦!”他像是忘记了我在面前。我呢,也不去打扰他。“我们都是人啊,”他接着说,“你应该原谅我才是,可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讲,结果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这当口,我大起胆子使他注意到我,告诉他,我和燕妮已经相爱。一听这话,精神颓丧的老人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恳求我替他把他的孩子找回来。
还有什么好讲呢!第二天我便又登上旅程,不过行前他给了我一封信,是他当天夜里写给他女儿的。而且请相信我,这次不再是一纸收据,愤怒和温情,怨恨和宽容,跟我与他坐在一起的那个长夜里从他口中交替吐露出来的一样,现在在这封信里全有。
余下的情况——阿弗雷德结束他的故事——你已经知道了。眼下我就站在这儿,带着她父亲的许诺和全权委托,等起锚的钟一响,就出发去作迎接自己的未婚妻的航行。我和阿弗雷德一块儿又待了约莫一个钟头;随后塔楼上钟敲三点,搬运夫便来把他的行李送到了下边的码头上。我送我的年轻朋友上船。夜里的空气凉飕飕的,强劲的东风激荡着海水,把小艇在栈桥上摔打得砰砰直响。阿弗雷德跨上船帮,将手伸给了我。“不是吗,阿弗雷德,”我用说笑来掩饰临别的伤感,说,“要么和燕妮一道,要么永远不回来?”“不,不!”他大声回答,这时小艇已经向黑夜驶去,“和燕妮一道,一定回来!”
那夜以后已过了半年多,我仍然没有到城外的庄园里去。眼下,当五月的熏风开始吹送进我敞开的窗户中来时,人家又对我发出了新的邀请;这次我不打算再让主人失望。在我面前躺着两封信。都是从圣克洛克斯岛的克里斯蒂安市发出的,其中燕妮写给阿弗雷德的那封信,由于收信人不在,由他的嫂子代拆了。信里写道:
“我找到了我的母亲,没有费多少力气,因为她在港口附近开着一家大客栈。她还很漂亮,精力也挺旺盛,可在她的脸上,虽然轮廓我还认识,我却已找不到多年来渴望一见的那些神情。我必须告诉你一切,阿弗雷德,情况与我想象的完全两样。我害怕这个女人,一想起在第一天吃午饭时她把我——她的女儿——介绍给一大帮男人的情景,我身上就不寒而栗。介绍完了,她又操着一种杂拌儿的混合语言,大声地得意地吹嘘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这一切,都在暗中咬噬着我的心,对我来说讳莫如深——旅客和食客多半为有色人,而其中一个有钱的混血儿,看来又居于左右全局的地位,他对我母亲的那个亲热劲儿,叫我的脸上直发烧。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像狗一般龇牙咧嘴的人,阿弗雷德,他要求我嫁给他,而且我母亲自己也逼我这样做,一会儿用几乎把我憋死的狂热的亲吻和抚爱,一会儿又在大庭广众中声嘶力竭地对我进行斥骂和威胁。我常常禁不住望着这个女人的脸发呆,像是神经已经错乱。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副面具,必须扯下它,才能看见那张在我童年时曾俯视过我的美丽的脸;仿佛在扯下面具以后,我也将重新听到那曾经伴我入睡的像蜜蜂的嗡嘤一般甜美的声音。啊,这儿围绕着我的一切真是可怕!一大早,由于我的卧室朝着码头一面,工人和搬运夫的吆喝声便吵醒了我。你们在那边的人不了解这种声音。它像嗥叫,像咆哮,听见它,我就浑身哆嗦,只好把头埋在枕头里。要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我自己就是他们的同类,身上流着与他们一样的血液,那血统关系就像一根链条,从他们身上一环一环地通到我身上。我父亲是对的。可是……我一正视面前的深渊,我就头晕目眩。我渴望投进你的怀抱:快来救救我啊,阿弗雷德,快来吧!”
救星离得已经不远,另一封信是阿弗雷德写给他嫂子的,发出的日期只晚几天。他踏上旅途时的乐观信念,也帮助他在大洋彼岸取得了胜利。
“还在船上,”他写道,“人家就告诉了我燕妮母亲的住处。在我进屋时,到门厅里来迎着我的第一个人正是燕妮自己。她高兴地叫着,投进了我的怀抱。自此以后,我也对她母亲有了足够的认识:她是个丰腴的女人,仍然很漂亮的,穿着一身窸窣作响的花绸裙忙来忙去,操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语言,不管是对客人还是对仆佣。时而柔声细气,时而嘶声狂叫。谈起燕妮的父亲,她仍怀着感激和尊敬,称他是那位‘好心的绅士’,由于他的慷慨大方,她才过上了今天的舒服日子。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离开自己生长的岛屿,更别提去跟自己女儿那高贵的父亲结婚。她在这儿适得其所,舒服自在。而燕妮,必定是大失所望,她挣断了与旧大陆的一切联系,梦想着来解除母亲的苦难,然而却没有找到这样的苦难,只找到了一群低下的人,在这群人中是不会有那种高贵的苦难的。尽管如此,女儿的到来却使这快活的女人喜出望外。她经常当着我的面,以一种狂暴的,我想说是原始的热情,对她的女儿百般爱抚。由于她想拿女儿到客人面前炫耀,就不断变着法儿打扮她,燕妮为了不穿母亲替她挑选的那些火红刺眼的衣服,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如此,她还为燕妮在店里的客人中挑选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做丈夫,在这个人身上,我感到他身上还激荡着足够的此地那种罪恶的血液,而且她已经认真着手准备,为了促成其事。就在这时我插了进来,那位‘好心的绅士’的意志和权威使一切问题都再容易不过地得到了解决。”
“我清楚地体会到,燕妮在迎接我时发出的不只是一声欣喜的叫喊,而是一声得救的欢呼。这样也好,她是得先体验一下,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属于我;只有她不再回首过去,不再怀念过去的家,才能嫁给一个男子,让这个男子骄傲而幸福地和她一起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庭,看着他的后代子孙从她的怀中诞生、繁衍。须知,我是在我们结婚的当天给你写这封信的啊。”
“在结婚的宴席上,殷勤好动的老板娘穿着闪闪发光的绿绸裙,往来穿梭地周旋在她的老主顾中间,为自己有一个漂亮迷人的女儿而无比骄傲,为她的女婿——我不能否认——也感到骄傲。她同时操着三种语言,用一些叫你无法相信的措辞,为新人一次次祝酒,这一切的一切,你们要能看见就好啦!——我们希望一开春就去你们那里。而你,格蕾特,以你对我们的友情,想必不会心生嫉妒,如果我私下告诉你,燕妮刚才悄悄对我讲:‘喏,阿弗雷德,帮助我,让我回到父亲那儿去吧!’”
这两封信是附在汉斯夫妇的邀请信后边的。“您来吧,”格蕾特用女性的秀丽笔迹写道,“燕妮的父亲已在这儿,阿弗雷德的父母今天就到,甚至约瑟芬姑妈也会光临,虽说她对于一个在小时候就那样肆无忌惮地糟蹋英国缝衣针的姑娘,不时地还会表示一些疑虑。我们已从自己的冬居迁回到明朗的花厅中。透过两扇大开的厅门,从草地上飘来五月百合的芳香。在对面的林苑中,立着维纳斯的水池也已让紫罗兰镶上了蓝边。”
紧跟着是我朋友汉斯的有力的笔迹:“双桅帆船‘伊丽莎白’号上个礼拜天已经驶过里斯本,燕妮和阿弗雷德就在船上,过不几天他们便会抵达此地,因为已经刮起的顺风,将把他俩和他俩的幸福一块儿带到我们身边。”
①濒临地中海的西班牙省份,以盛产葡萄酒著称。
②似指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提(约前460~前377)。
③指死神。
④安德烈·勒侬特尔(1613~1700),法国园林风格的创始人。
⑤德国北部的著名温泉疗养地。
⑥意即托付终身,与人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