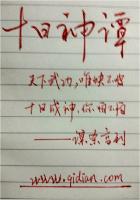“一个有色女人的手。”她的嗓音喑哑了。“你的手,燕妮。其他的一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她站着一动不动,只有她那仍然被我握着的手在颤抖,使我感到她还有活气。“我知道,我是很美的,”她后来说,“美得令人迷醉。就像我们人类之源——那罪孽一样。可是,阿弗雷德,我却不想迷惑你。”话虽如此,当我默默地向她伸出双臂时,她突然扑到我的胸前,用手紧紧搂住了我的脖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深不可测。“是的,燕妮,”说话时,我觉得仿佛有一股寒气从树林中吹出来,直透我的骨髓,“是的,你美得令人迷醉。那曾经扰乱人们的心,使他们忘记自己过去所爱的一切的魔女,也不比你更美。没准儿你就是魔女的化身吧。在这样的良夜里,你来世上巡行,只是为了赐予那些仍信仰你的人们以幸福。——不,不,别离开我的怀抱。我知道得很清楚,你跟我一样是人,一样为你自身的魅力所困扰。在它面前一样无能为力。还有,像那吹过林梢的夜风一样,你也会玉殒香消,杳无踪迹。不过别诅咒那使我俩相互拥抱在一起的神秘的力量。就算我们在这儿是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未来生活的基础,它将要承受的大厦却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把她的手从我脖子上轻轻拉下来,用一条胳臂搂住她的腰。随后,我扯掉缎带,把戒指套在她的食指上。她像个安静的孩子似的偎依着,任我带领着向前走去。不多时,我们走到了另一片池塘边,那尊维纳斯女神果真依然立在一朵朵白色的睡莲中间,此刻我更加确信,我搂在臂膀中的是一个凡间的女子。
几经踌躇,我们终于还是离开了那些树影幢幢的幽径,走进小树林中,从小树林出来,又到了房子对面的旷地上。草坪对面,穿过那两扇敞开着的厅门,我们看见我的哥哥、嫂嫂正在明亮的厅中踱来踱去,好像密谈着什么似的。
还没等我明白过来,燕妮一弯腰挣脱了我的搂抱,但同样飞快地,她一下又抓住了我的手。
“你要做答应了我的事,阿弗雷德,”她说,“而其他的一切,”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补充道,“都忘掉吧!”
格蕾特走到敞开的厅门边,冲着黑夜大喊:“燕妮,阿弗雷德,是你们吗?”这时燕妮急切地请求我:
“别提我的事,对你母亲也别提,咱们不应叫她们不痛快。”“可我不懂你的意思,燕妮。”她只使劲儿地捏我的手。然后,她离开我,奔上露台,站在格蕾特身边。当我们走进大厅时,格蕾特摇着脑袋,把我俩打量了又打量。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马进城去,实践自己的诺言。在城里,我分别找了两个珠宝商给首饰估价。它值不少钱,而我当时的钱包正好很充实,因此可以替燕妮把首饰自行保管起来,用我随身带的现款调换成价值相当的金币给她。事情办妥以后,我还在美丽的港口里溜达了一会儿。在港外的泊船处,一片金色的光雾中,能看见远远地停着一艘大船。一位海员告诉我,这艘双桅帆船正整装待发,即将驶往西印度群岛。“驶往她的故乡!”我心里嘀咕,这一来我便十分想念她,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赶紧踏上了归途。将近中午,我跨进大厅。厅中阒无一人,但看门外,却见燕妮和一位瘦削的上了几分年纪的男人站在花园里,离大厅有相当距离。接着,他颇为庄重地把胳臂伸给她,领着她朝房子走来。走近了,我方才看出这男人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但在清癯的脸上,一双眼睛咄咄逼人。脑袋的简捷摆动也表明,他已习惯发号施令。白色的围巾和衬衫皱襞中的大钻石别针,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是他身上的组成部分。我立刻就知道,他是燕妮的父亲,那位阔绰的庄园主,我自己迄今尚未谋面的远房表叔。不过尽管如此,他眼下这模样却和我孩提时代的想象完全吻合。此刻我听见了他那异样的嗓音,他对自己女儿讲的话短促有力,我听不懂讲的是什么意思;燕妮呢,也是只听不答。
我感到自己没有立刻与他见面的精神准备,便赶在他父女俩登上露台之前离开大厅,到楼上去了。燕妮的卧室门开着,我走进去,按照约定把用首饰换来的钱放在房门上方的壁橱里。然后,我退回到自己的房间,既激动又疲倦地倒在沙发上。
约莫才过了几分钟,我就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接着有两个人从我房前经过,走进隔壁大屋子去了。正对着我的座位,有一扇沟通两间屋子的门。这门眼下虽然关死了,但上边却是一面玻璃窗,背面挂着一块白帘子。
我从声音听出来,走进隔壁房中的是燕妮父女,虽说他们可能站在房里的另一端,我一点听不明白他们谈些什么。我正打算悄悄离开,却见他们走过来了,而清楚地传进我耳际的头几句话,就对我产生了奇异的影响,我把其他一切统统给忘记了,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不,你不能留在那儿!”我听见燕妮的父亲道,语调仍如刚才讲话那样急促。“为什么呢?”燕妮问。这时我听见他来来去去地踱了好几圈,然后静静地站住了。“你既然非要我说不可,”他回答,“那就听好了。由于你母亲的血统关系,你永远也别想进入你父亲的社会。”“也由于我自己的血统关系,”燕妮补充说,“这我了解。”“你了解?谁给你讲这些事的?”“谁也没有,我自己从书里读到的。”
“喏,既然如此,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送你到欧洲来。我想,你应该感激我才是。”
“是的,”她说,“就像我要感激你让我生下来一样。”父亲没有回答,但是一扇窗户被推开了,从声音判断,他是把脑袋伸到窗外,在十分激动地清着嗓子。燕妮背靠在两间屋子之间的门上,透过挂着白帘子的下玻璃窗,看得见她脑袋的影子,听得见她裙子的窸窣声。
过了片刻,父亲像是又退回到了房间中央。“我为你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他又开始说,“你自然从未表示过任何违抗我意志的愿望,不过我也不知道,你还能有什么愿望。”燕妮站直身子,向他慢慢跨出一步。“我的母亲在什么地方?”她问。
“你的母亲,燕妮!”老头子失声叫喊出来,仿佛他准备好了回答一切问题,就是想不到女儿会问这个女人,“你自个儿也知道,她还活着,她得到了照顾。”
“可是,”姑娘毫不留情地追逼着,“在你的大房子、新房子建成和布置好以后,你有过去接她上这边来跟咱们生活在一起的打算吗?”
我听见老头子脚步沉重地在大屋子里走上走下,随后再次来到了女儿跟前。
“你还是个孩子,燕妮,”他压低了嗓门儿,语调却变得严厉起来,“你不了解那边,不了解你出生的那个国家的情况,再说你也不需要去了解。”这时候,老商人像是突然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似的,继续说,“她真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啊,那个女人,难以置信!——她那么躺在吊床上轻轻地摇啊摇,在芒果树宽大的绿叶丛中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头顶着热带明净的蓝天,脚下是阳光灿烂的港湾,特别是当她和她的鸟儿们嬉戏的时候,或是朗声笑着把一个个金球抛到空中的时候!可是你千万别听她讲话,她那张漂亮的小嘴儿说着黑人的粗劣语言,哇啦啦地跟个学语的孩子差不多。那个女人,燕妮,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想成为你现在已成为的这种人的话。”
燕妮又把身子倚在门上。“为这个,”她说,“你就把一位母亲的孩子给抢走了。她大声哭叫,啊,她大声哭叫,当你把我从她怀抱中夺过来,走上跳板抱进船舱的时候!而这哭叫声,就是我听见自己母亲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有好长时间我把这声音给忘记了,因为我是个没头脑的孩子。上帝宽恕我!——而今每天夜里我的耳畔都响起这声音。是谁给了你权利,用我母亲的痛苦来做换取我未来的代价!”我透过窗帘看见,她讲到这里时将身子挺得笔直。
当父亲的像是抓住了她的手。“你要明白,燕妮,”他说,“我只能在你和她之间作出选择——而你是我的女儿。”
说最后这句话的温柔而慈爱的声调,似乎对女儿仍未产生影响。“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说,“那付出代价的,既非你,也非我。必须将它偿还给她,趁现在还来得及。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我的母亲将和我们一起住在新居里吗?”
“不,燕妮。这不可能。”随后是一片死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姑娘的内心活动如何,神态举止中表现了怎样的情绪,我都无从得知。“我还有一个请求。”她终于又开口了。
“尽管讲吧,燕妮,”她父亲急忙答应,“尽管讲吧。其他一切全成啊,只要我力所能及!”
“那么我请求你,”燕妮说,“当你去皮尔蒙特疗养时,允许我留在这儿,我朋友的家里。”
父亲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如果你认为不陪伴自己的父亲更合适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燕妮没答理,只是问: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要是你再没话对我讲的话,我也一块儿下楼去。”接着,门开了,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在外边的走廊上渐渐移向楼梯——我自己一直待在房间里,直到被叫下楼去吃午饭。在哥哥把我介绍给燕妮的父亲时,他用眼睛迅速地将我打量了一下。我感到,我这个人已经让他作了大致差不多的估价。接下来他问我学过些什么,到过哪些地方,我的专业知识在家乡有无机会派上用场,颇有些老师考学生的架势。末了,我也受到很客气的邀请,一等他从温泉疗养地回来,就前往他的新居,以便对它发表一些行家的意见。从这个男人的外表上,已经丝毫察觉不出适才在他和他女儿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吃饭时,他坐在我母亲身边,专心一意地和她聊着天,当母亲把话题引到他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年华时,他甚至还会说说笑话。他提醒我母亲,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故乡城里的音乐厅里跳舞,而且在音乐厅的壁毯上,有一个真人大小的胖胖的小爱神。“那些年轻的女士们,”他说,“在他面前是如此害羞,以至于跳舞的行列在那儿总是出现一个缺口。”“可您,表哥,”我母亲应道,“却总是热衷于把您的小姐领到那个堕落的神道跟前去,一而再,再而三。”只见他彬彬有礼地对我母亲鞠了一躬。
“我知道的,表妹,”他说,“您和我在一起跳舞时,也并不怕她呀。”我看见母亲在听着这几句话时,那至今风韵犹存的面颊上掠过了一片红晕,便不禁想,难道他俩也和现在他们的孩子一样,当年曾经互相倾慕吗?就连刚才一直漠不关心地坐着一点儿东西没吃的燕妮,这时也抬起了眼睑,也许她从未听自己的父亲讲过如此轻松愉快的事吧。她父亲呢,则压根儿不跟坐在对面的女儿说一句话,而是又和我哥哥扯起交际场中的种种趣事。过后,在喝咖啡时,我却听见他对我母亲讲:
“承孩子们的好意,燕妮将在这儿继续待一段时间。我明天独自动身。我们相知多年,尊敬的表妹,你有机会不妨给她讲讲那些咱们在一起时的日子。过不多久她就要陪一个老头子生活,在这之前让她了解一下他年轻时的情况,也许有好处。”他一边与他青年时代的女友握手,一边站起来补充了一句,“要这样,您就算帮了我大忙啦,表妹。”
一天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机会单独碰见燕妮,她显然有意躲着我。格蕾特也多半在外边忙着家务。
第二天早上,在我们的客人动身后,格蕾特来到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将双臂抱在胸前,冲我笑了笑,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这下又只剩下咱们自己啦!”我立刻惊讶地得知,燕妮当天上午就要进城去耽搁许多日子,为了和她父亲的女管家一起在新居里进行鬼才晓得的什么布置。当燕妮一身旅行装束朝我走来时,我正孤零零地站在露台上。她把手伸给我,我却为她竟忍心在现在离开我而生她的气。“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燕妮?”我问,“难道那些事就这么急?”她摇摇头,一双大眼睛安详地望着我。在她的眼神中,我只能讲,流露出一种崇高的热诚。
“你还是要走吗?”我又问,“而且正好是现在?”“我不愿欺骗你,阿弗雷德,”她说,“并非你想象的那样,我是必须走,没有别的办法。”
“那我每天都进城来帮助你。”她显然吓了一跳。“不,不,”她大声说,“你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别问我!——啊,相信我的话吧!”“你是不信赖我吗,燕妮?”
她哀叫一声,我从未听见过这么惨痛的声音。随后她向我伸出胳臂来,全不顾会有谁看见,就像上次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样,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又把她搂在自己怀里。
“既然这样就别待得太久!”我请求说。“我父亲盼我回去,我在这儿的时间不长了。”她默不作声,我低头望着她那美丽而苍白的脸庞。她紧闭着双目,脑袋靠在我肩上,像是想在此安息安息。只这么待了一会儿,她便挣脱身子。接着我们绕到了屋子正面,那儿已停着一辆马车。她上车以后,我还听我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别哭了呀,孩子!瞧你哭得心都碎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