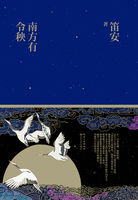我客居在德国北方某市近郊一位朋友的庄园里。我俩曾共同度过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直至青春将逝,各人有了各人的职业,才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在彼此不曾见面的二十年内,他创建起一家大商号,成了这家商号的总裁;我却让时事逼得远走他乡,并且永远待在了那里。而今,我终于又回到故乡来了。
朋友的妻子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她已不再年轻,然而举手投足仍像少女一般轻盈敏捷,安详的目光仍跟孩子似的清澈明亮。而且我很快发现,这两个人相互体贴入微,恰如一对新婚夫妇。早上她穿戴整洁地走进餐厅,眼睛首先搜寻的总是他,恰是想向他的眼睛发出无声的询问,她这样打扮可合他的意。接下来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一下子消失了,他随即握住她伸过去的手,好似她刚刚才把她的手和终身交给他似的。有时他坐在自己书房的办公桌前,她则从起居室或者前边的花园走进来,默默无声地坐到他的身旁;有时她也会悄悄踅到他的椅子背后,将手轻轻儿搭在他的肩上,仿佛要他相信,她在他的身边,她为他而存在。
十月里一个晴朗的午后,我的朋友办完他的商务,刚刚从城里回来。我俩坐在房前宽阔的露台上,一边聊着往昔的岁月,一边目光越过下面的花园和前方紧接着的绿草地,眺望东海海湾的暗蓝色海水,以及海湾对面缓坡上的山毛榉林。这时节,榉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这整个画面以及头顶上深秋季节的蔚蓝晴空,都嵌在露台两侧挺立着的参天白杨中间,活像镶着个巨大的黑色画框。
朋友的妻子牵着她最小的女儿从花厅敞开的双扇门中走进来,打我们面前经过时面带着文静的微笑。她不想介入我们的过去,那跟她完全不相干。眼下她伫立在露台边上,手里抱着孩子,目送着一艘从眼前驶过的汽船。已经好一会儿,四周的岑寂让汽船的轮机声给打破了。在蔚蓝色天穹的映衬下,她高挑的身材和高贵的头形看上去格外分明。
我俩的谈话中断了,目光可能都情不自禁地追随着她。我无意识地伸出了手,想去取摆在面前大理石桌上水晶盘中的葡萄。
“事情注定了这么发展,”我终于重新拾起话头道,“我,一度甚至做过栗子和樱桃仁买卖,结果成了一个文化人;而你——念文科中学六年级时写的那些个悲剧,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
“意大利式的簿记,”他微笑着回答,“是一帖克服文学癖好的猛药。尽管如此,为了让它生效,我还不得不添加上坚强的毅力。”
他用自己那双深色的眸子盯着我,目光仍流露出青年时代所具有的坚毅个性。“可能够吃力的吧?”我说。“吃力?”他慢慢地重复着,“我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少得不能再少了。”说时他朝自己的妻子送去温情脉脉的一瞥,满含着喜悦的一瞥,就好像他刚刚才得到这个爱人似的。
我不由得想起来此第一天的一件小事。当时我跨进朋友的书房,一眼就发现在他的写字台旁挂着一位美丽少女的肖像。那是一幅油画,色彩明快鲜亮,形象生机勃勃。我问画的是谁,鲁道夫便回答:
“是我妻子的画像。也就是说,”他补充道,“是那个随即成了我未婚妻,后来做了我妻子的女孩。像最初是画来送给爷爷奶奶的,最后又作为遗产回到了她自己手里。”说着他踱到了画像跟前。我呢,则在脑子里把这青春焕发的容颜,和我还只是匆匆瞥见的主妇的面容做着对比。——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注意到他时,发现他的脸上分明流露出一丝隐痛,一种发自内心的、我在这个家住得越久越无法解释的表情。要知道,这位少女而今已经属于他。她健康地活着,而且——看起来是这样——现在仍使他感到幸福。
这当口,我们面前那美丽、安详的身影离开露台,走到下边的花园中去了。我呢,也不怕碰着人家尚未痊愈的伤口,没法再管住自己的嘴巴,便将适才的发现径直抖搂了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鲁道夫?”我边说边抓住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手,“告诉我吧,要是你办得到!”
他再次望了望下边的花园。在花园后面的草地上,已经冉冉升起了暮霭。接着,鲁道夫抹开额前平直的头发,用我曾经十分熟悉的诚挚声调讲起来:
“没谁做什么亏心事,也没发生任何不幸,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把这种事能行诸言语的部分统统告诉你。——你那会儿从我的信里已经了解,十五年前,我在自己父母家里认识了我的妻子。她来访问我的妹妹,她跟她是游泳时在咱们西海中的岛屿上偶然相遇。我当时正处于事业最艰苦和最折磨人的阶段。一个出资建造我们商号用房的合伙人突然逃之夭夭,所缺的资金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另行筹集,加以填补。
再加上这时我计划创办轮船航运公司也招来邻里妒忌,因此不断碰到新设置的障碍。在紧张的工作中熬过了一天,晚上就需要得到同情和鼓励,就需要有一个心灵的休憩地。这两样,我都在妹妹年轻的女友那儿找到了。傍晚在父母家的花园里,我俩来回漫步在女贞树的篱笆之间,我的打算和我的忧虑便成了谈话的内容。她不只善于倾听,还理解一切。你来此第一天就赞赏过她为人朴实、稳重,在当时她已表现了这些品格,还有年轻人的敢作敢为精神,她同样不缺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和两个姑娘面对面坐在凉亭里古老的石桌旁。那天白天,我真是什么祸事全降临了。一瞬间完全心灰意冷,竟叫了起来:‘完啦,我已经精疲力竭!’她没有搭腔,却默默用手支着下巴,用近乎愤怒和惊愕的目光瞅着我,瞅了有好一会儿。随后她把头转向我妹妹,笑了笑说:‘你瞧瞧!他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她说得确实不错,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已感到有足够的能力。终于,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她把自己的手交给了我;我呢,也紧紧握住了它不再放开。
“别人常对我说起她的美貌,这我也注意到了。过去我从未想过这事,后来同样也没有再想。她就这样成了我的妻子,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伴侣,而我在生活中,每天总会遇上需要解决的新的难题。你应该回忆得起来——当时我经常给你写信——从此我怎样摆脱了一个麻烦又遇上新的麻烦。我当时有种感觉,好像一切全靠了她。她似乎遇事总知道该干什么,她似乎能听懂事物无声的语言,就像童话里的那个金姑娘,在经过林子时能够听见树木发出的喊声:‘摇摇树干,摇摇树干,我们这些苹果全都已经熟啦!’①——没过几年,我已有能力买下这座庄园,并且进行装修,以满足自己不多的心愿。但是,随着好运的光顾,业务也日渐增多起来。不是我支配它们,而是它们支配我,让我陷入了一个接一个连环套似的网络,整个的心力全投进去了,一天又一天地只做着这件事。”
我的朋友停止了讲述。他那个最大的十二岁的女儿从屋子里来到我们跟前,问她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鲁道夫抱起了她,侧耳朝下边的花园倾听。花园围墙的旁边,玻璃暖房的白色屋脊高耸在灌木丛的顶上。从暖房里传来小妹妹的笑声,其间也不时能听见妈妈诓哄小家伙的声音。
“快去,燕妮!”鲁道夫微笑着说。“有两只大无花果熟了,你们可以摘走!”小姑娘点点头,离开父亲,跑下台阶,越过铺展在露台下边的草地,消失在一旁的灌木丛中。
父亲目送了她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讲:“那是春天里一个礼拜天的午后,这个我们刚让她去了母亲那里的苗条小姑娘还不满半岁。这儿露台边上那间花厅当时刚刚刷过漆,春天的阳光照着地面,穿过敞开的双扇厅门,飘进来才露头的新叶和蓓蕾的芬芳。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了一本书。很久很久了,我已经不再看这样的玩意儿。我不知道,当时是想起了你和咱们曾经热衷的古德语研究呢,或者我只是打算叫自己相信,除了城里我那些幽暗四壁间的狭小帐房,我在这外边还有另外一片天地。我翻开的是歌特弗里德②大师的《特里斯坦》。正对面的窗前,离我不远坐着我正在做女红的妻子。我俩的孩子则睡在隔壁房间的摇篮中。周围一片宁静,没有任何事物来打搅我,于是我便跟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开始了他俩的海上旅行。
“帆船破浪前行。寂静的正午时分,伊索尔德独自坐在甲板上。夏风吹拂着她金色的秀发,她眼里却充满了泪水:她思念自己的家乡,她害怕去到异域,怕去那儿与一位白了头的老国王成婚。特里斯坦上前安慰她,她却赶走了人家,她恨这个男人,因为他杀死了她的叔叔莫罗特。空气变得闷热,她口渴了。船舱里随意地摆着一瓶药酒,原本是为点燃伊索尔德心中对老新郎的爱火而准备的。一名年轻的侍女叫道:‘瞧,这儿有酒呢!’特里斯坦于是不经意地把它递给了王后。
她迟疑地饮了口酒,心中十分难受,
随即递给他酒杯,他也喝了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