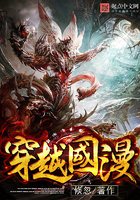始元六年的初夏,长安城里已经稍微有了些的热意。
永远沉浸在寂寂夜色的永巷似乎也被这初夏的光感染,透露出一种不可多见的蓬勃的气息。
一座平凡的小院子里,一身着属官服的中年男子负手而立,很是静默。近看时,这男子虽然衣着平凡,眉目间却别有一股子气宇。这人,便是因触犯刑法被贬为暴室啬夫,许广汉。
许广汉的前尘往事,暂且不理会。然而如今一件事却颇让他烦心。因为今天,掖庭要迎来一个特殊的人,卫太子的后代,当年巫蛊之祸的幸存者,刘病已。
虽然宗室里已经明确了他的地位,但是刘病已的身份,始终是尴尬的。许广汉打不定主意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位落魄的皇室贵胄。
好在他终究是个豁达的人,没过多久,释然一笑:“罢了罢了,随缘吧。”
正打定主意,却见张贺迎面走进,身后跟着一位约摸十一二岁的少年,眉目俊朗,落落大方,面容沉静,很有风度。
许广汉顿时对这位少年产生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欣赏。
许广汉见到张贺,只随意行了一个礼,此时的他,眉间除了悒悒之色,倒是别无他物了。
他和张贺虽然地位相差很远,可张贺一向是爽朗的性子,并不在意这些,随意摆摆手,又看向身后的少年:“这是皇曾孙。”
许广汉敛衽一拜。
那少年侧身避过,淡淡道:“许大人不必如此,叫我病已便好。”
许广汉暗自惊诧,以前听闻张贺总爱赞这位皇曾孙聪颖有风度,他还颇有几丝不以为然,如今见到刘病已,却也明白张贺赞他的原因。可他毕竟不是张贺,于是微微一笑道:“礼不可废。”
张贺到一向是个爽直的,拉着许广汉,笑道:“以后皇曾孙就在此处住下了,广汉你要好好的照顾他。”
许广汉暗叹这位张贺和他弟弟还真是性格迥异,却还是应道:“是。”
张贺在刘病已来之前,已经暗中吩咐许广汉打点好了一切,他有职位在身,不便多留。许广汉和刘病已在院子里两两对望。
刘病已虽然如今是落魄的皇室贵胄,可毕竟也是贵胄。更何况当年卫太子的风仪许广汉虽不曾见,却也有耳闻,心中对病已也存了几分怜悯,于是自然是对病已甚是上心:“公子请。”
少年听他这称呼,却也只是缓缓一笑:“以后我们还要相处,叔父实在不必如此。”
刘病已虽然这么说,许广汉却不是直爽没心眼的张贺,他自忖自己当不起刘病已这声叔父,于是只是一笑,依旧如常。
却说长安城中一位寻常的宅子里,绿意蓊郁。有一妇人的声音传出:“平君,你慢点,有点女孩子的样子。”
随着夫人的声音,从宅子里跑出了一身着半臂襦裙,梳着双丫髻的女娃娃。她听到妇人的话,随即便放缓了步子,不甘不愿的应了一句:“知道了。”
那边没有妇人的声音传来,平君顿时像是出笼的鸟儿,一边蹦蹦跳跳的向前走,一边自言自语:“娘总是管东管西,真没意思。”
她年纪小,那里是静的下来的性子,况如今长安城里的夏日刚开了个梢,春末的明丽欢快还未退去,真是人间的好时节,适合在城中乱转的好时节。
女娃娃秀丽明媚的面庞稚气未脱,双丫髻随着她的步子,极是惹人喜爱。
平君自顾自转了一会,想起来自己当值的爹爹,一时兴起,索性去找爹爹。
她不知道家中究竟出了什么变故,导致父亲这几年心情郁郁,只得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父亲。掖庭虽然是未央宫中的一部分,当值的侍卫却也认得平君,倒也没拦着她。
平君自幼和父亲亲近,自然是极其欣悦的走着。走着走着,只听得“哎呀”一声,却是女娃娃和一个少年在拐角处相撞,冷不防便被撞在了地上。那少年似乎是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一时间有一些怔愣。
却见女娃娃已经先声夺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少年看着她哭,神色颇有几分懊恼,身体也僵硬了几分。他盯了女娃娃一会,终于蹲下身子去看女娃娃,一边颇不熟练的安慰女娃娃:“你……你,不要哭了。”
那女娃娃却是愣了一下,哭声暂停,然后觑了他一眼,可能是发现了他神色的僵硬,于是,继续哭了起来。
大汉的女孩子虽然不至于柔柔弱弱,却也极少有女孩子哭的如此惊天动地的。更何况少年所见的女孩子甚少,哪里又见过这般阵仗。
他皱眉想了想,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眉间一喜,哄她:“你要是不哭的话,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边话音刚落,就见到原本哭泣的女娃娃哭声已停,眨着眸子问他:“那是什么?”
少年顿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想了想:“是酒,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种的葡萄酿成的酒。”
说罢,果不其然看到女娃娃已自行站了起来,抹了抹脸,冲他灿烂一笑:“那便走罢。”
少年顿时有一种无力感。虽然如此,他还是带着女娃娃去了自己以前住过的外祖母家里的宅子。
这个少年,便是趁着空闲在长安城里逛街的刘病已。
他不过是趁着天气好想出来走走,谁料刚出来便见到了平君。
平君这会子倒是很乖的跟在刘病已的身后,病已看她自言自语的嘀咕,不禁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平君一愣,看了他一眼,倒是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反倒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病已微微一笑:“你倒是不肯吃亏。”
女娃娃眨了眨眼,没有说话。
病已道:“我叫刘病已。”
话音刚落,却见女娃娃“啊”的惊呼出声,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遍:“你就是那个皇曾孙?”
病已挑了挑眉,卫太子一案牵连甚广,在当时的确是轰动一时,自己的名字却并非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他正思索着女娃娃的身份,却见女娃娃已经自己自报家门:“我叫许平君。”
病已吃了一惊,许广汉虽然官阶不高,却让人捉摸不透,不料却生出了这么一个女儿。虽然这么想,面上却分毫不露。只是故意皱眉也上上下下打量了平君,挑眉:“倒是糟蹋了这么个名字。”
他本继承了父母绝好的容貌,如今故作皱眉,却衬得眸子愈发湛湛,很是有几分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样子。平君当即反驳道:“你却倒是糟蹋了好好的一张脸,明明是小人,却故作君子。”说罢却又恍然自己倒是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了,不满的哼了一声。
刘病已高深莫测的“哦”了一下,却也没再说什么。
两人走着,发现已经走到了一个宅子后面。
这所宅子虽然外表寻常,内里却古意森森,精致典雅,可见当初卫氏的盛极一时,以及如今的落魄。
想到传说中的巫蛊之事,平君莫名的生出了几分惆怅。
病已见她明显神色闷闷,以为她是小孩子心性,不禁问道:“马上就能喝到葡萄酒了,你却怎么又不开心起来了。”
平君回过神来,余光瞥见病已身上的曲裾深衣,虽然不至于短褐穿结,却也着实不像是大富人家的孩子该有的,她听闻宫中克扣不受宠皇子的用度,心里便软了几分,便问道:“虽然你撞了我,是你的不对,可是葡萄酒实在难求,你不用那么客气。”
病已听到她这么说,倒是笑了:“这是我偷来的种子自己种的葡萄,且是我自己亲手酿的酒,你真的不要尝尝?”
平君一听他这么说,当即反悔道:“你既然如此诚心相邀,我怎能人心辜负你的好意。”
说罢,反倒是自己先推门进去了。
病已见她丝毫不知道什么叫客气,却也并没有厌烦,只觉得好笑。他自幼身世多舛,自然不可能有普通小孩子的天真可爱,虽然有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演戏,如今见到平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自觉的想惹到这个麻烦。
后来,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宿命。
却说平君走进了院子,顿时便被院中的葡萄架子吸引。
病已凝视着遮住葡萄藤,说道:“这是我问张骞要的。据说,父亲母亲以前在宫中也种了一株葡萄藤……”
平君眨巴着眼睛看着面前少年的背影,少年削瘦的背影莫名被打上了一束柔和的灯光。
君不见长门咫尺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她出声唤他:“病已哥哥。”
病已的思绪猛然收回,他脊背僵了僵,回身时,已经神色如常。他看着一派天真的女孩子,忍不住淡淡微笑:“病已哥哥?”
平君看着他玩味的神色,一时之间有些困窘,但是她素来比一般的女孩子脸皮厚,于是清了清嗓子,强自镇定:“爹爹说过,人不能困于过去,你要开心一点。”
刘病已虽然没有在深宫中长大,却自幼体会过世情冷暖,他一向便是心胸开阔之人,刚刚也不过是些许感伤。纵然有解不开的心结,却也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看到女孩子担心的神色,于是顺水推舟,点了点头。
病已念及自己是邀平君前来尝酒,不禁拍了拍脑袋,唤道:“平君,随我去挖坛子去。”
史家这所宅子虽小,院中梨花却开的很好,梨树的老枝上点缀着雨雪般的梨花,风一吹,四处蹁纤。病已酿的葡萄酒,就藏在这树梨花之下。
两人费了好大劲才将坛子挖出来,谁料的那梨花纷纷落下,两人满身满脸的落花。平君乐了,不禁笑出声来。病已正一边手忙脚乱的抱着坛子,一边拂去身上落花,见她站在一旁笑,不禁没好气的瞪了她一眼:“快过来帮忙。”
平君还是笑,不过笑归笑,这次终于知道去接过刘病已手中抱着的坛子。
病已这才得空拂去身上零落的花朵,看着一旁抱着酒坛子的平君,失笑:“你还真是……”真是什么,却也没有说下去。
他取下泥封,葡萄酒的醇香顿时弥散开来,平君小心翼翼尝了一口,酒浓郁的香味在舌尖打转,白皙的脸上不觉留下了胭脂色的酒,她眯起眼睛惬意的叹了一口气,满足的像是偷腥的猫儿。
病已不觉得咽了口口水,取过酒坛子自己也尝了口,酒刚入口,就看到平君狡黠的笑容,病已心道不好,回过神来才发觉这酒的味道怪怪的,忙吐了一口出来。
那边平君早已经乐不可支,摇头晃脑的学夫子:“贪吃惹祸。”
病已看着她的得意样子,不禁出言:“刚刚是谁因为酒跟着我来的?又诓我喝这种酒。”
平君笑:“兵不厌诈。”
她如今是个白团子状,脸颊上的婴儿肥极是讨喜,眉眼弯弯的样子甚是可爱。病已心中一动,他一向与人交往带着几分置身事外的生疏和冷淡,如今却觉得有个这般的妹子也是好的,虽然十分闹腾。他抿了抿唇,最后对平君道:“你可真是够闹腾的,女子不是都该端庄一点的么?”
平君皱眉,冷笑:“哼哼。”
病已乐了,干脆伸手去捏她肉嘟嘟的脸,平君嚷:“不许捏脸。刘病已,你妄作君子。”
病已哈哈大笑:“我可没说自己是君子。”他自小都是淡淡的,也没人肯同他玩耍,虽然自诩为大人,却还是挺向往这种童真的,干脆和平君闹了起来,两人追追打打,反而玩的十分开心。
及至夕阳西下,平君才觉得今日出来已经很长时间。病已似是也看到她心中所想,提议道:“天色不早,你也该回去了。”
平君蓦地一笑,满脸因酒晕而产生的酡红,恰若飞霞:“嗯。”
平君临走前说:“我阿爹虽然不善于言辞,却是个高风亮节的君子。”
病已愣住,却是明白这个小姑娘言外之意是说道许广汉甚好相处,让让自己宽心,于是回之一笑。
病已一个人回到了掖庭。
永巷的夜色永远是寂寞的。永巷是失意人的聚集地。失宠的妃子,落魄的皇孙,被贬的官吏……和长信宫,椒房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夜如何其?夜未央。说的或许应该是未央宫中的永巷。
病已静静跪坐在几案旁边,摊开了张贺送来的竹简和布帛。
夜色沉沉,夏夜微凉的风吹入。病已捧着手中的竹简,却并没有看进去。连枝灯的光更暗了些。
他还清楚记得自己年幼时朝不保夕的感觉,他的命,不就是丙吉保下来的么?皇家的子弟,天真单纯,不过是捅向自己的利器。而所谓的偶然,也不过是费尽心机。
暗夜之中,一玄衣男子静静出现,由于站在光线的暗处,看不清面容,从声音上判断,应是一二十多岁的男子:“事情都办妥了。”
刘病已点点头:“辛苦你了,卫洛。”
他凝视着窗外的一轮明月,神色莫辩。
连枝灯的光又暗了许多。
病已开口:“还有,帮我查一查许广汉。”
那人一愣,旋即答应道:“是。”
连枝灯的一枝,终于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