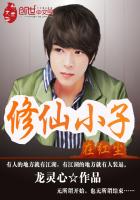我小心翼翼地输入了风儿,然后庄严地点击了开始搜索,看到机子上那一个个闪过的小人头像,心里竟然感觉怪紧张的。然后又一下子明白过来似地,觉得自己真可笑。天,犯得着吗?自己制造紧张气氛哩,她跟我有啥关系?
然而我还是找到了风儿,而且正好在线。那时候分明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又让我隐隐觉得自己很可笑。
飞快地给她发了一个Message:Hi,深圳属猫的年方二六一十二的绿色的疯’美眉’,还记得我吗?
哈,是你呀,西安属鼠的跟刘志丹一拨起事的蓝色’匪盗’GM,我当然记得了。:)那边马上就回了一个信息.
我得意洋洋地对旁边的老侯说:怎么样?网还是方便吧,这是昨晚聊天室认识的深圳美女,嘿
嘿。老侯也颇有些好奇,就是,就是,挺有意思。
这时,那边又发过来一个信息:我在昨天那个房子聊天,你呢?
噢,我刚上来,给一个哥们教上网呢,没机会跟您老人家聊天了,真遗憾,俺命不好,没这福分。:)
哈哈,说得我跟什么似的。没关系的,改天见面再聊^O^
嗯,有缘网上来相会,嘿嘿。
只见她飞快回了一句:千里网情一线牵。:)
我恋恋不舍下了线,回头问老侯:怎么样?这就叫’上网真奇妙,不玩不知道’,
明白我为啥说网这东西容易上瘾了吧。
嘿嘿,那就好,我这人现在就是无瘾可上,就***差试试白粉了。是这,你啥时候有空,替我把这套行头置上。
明天吧,下午你开车来接我,半天就搞定。
好,你办事,我放心。来,咱把剩下这几瓶酒处理了,干……
我跟老侯每回都要喝很多酒。瓶子全空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然后就听见老侯得意洋洋的声音,你小子现在酒不行了嘛,好好歇着,明儿给我干活哪。然后听到门哐当一声,我就晕晕乎乎睡着了。
昨晚酒是喝多了,今天早上骑车上班时头还是晕晕的。进了办公室,迎面见刘佳,她看了我一眼,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嗯,没事,昨天喝了一点酒。
一看就知道喝酒了,真不知道你咋那么爱喝酒。
刘佳的眉头紧锁着,稍稍抿着嘴。我耸耸肩,朝她笑笑,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谢谢。那时刘佳的脸微微一红。我突然觉得,她这个表情真漂亮,很可爱。是啊,被一个女孩子关怀着,对谁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呢。只可惜,这个刘佳,我和刘佳……哎,我也不明白。
上午的工作还是老样子,从一堆资料和报纸里整理出我们要的东西,然后分工,写完之后互相校对一下,交总编大人签个字就完事。这活儿是如此之机械化而易操作,通常我花两个小时就搞定了。那么剩下就有充足的时间试图数清楚刘佳头发的数目。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件事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就是管体育版的小龙会经常跑过来请教若**已经在网上球迷论坛阐述过的问题。
这不,这小子又来了,哎呀,阿飞,你来帮我看看,这陈亦明事件的新闻标题咋起好呀?
我伸手抓过稿子,嗯,《陈亦明足球之夜大鸣冤》,这个题目早上好几家报都用了,我给你想一个火爆点的咋样?
行呀,你说。
’陈胖子痛失贞节意铿锵,张大嘴**未遂语惆怅’,用来形容陈亦明受罚那难受劲和张斌想套新闻的迫切劲,贼贴切。
得,你饶了我吧,这上了报咱主任非扒我的皮不可,你给换个’素’点儿的行不?
哎,好东西你接受不了嘛,那就这个吧,’张记者贴身逼抢,陈教练大脚解围’,行不?
好,好,这个要得,高!咳,还是咱阿飞行,张嘴就来,嘿嘿。
刘佳转过身来,哼,你就不务正业,成天吃里扒外,干脆让你去体育部算了。我笑眯眯地盯着刘佳的眼睛,不会吧,这么打击革命同志,我可是从来没耽搁咱家那一亩三分地呀。我特意把咱家加了重音,刘佳一下子脸又红了,瞪了我一眼,转过头去。我凑过去,轻轻拍了她一下,压低声音说:今儿下午咱安排出去采访民间文化活动。刘佳也轻轻地说:瞧你这鬼鬼祟祟的架势,下午又要去修哪个栈道奔哪个陈仓?嘿嘿,我去给我一哥们帮忙买台电脑。那就又让我一个人去?这回不用,反正内容心里有数,明儿我直接编出来,你下午逛街回家都行。但咱们中午得一块儿出去,别露馅把我卖了。废话,我要卖你,你都死了500回了。是是是,咱是革命战友嘛,我要犯错误,你当然得掩护。刘佳扮了个鬼脸,扭过头去,她的一头长发便又气势恢宏地从空中舞过,并且轻轻地拂到我的脸上,呵,痒痒的。
中午按计划和刘佳出了报社,跟老侯接上了头,我说:谢谢刘佳同志掩护,你下午干啥呀?
没事回家呗。刘佳的表情有点无奈。
我说那要不陪我们一块去买电脑吧,刘佳便开玩笑说:不会吧,这么就想拉一短工苦力呀。老侯这时却连忙跳下来,咳,来来来,算给我帮忙,晚上我请客。然后殷勤地给刘佳拉开了车门。
下午给老侯收拾好了机子,又教了半天,老候终于知道怎么上线浏览了,于是兴高采烈地宣布:祝贺中国诞生一位新网民,今晚上地儿随你俩挑。
吃饭于我们似乎往往意味着喝酒,如果说昨天我发现自己酒量下降了些,那么今天的另一个发现就是酒瘾却在持续增长着。今天喝得更多了,后来只记得刘佳似乎生气了似的,问我是不是要酒不要命了,还隐隐记得老侯送我回家时悻悻地说:你小子,命真好,我要有刘佳那样的女孩子,成天喝凉水睡地板都行。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中途不知怎么醒了,口干得厉害,从桌子上摸了杯子,里面是不知什么时候的茶,端起便喝了两口。这时,城墙上又传来了画家的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