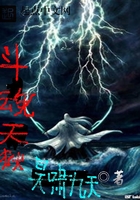每年三月有风起,抚青山拂杨柳,如隔壁老王家的儿媳妇温柔如水,轰隆隆的春雷破开天地间的混沌阴晦,如隔壁小王发现婆娘出墙暴怒如雷。
老天爷发了个温和而不容拒的号令,于是老农抻着懒了一个冬天的懒腰下地耕田去,老兵将抹好油的朴刀放入刀鞘准备杀人去,老蛮子吆喝着御马南下抢掠杀人去。
云中城隶属秦国通常被称为山内的云中郡,与蛮子所在的大草原仅一山一水之隔,却是扼住蛮子咽喉的一只手,属于蛮子的眼中刺肉中钉,是蛮人每年南下必攻之地。
一山为阴山,一水为武泉水,大草原本名大草原。
秦国人想着给大草原改名,蛮子想着让云中城回到世间。
为此,边疆长年纷战不休,同时边城人也自然悍勇热血,胆小的要么被吓死或者杀死,要么携家带口南逃了。边城人常说割脖子掉脑袋碗大一块疤的事儿,每家每户长年备着棺材、明幡,香烛等一应丧葬物事。每年三月蛮子南下掳掠当做每年的割草时,像割草一样一茬茬的收割人头。他们生活在死的阴影下,向着生的光明努力靠拢。
每年大多数人都做着与往年一样的事。老树发新芽,纤细枝条稀疏嫩叶下逗弄蚂蚁的年幼顽童做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事。他认真仔细的看着蚁巢洞口附近进进出出的蚂蚁,在数个时辰之后用石头把洞口堵住,开心的拍拍屁股走了。他想这会儿缺哥儿应该回来了,下次会带我去……割草了吧。
“缺哥儿,这刀又得修修了吧。”
“割草多了嘛,也容易崩了刀口,你姨还不给你换口好刀啊?赶明儿到明叔铺子来,明叔给你整整。”
“明胖子,这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缺哥儿这刀我帮他整,有你什么事儿啊!”
“嘿,齐大白话别扯呼呼,谁和你朋友啊,这事儿只有我能办,你——办不了。”
明胖子和齐白话是分居城东城西的两个铁匠,一年上头碰不见几次,每次见面都是针锋相对,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快的。
今天能碰见是因为割草的人回来了,按着往年的习惯,割草回来,百姓夹道相迎,割草最多的人,会被称为边子,武器会由边军出资维护或更换。只是这计数的不是草的堆数或重量,而是血淋淋的人左耳。
两人看着寥落狼狈的队伍及路中牵瘦马穿破衣缓行的清秀少年,看着他脸上身上的血痕,看着他拘谨腼腆的笑容,笑着笑着哭了。
“明叔,齐叔,我会铁匠活儿。”少年把明胖子身旁的小孩放在马上,朝这一把年纪却在不知羞的抹着不知眼泪鼻涕的两人笑了笑,朝着周围也在抹着眼泪的人笑笑,跟着队伍继续向军营走去。
小孩儿朝他们挥手,缺哥儿说了,会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人们闻言,摇摇头抹干净眼泪笑着各自回家了。此时,云中城的阳光正暖,这样可以暖暖的烘干眼泪。
在淳朴简单的边城人看来,能够杀死敌人、保护他们的人就是好人,对于好人,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去让他变得更好,杀更多的敌人,也愿意为了好人去杀人。
在今后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里,边子会背负边城人生存的野望,继续杀人,直到被杀。
少年去军营交了草,领了与草相符合的银两,接过军长偷塞过来的一块沉甸甸黑黝黝的石头,和众人打了声招呼,牵着他的那匹瘦马走了。
少年牵着瘦马,瘦马驮着小孩儿,在云中城里转了一圈,置办了些物事,告诉他长大了才可以去割草,捏了捏他的脸回到了家中。
云中城除了少部分用青砖堆砌的城墙外,四合及城中房屋都是由黄土轧实的砖垒成。黄土砖易碎易塌,所以坊间房屋皆较低矮。就像边城人,整天都是微躬着身子驼着背,恨不得钻进泥土里。边城多战,军士身子微躬可以更好的隐藏行迹,行动更为迅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战时最大可能的活着。
少年走进街尾门前有一棵蓊郁的槐树的院子,反手把咯吱作响的木门关好,将刀从背后取下。一道寒光闪过,缺哥儿拔刀出鞘,挥刀将直飞面门的三只箭挡下,右脚一跺地面,在灰尘扬起之前便欺身而进,靠入射箭之人怀中。
缺哥儿将刀置于地上,伸手抱住面前清丽的少女,用他的脏脸贴着她干净白皙的脸说:“姨,我回来了。”
“小屁孩儿,一回来就占老娘便宜,赶紧把银子交出来。”少女推开缺哥儿,伸手在他怀里摸索一番,将缺哥儿刚领的二十两银子尽数搜刮了去。“把脸擦擦,热水烧好了,去洗澡吧!”
缺哥儿接过热毛巾,将脸上因为几天奔波杀人留下的血污灰尘擦净,露出了清秀干净的眉眼,笑望着余乐儿,也不急着去洗身子。
“又占老娘便宜,你不怕天打雷劈啊!”余乐儿微恼微羞地踮起脚尖在缺哥儿嘴上亲了一下,嘟囔着:“二十两银子亲一次,赚了!”
和往常一样,割草回来两人没有兴奋之类的情绪,没有过多的话,神情也有些沉重。每次割草都会死人,这割草的刀挥起来,伤人也伤己。
“杀了两头野狼,割了十三斤草,城西的卓子、铁蛋、二根,城东的明三死了,老王失踪。”
野狼不是真狼,是蛮人骑兵的小队长,一头野狼值二两银子,同时也代表着四十到五十斤草。余乐儿惊惧地看着余缺,一时不敢相信所听到的消息,感觉阵阵寒意袭来,似料峭的春风灌进衣裳般冰凉,不禁压实了被沿,身子蜷成一团缩进了缺哥儿怀中。
大草原与山内间有一山一水之隔,无论是秦人还是蛮子想要攻打对方都要越山绝水。武泉水面宽阔,水流湍急,人马一旦落入,连个漩涡都不会出现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生活在“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的蛮人没有足够的木材制船,也不会制船。每年饿得发昏的蛮人只有穿过阴山中的峡谷隘口,冲破骄傲悍勇的秦军的重重围堵才能南下,才能抢到能让他们度过牲畜尚幼的春天的口粮。
往年那些草原上的狼都会弃云中城这块咬了会崩牙的硬骨头于不顾,仅留下小部分的骑兵用于骚扰牵制,大部队则转而攻向其他的小村庄,在搜集到足够的粮食和女人之后,男人孩子老人杀光,村庄焚毁,按着原路返回。
今年新长的草已经割了三次,已经杀了八头野狼,割了上百斤草,这背后代表的蛮子已经超出了往年的数目的几倍。
或许,这是一次新的战争。
“活着回来,你说过要看我出嫁的。”吹熄了灯烛的房间里,余乐儿抱着缺哥儿的臭脚正在说着梦话。
活着的愿望或者说野望,只有在梦里才敢说出来。
余缺把头蜷进被子里亲了亲乐儿冰凉的脚丫子,朝胸前拢了拢,想道:乐儿姨,我会活着的,可是我不想看你出嫁啊。
屋外有风刀子割过,青绿的槐树叶落下,淡白色的小花在深黑的夜里摇曳。
三月春风似剪,裁人头如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