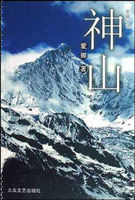那日黄三金闷闷不乐地坐在家里,心想女儿久无下落,在刘大人那里如何交代。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主动些好,以免又生出枝节来。正好盐号无事,他带上牛二,坐上马车到长江县衙去拜会周大人。
周成本以为给刘公子牵线搭桥,讨刘大人个欢喜,没料黄小姐突然出走,他的颜面也随之丢尽。见黄三金突然来访,还一再求他在刘大人面前给打打圆场,气便不打一处来。
黄三金沮丧地道:“小女脾气太倔,就是死,也不会答应嫁刘公子的。如今小女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我也急得走投无路了。”
周成却道:“你家小姐脾气倔,我告诉你,刘公子脾气更倔了!这事在刘大人寿宴上是你亲自允诺过的,该怎么办你自己向刘大人说去。”
离了长江县,黄三金无奈之下,索性厚着脸皮去向刘大人赔罪。
车进遂宁城天已黑尽,他不便去刘府讨扰,便在常住的兴隆客栈定下房间,而后只身来到东大街的四海春酒楼,在楼上寻了个清静的位子坐了下来。
小二是认得黄大掌柜的,很快上了酒菜。黄三金自斟自饮,想着近来发生的倒霉事,很觉晦气。喝了一阵闷酒,黄三金内急,起身上茅厕小解。返回时途经一雅座包房,听得里面传出熟悉的说话声来。
“这些小事,你就放心好了。”是盐监官卢禺的声音。
黄三金停下脚步,就着窗棂向里看去,是卢大人与一衣着体面的男子在喝酒,两个烟花女子陪着。那男子黄三金是认得的,姓瞿名天成,江南盐商。此人官盐私盐两边都做,轻车熟路,左右逢源,从没翻过船。黄三金晓得瞿天成是个有本事有背景的人,也曾大着胆子与他往来,互益双赢,确也得过不少好处。
又听瞿天成在说:“鄙人就要卢大人这句话,其他事情,我自会处置。退一万步说,即使有啥闪失,也决不会牵涉到你卢大人的。”
卢禺的声音:“牵涉我什么?我做了什么了?”
瞿天成:“是呀是呀,我明白我明白。”
听到这里,黄三金急步走回原座,草草吃完喝尽,了账下楼。
次日黄三金到刘大人府上拜望,却见卢禺早已在客厅坐着了。他拜过刘大人,又向卢禺施了一礼,而后一旁落座。刘大人随即问黄三金道:“黄小姐可有消息了?”
黄三金长叹一声,竟然落下几滴泪来:“凡是可能的地方,我都派人去找过了。事到如今,我已是无可奈何,今日特意向刘大人赔罪来了。”说着,泪流满面,扑地跪了下来。
刘元朝扶起黄三金,叹息着说道:“听别人说,你家小姐早先曾与广运盐号的少掌柜罗通达有过婚约,既是这样,那日你就不该答应周大人,又将小姐许与我那犬子了。”
黄三金听了便又扑地跪下,哭道:“我家小姐与罗家大少爷实无婚约,只是早先家父在酒席上的一句戏言,两家都未曾当真过的。请大人明察。”
卢禺也便说道:“这个内情下官也略知一二,黄罗两家确实未曾定过婚约。”
刘元朝又长叹道:“如今黄小姐生死不明,再说,即使小姐找到了,也未必会回心转意的。我真不知道来如何处置了。”
黄三金见刘大人如此说,便欲趁势将退还彩礼的事说说,不料公子刘义闯了进来。
见了黄三金,刘公子口呼岳父大人,倒头就拜,泪如雨下。声称不管黄小姐是死是活,都是他刘义的人。生,他要大礼迎娶,死,他要厚礼安葬,反正他要要人。
刘公子要死要活,疯疯癫癫,黄三金确也未曾料及。任他哭闹了一阵,刘大人唤来两个衙役,好歹将公子拉走了。
经刘义这么一闹,黄三金本想要说的话反倒不好说出口来。寻思再三,他将卢禺看了看,犹豫着掏出一张两千两银票,双手捧给刘元朝,说道:“这是在下一点心意,请刘大人笑纳。”
刘元朝眉头一皱,没接,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看你还是再设法找找吧,实在找不着小姐了再说不迟。”
黄三金也便告辞,卢禺说他也要回蓬莱去了,于是二人别过刘大人向外走去。刚到府门口,就见刘夫人陪着一位老尼走了进来。二人又向刘夫人问候过,才一同去了。
这老尼就是静业禅院的住持惠果法师,黄三金却不认识。
卢大人说,这惠果可是个十分了得的比丘尼了。虽然一个女流之辈,她却曾云游四海,历经天下名山,还曾去过缅甸、暹罗和印度,深得佛学奥理,颇受人敬重。加之尤能善解人意,为人排忧去烦,因而大凡官宦、殷实人家的女眷没有不去静业禅院进香,向惠果法师讨教的。
知府刘元朝的夫人便是惠果法师虔诚的俗家弟子。那日一早,刘夫人带着丫头来到静业禅院,惠果迎着,给菩萨上过香后,请进禅堂坐了,刘夫人便哭哭啼啼地述说起满肚子的烦恼来……
惠果已知究竟,口念阿弥陀佛,说道:“人生在世,凡事随缘。原非己有,不可强求。否则自寻烦恼,尤恐祸及自身。”
刘夫人便说,如今公子已为黄家小姐走火入魔,谁也劝他不住。夫君已是无可奈何了,恳请法师到府上坐坐,以佛法开导公子,或许他能翻然醒悟。
惠果道:“公子心中无佛,岂是佛法开导得了的?”
刘夫人跪了下来,恳求再三,惠果也便答应了。
这天一早,刘夫人去静业禅院接了法师回来,刚进府门就碰上黄三金和卢禺从里面走出。打过招呼,刘夫人低声对惠果说道:“那位就是黄小姐的父亲黄大掌柜。”惠果回头看去,没料黄三金也回过头来将惠果看着。惠果道了声“阿弥陀佛”,返身进去了。
刘元朝本是个谦恭厚道之人,对惠果也特别的敬重,见法师到来,赶忙迎进客厅坐了。家人沏上鲜茶后,刘大人欲言又止,心中似有莫大的苦衷。
惠果便道:“刘大人公事已够操劳的了,还为儿子之事如此伤感,善哉善哉!”
刘元朝道:“也许是本人前世之过,才养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报应了。”
惠果道:“佛说万世皆空,刘大人凡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心情自然会好些的。”
刘夫人便要家人去将公子唤来,没想刘义却自来了,手中抱着一大叠纸。
刘元朝即令刘义拜见惠果法师。刘义拱了拱手,道:“给师太请安!”
惠果便问:“公子手中拿的什么?”
刘义道:“是我请衙门口二神仙写的寻人招告。我要令人到各县张贴,找不到黄小姐,我也不想活了……”说着便傻痴痴地流下泪来。
惠果见刘义如此,问道:“你与黄小姐可曾定有婚约?”
刘义道:“长江县令周大人做媒,她父亲黄大掌柜是应允了的。这算不算数?”
惠果道:“只是口头说了,而无一纸婚约。你父亲是知府,他就晓得这是算不了数的。再说,我也听说那黄小姐并不愿意这门婚事,方才离家出走,生死不明的。”
刘义便嚷了起来:“我不管!自古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黄大掌柜答应了,黄小姐就是我的老婆,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到她!”
见儿子耍起横来,刘大人气愤已极,骂道:“你给我滚!”
刘义哭嚷着找人张贴寻人招告去了。眼看开导之事成为泡影,刘夫人不禁泪如雨下。惠果却道:“刘大人、夫人,不必气恼。公子性情乖戾,一时难以扭转。佛说‘随缘起佛刹,音声不可尽’。依贫尼之见,‘顺应机根之缘而定行止’,还是随缘的好。”
听惠果法师这样说,刘元朝心想也只能如此了。那逆子要折腾就让他折腾去,一旦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总会罢休的。
当天,刘公子便派了仆役到各县张贴寻人招告。其后不几天,又才生出前面所述罗通达在灵泉寺山门处遇险的故事来。至于惠果法师为何突然现身救了通达,又在渡口开导于他,其间自有隐情。
黄三金与卢禺辞别刘大人后,相约一起回蓬莱。二人同乘一车,徐徐上路。
见黄大掌柜一路上郁郁寡欢,卢大人揶揄道:“我说你黄大掌柜呀,当初何必非得要把小姐许与刘公子?罗家少掌柜多好个人哟,你却硬要棒打鸳鸯。现在如何?”
黄三金埋头不语。
卢禺又说道:“千年的衙门流水的官。我在官场混十来年了,见得也多了。官场凶险得很哩,还不如趁着这年头生意好做多捞些钱,安安稳稳过日子。”
黄三金抬起头来看了看卢大人,却不言语。
卢禺意味深长地笑着:“我看你家小姐跑了也是好事。你看那刘公子,傻乎乎疯癫癫的,要真是嫁了他,可就把黄小姐害苦了。”
卢禺确也说了句实在话,黄三金何曾没这样想过呢?不过,要回过头来顺了梦瑶的心思嫁到罗家去,那又是决然不行的。他与罗家有怨,有仇,势不两立。
黄三金苦苦地笑了笑:“别说这码事了。”
马车慢悠悠地行进着,黄三金突然想起昨晚在四海春酒楼偶见卢大人与江南盐商瞿天成密谈的事来。他故作不知,说道:“卢大人,那个瞿天成前日又来找我了,说还要五百担干路货。”
所谓“干路货”是道中行话,就是私盐。逃了官家的税银,还有不净赚的?故有此说。
卢禺有点异样地盯着他。黄三金道:“他的胃口也太大了点吧?一月前已经给了他五百担,我已是提心吊胆的了。即便你卢大人睁只眼闭只眼,一旦他在外面犯了事,还不把我也牵了出来的?”
卢禺心中不悦:“哪个睁只眼闭只眼了?谁要是走私贩盐那可是法不能容的,你黄大掌柜可得要小心行事了。”
黄三金即道:“是呀是呀,本人断然不会去以身试法的。”停了停,又道,“我不会再给他了。再说,做干路货我又能多得几个?冒这样的风险划不着,搞不好把老本都赔了进去。”
卢大人笑而不语,黄三金也笑了起来。
黄三金算是把卢禺这个盐监官吃透了的。这厮插手私盐勾当手段高明而隐蔽,在本地各盐号大掌柜面前从来都是一副正经的面孔,即便只有他二人在场,还得要戴着假面具说话。这还不好笑么?
黄三金笑罢便不言语了。卢大人却又想起翠娘来。他回忆着那夜与翠娘颠鸾倒凤的情景,品味着翠娘那万种风情的滋味,心里就直痒痒。突然说道:“你太太好多天没去看她姐姐了,她姐怪想她的。”
黄三金心里只觉一阵酸楚,却道:“好的,过两天我一定陪太太到府上拜望。”
车到蓬莱,就见一遛子十来辆马车满载着食盐迎面而来,一看盐袋子上的印记便知是广运盐号的车队。少掌柜罗通达远远看见卢大人和黄三金了,从车队后面急步赶来,拱手致意。
但见罗通达面色蜡黄,卢大人说道:“我看少掌柜病未大愈,怎不多调养些日子?”
罗通达叹道:“号子里事情太多,没法子的。”
卢大人又问:“这都是大英盐场出的货?”
罗通达:“是的,船在码头等着,十几辆车要跑好多趟才拉得完的。”
“好好好。”卢大人赞道,“看这气势,你们广运真是洪福齐天了!”
罗通达淡淡地笑了笑,问黄三金:“黄伯,梦瑶还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吗?”
“她早死了。”黄三金不看通达,却对车夫说,“走!”
马车快速驶进城去。
黄三金一脸阴沉,他太不服气了,凭什么罗广仁就能在大英那谁也打不上眼儿的山沟沟里凿出最好的盐井来?忌妒和仇恨充塞着黄三金的心,回到家后看见啥都不顺眼。丫头玉容好心泡来鲜茶,他竟一扬手拂在地下,“啪”的一声将茶杯打碎了。
翠娘不满地睖着黄三金:“谁惹你了?”
吴氏赶来,问道:“刘大人那边的事办得怎样了?”
黄三金忽地嚷了起来:“滚,都给我滚!她死了,就当她死了!我根本没生过她这个女儿!”
他伤心地流下泪来,倒在床上一觉睡去。这一觉直睡到翌日近午方才醒来,翠娘“哼”了一声,说道:“我还以为你就睡死了呢!”
就听牛二在房外说道:“大掌柜的,卢大人送来了帖子,说是请你和太太过去吃晚饭。”
“不去!”黄三金断然道,“你就说,太太病了,我没空。改日登门拜访。”
翠娘冷冷一笑:“你干脆说我死了好了!”
此后几天,黄三金白日里跑盐场,到晚来便蹲在号铺里。院子里死一样沉寂,吴氏成天关在房间里,也没见她再提起梦瑶的事来。翠娘则逗着玲儿找乐子,偶与男人喝两杯消消闷儿。黄三金看似消沉着,其实他心里一直鲠着哩,他与罗家的恩恩怨怨难道就这么算了么?
这天傍晚,黄三金正在号铺里坐着,突然走进一个胖罗汉似的人来,笑道:“黄大掌柜,今晚我请你喝酒,肯赏脸么?”
黄三金抬头一看,是荣生盐号大掌柜莫道全。
“莫老弟,今日怎么想起请我喝酒了?”
“你黄大掌柜想不起请我,我还想不起请你吗?”莫道全道,“走吧,好久没聚了,喝两杯。”
说来莫道全与黄三金交情也还不错。尤其是近几年,黄三金盐场不断扩大,生意越来越红火,而且与盐监卢大人也走得很近,莫道全看着就眼红,故而时时约上黄三金喝几杯。癞子跟着月亮走,沾个光。
黄三金心想这胖子一定有事,不然咋会无缘无故来请他喝酒了。他欣然应允,从柜台里走了出来。
二人来到悦来酒家,在楼上清静的地方坐了。莫道全点了几样菜肴和一斤射洪烧春,二人便你来我往喝了起来。酒过三巡,胖子忽然神秘起来,压着嗓门说道:“黄兄,你知道不,广运的大英盐场真是神了!”
黄三金纳闷了:“你说什么,大英神了?”
莫道全:“罗老爷子在那山沟里凿出的是神井,叫七星……什么井,没人见过的。”
黄三金仍纳闷着,直直地将莫道全盯着。
胖子寻思道:“那天下午你和卢大人不是去大英盐场看过么?你就没看出其中的奥秘来?我想既然是‘七星’,那一定是七口井了。”
黄三金断然道:“不对。是八口,每口井我和卢大人都细细看过,与我们盐场的井没什么两样,就是盐卤出得多罢了。”
莫道全想了想,问:“那天罗大掌柜有没有跟你们说起‘七星’什么井这样的话来?”
“没有,绝对没有。”黄三金笑了笑,“你是哪儿听来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莫大掌柜叹息道:“怪了怪了,这可是罗家二少爷亲口给我家春生说的。”
原来罗通才的烂兄弟莫春生就是荣生盐号老板莫道全的少爷。那天与莫春生、田丰雨酒喝到兴头上,罗通才冲口而出,将“七星卓筒井”说了出来。当晚被通达一阵责骂,酒便醒了大半。通才后悔莫及,担心生出什么祸事来。但他又心存侥幸,那晚莫、田二人都已喝得七八分醉了,还能在乎他说了什么话么?罗二少爷想错了,莫春生这小子却依稀记住了他这话,却又没记全。第二天在饭桌上便当奇闻讲给他爸听,没想竟引起了父亲的警觉。
黄三金不再笑了,愣了愣,突然说道:“算了,不说这玩意儿了,我不感兴趣。喝酒喝酒!”
“咋没兴趣了?”莫道全非常失望,说,“我约你来喝酒,就是专门要给你说说这事的。我想你是去大英看过的,有什么神秘之处你肯定清楚。”
黄三金道:“我真的不清楚。不信,明日你亲自去大英看看好了。”
莫掌柜觉得黄三金不像是真心与他打交道,便不再说大英盐场的事儿,而接下来的酒也就喝得不怎么痛快了。
黄三金回到家里神情便显得有点古怪。愣愣地坐在床边,时而“嘿嘿嘿”地笑笑,时而又木然不语。翠娘道:“你这是咋了?”
黄三金没理,摇摇头,又晃晃头。翠娘甚觉奇怪,她哪里晓得,此时他男人正在回忆并琢磨着那天与卢大人一道在大英盐场的每一个细节。就见他“唔”了一声,脸上腾起了笑。
翠娘轻轻掴了男人一巴掌:“三金,你发神经了?”
黄三金摸了摸脸,狠狠骂道:“妈的,老子很可能又给罗老爷子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