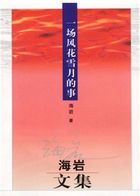常言说,秋裹伏,热得哭。伏天恰巧又是秋收的时候,社员们都在烈日下劳动,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裤,他们全然不顾,往往因为一点活路要抢着做完,就会推迟吃饭的时间。这几天,史正仁也不再蹲在家里听唱机了,他一早就趁凉快出去走一趟,这样一来可以使别人不敢出工慢,另一方面也可以标明他这个干部十分关心生产。但一到中午,他不是在东家乘凉,就是在西家睡觉。近几天来,他到生产队公猪饲养场去的时间是最多的。这公猪饲养场真是一个好地方,它修在一个山梁的垭口上,地方较偏僻,四周长满了树木,特别是那几间敞屋,过堂风从中间吹过,要是搭上一把椅子,坐在那里喝茶、摆摆龙门阵什么的,那真可以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但这还不是吸引史正仁到这里来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那个新上任不久的饲养员,一个年仅十九岁的漂亮女子。这姑娘真的很招人喜欢,她没有曲线的风韵和高高突起的胸脯,也没有招蜂引蝶的打扮,她有的只是朴实。梳两条不太长的发辫,细线条似的重眼皮内,一对乌黑发亮的眸子,每逢对人说话时,微笑的脸庞上总会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她的身材很苗条,虽经太阳曝晒,皮肤仍然显得非常白净,一双细嫩而微带茧疤的手,是她勤劳的见证,她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特别是在长辈面前说话时,她从来都是恭恭敬敬的。这年头,很多女孩子说起话来都是一口脏,从不吃“素”,但从来就没有人听见她说过一句带脏的话。老太爷老太婆们都说这个姑娘很滋润本分,很守规矩;年轻小伙子们都说她很可爱;中年人们都说她很沉着,很稳实。正因为这样,大家又鉴于这些年来凡喂公猪的人不偷就拿的苦恼,便让她担任了饲养员。她到任两个多月来,工作挺积极,公私分明,干活踏实,猪草砍得细,猪食子煮得烂熟,清洁卫生也打扫得很好,大家都觉得挺满意。她叫潘淑贞,是本队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太婆张王氏的外孙女儿。那张王氏一生养了一儿一女,女儿老大,解放前就出嫁了,后来儿子又死了,因此在淑贞两岁上,张王氏就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站,距今已经十七个年头了,淑贞也一天比一天长得可爱了。张王氏的规矩礼行特别大,家教特别严,淑贞从小就是在外婆的严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别看张王氏人已经老了,却是个挺爱干净的人,又节俭朴素,衣服上补得疤重疤,但却洗得出奇的干净,家里的东西都是摆放得一层一序的。她有个火炮急性子的个性,亏也吃得,可就是受不得半点冤枉气。她待人接物很大方,也很好面子,可惜人老了,她的这些美德只能从外孙女儿淑贞身上体现出来。
早在前一年,史正仁就看上淑贞的姿色容颜了,但那时淑贞还在读书,没有下手的机会。后来毕业了,又由于张王氏对淑贞的管教极严,每逢没事天黑不回家或是随便和别人说说笑笑什么的,那都是不行的。张王氏常说:“我们那些年,十四岁就是出嫁的头道年月了,十六岁是二道年月,十八岁就没年月了,成老女子了,嫁都嫁不出去了,哪像你们现在这些女子,二十几岁一个一个的还晚上晚上地不拢屋,没规没矩的,像什么话。”淑贞也从来不反对外婆的意见,而且她也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因此,史正仁虽然常常每见淑贞就心里痒痒的,但总觉得不便下手。现在,潘淑贞被安排在这样一个好的地方,他真是喜出望外,他甚至埋怨自己有些蠢,怎么先就没想起让她来做这个活路呢?
这天吃过早饭,淑贞去坡上捡了一捆柴回来晒好,刚坐下歇了一会儿,史正仁来了,说是要看看近来生猪的情况如何,淑贞忙从屋里搬了一条凳子出来放在敞屋里说:
“正仁表叔,你先坐坐吧!天这么热,我去给你烧些开水哈!”因为张王氏老太婆从来就不习惯叫官衔的,无论年龄的大小,她都以辈分来叫什么爸、叔、姑、婶、哥、姐的,所以淑贞根据前辈的习惯,也叫史正仁“表叔”。
史正仁说要先去猪圈看看,淑贞便去给他开了门,又引他去猪圈走了一趟。出来后,史正仁便坐下给淑珍大谈猪要如何养什么的,还教育淑贞要大公无私。他说:“养公猪这件事,就是要和粮食、柴草这些家里同样需要的东西打交道。以前的几批人,所以都干不长久,就因为他们都在这方面过不了关,你一定要注意,你是一个青年团员,前途还很远大,一定要好好干下去。”
在史正仁面前,淑贞显得非常拘束和恭敬,对于史正仁的话,淑贞都把它当成指示似的记住了。工作上的正事谈完了,史正仁就开始谈生活和一些家庭琐事,最后甚至问起淑贞的个人问题来,淑贞觉得史正仁今天话特别多。边谈,史正仁还不住地用手比比划划,显得很亲切。
“你外婆对你管教得极严,你习惯吗?满意吗?”史正仁问。
“她老汉家说的、教我们的都是好话,有什么不满意的,很习惯的。”淑贞回答。
天快晌午了,史正仁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走了。
一连几天,史正仁都要来这里坐坐,谈论的也不是些什么要紧的事,淑贞觉得太耽搁她的时间了,但又不好说,只好在史正仁走后加油地去干一阵,有时甚至回去还赶不上吃饭。
一天,淑贞喂完猪,又把屋里屋外的清洁卫生打扫了一遍,刚放下扫把把脸手洗过,突然发现大母猪不知怎么把圈门给拱开了,她正准备去关猪圈门时,史正仁来了:
“怎么,打扫得这么干净,要迎接客人啦?”
“太脏了!”淑贞笑笑,照样又去给史正仁抬凳子。
史正仁坐下后,淑贞发现那头大母猪已经把头伸出了猪圈门,她正想去关时,史正仁叫住了她,要她歇一会儿,说有事和她谈谈,淑贞只好也找个凳子坐下。史正仁就又问些老生常谈的话,眼睛却不住地看淑贞,淑贞觉得很有些不好意思,便把头低了下去。
“走,去看看你煮的猪食吧!”说话间,史正仁先站起来向另一间屋走去,淑贞也只好跟在他后边。
史正仁并没有细看,于是就连连夸奖不已,于是又顺手把门关了,屋里的光线顿时暗下来了。淑贞的心里猛地一紧,她一急,浑身发热,史正仁趁势就忙去搂淑贞,淑贞被史正仁这突如其来的一抱给吓了一大跳,她本能地叫了一声,趁着黑暗猛地挣脱了史正仁的双手,一下子把门打开,一口气地跑了。
史正仁没趣,等他出了门时,淑贞已经跑出好远了。
淑贞开始往家里跑着,她又突然觉得不对,外婆要是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她一急,脸上涌出了豆粒大的汗珠,汗珠和着泪珠,不住地往下滴。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平时那么敬重的正仁表叔,居然会在她面前做出这样的事来。但她又不敢往别处跑,只能瘫坐在回家路上的一棵大桐巴树下面,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眼看吃中午饭的时间都过了,淑贞掏出手帕来擦干了眼泪,又慢慢地向家里走去。张王氏问她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淑贞说人有点不舒服,张王氏真以为她是病了,也就没再追问什么。
史正仁怏快地往回走,他这时候的脾气特别大,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发泄一通。快到家的时候,正巧玲玲从斜路上跑出来了,她跑到史正仁面前,不住地问这问那,史正仁不理她,只顾走自己的路,玲玲跟不上,便硬要史正仁背她,史正仁此时哪里肯背,要她自己走,她不走,史正仁一时火起,狠狠地打了玲玲一个耳光,玲玲在路旁大声哭起来,边哭还边一个劲儿地喊“姑姑”。
春英听得喊声,只以为玲玲摔着了,她紧走几步,把玲玲拉起来,这时史正仁已经走得远了,春英问玲玲:“你怎么了,给姑姑说说。”
“爸爸…爸……爸……打……打……打我——”玲玲哭得更加厉害了。
“别哭了,别哭了,来姑姑抱。”春英抱起玲玲继续走路。
史正仁走后,养猪场就没有一个人了,可猪圈门还没有关,大母猪趁机溜了出来,这母猪本来再隔一月时间就要下小猪了,所以行动很不灵便,一脚踩空,竟掉到粪坑里去淹死了。
当天下午,又该去喂猪了,但淑贞一想起养猪场就有些后怕,她本来不想去的,但是,喂猪这活不比其他活,缺一顿也是不行的。于是,她只好硬着头皮,颤巍巍地又来到了养猪场。
当她再去给母猪喂食时,发现圈里已经没有猪了,她这才猛地记起自己上午还没来得及关猪圈门就被史正仁给搅和得走了。
她慌忙各处去找,菜地里、谷子田里、坡上等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有大母猪的影子,她突然想起了粪坑,急忙跑去一看,天哪,那母猪头埋在粪水里,肚子胀得像个鼓,浮在一坨粪渣子的旁边。淑贞用粪筏子一攀,是硬的,她知道大母猪已经被淹死了。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失声痛哭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社员们都急忙赶到现场,大家又动手把死猪捞了起来。淑贞一见死猪,又想起上午的事来,哭得更加伤心了,社员们看不过,都劝慰她,但淑贞总是哭个不停,几个好心的女社员又把她扶回家去,另外几个人又帮着把其余的猪喂了,把死猪埋了。
史正仁听说饲养场死了母猪,而且是一头马上就要下小猪的抱窝子母猪,他这下可得意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召集社员开大会。会上,他说尽了大话,又算了损失账,最后说还要看淑贞的态度。如果态度不好的话,那就是十足的搞破坏,挖社会主义墙脚。淑贞也不敢说什么,张王氏觉得外孙女儿也太不争气了,不但给队里造成了损失,还弄得一家人都没面子,一气之下,病倒在床上。
会后的第二天,淑贞照样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了饲养场。
不一会儿,史正仁又来了,为了不把事情弄僵,他先劝起淑贞来:“工作嘛!哪有不出点毛病,有我担保,你就不必顾虑太多了吧!昨天晚上嘛,那是开会,不说几句怎么行呢?再说,人多嘴杂,群众的话不好说呀!”
淑贞因为前几天的事,心里一直是惴惴的,但眼前是自己的领导,她又不得不说两句话,况且人家又是这样地关心自己。
她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说明愿意赔偿损失,史正仁却尽量说得没事人一般,而且还开起玩笑来,说着说着,便又动手动脚地耍起流氓手段来,淑贞还只是不依,史正仁见淑珍还是这样,便装出大怒的样子。他骂淑贞不识好歹,没良心,可杀不可救,“赔,你赔得起吗?你知道一头马上就要下儿的母猪得值多少钱?就是把房子卖了也不够赔的。再说,这难道就只是个赔的问题吗?我看最起码还要从思想上找原因的。”淑贞本来就是一个胆子极小的弱女子,一听这些话,连气带吓,一急,竟昏过去了。史正仁见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把淑贞抱到一间堆放柴草的空屋里,在地上垫了张砍猪草用的簸箕,把淑贞放在里面,又去舀了点凉水给淑贞灌上。淑贞慢慢地醒过来了,眨了眨眼睛,又吃力地翻了翻身,然后用哀求的语气说:“正仁表叔,我求求你,求你不要……不要……”
史正仁见淑贞醒了,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狞笑。他哪里肯放过这一机会,便不顾一切,忙忙地关了门,向淑贞扑去。
史正仁死死地把淑贞压在身下,几下就扒光了她的衣裤,然后又脱光了自己,野蛮地骑在了淑贞的身上。淑贞拼死拼活地挣扎了一番之后,终于失去了任何反抗能力,两行眼泪齐刷刷地从她的眼角流出,在还残留着猪草残叶的篾簸箕里留下了两滩湿印。
屋里黑暗极了,没有丝毫的阳光,也没有一丝风,有的只是黑暗,除去黑暗和悲伤,什么也没有。
春英这天和玲玲一块儿在全队的山坡上转了一圈之后,没有发现有人违章进山。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收谷子,一眼望出去,连个人影子也很少见。春英在山梁上的一根桐树下的石头上坐了一会儿,太阳金光火辣的,四周一片蝉声,玲玲戴着花布草帽活蹦乱跳的,显得十分可爱。春英怕玲玲受热中暑,想给她找个阴凉一点儿的地方躲躲。于是,她想起了就在不远处的生猪饲养场,同时也想起了淑贞姑娘,想起了死猪的事,她想淑贞此时一定是很苦恼的,自己该去劝慰她几句才对。她叫过正在山坡上捉花蝴蝶的玲玲来,一同向饲养场走去。
快到的时候,春英朝饲养场看了看,门关着,除了猪在圈里走动的响声外,没有一点人的动静。她本想从岔道走开的,但调皮的玲玲已经跑得快拢了,加上太阳又晒得人身上像针扎一样的不舒服,春英还是朝这里走来了。
这座生产队的生猪饲养场,修起才一年多时间,春英很少来过,所以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还有些新鲜,何况淑贞又把各处都打扫得挺干净的。她和玲玲先在敞屋里站站,吹吹风,玲玲取下头上的花草帽,只顾玩手里才从坡上捉来的花蝴蝶,也不问这问那地说话了,春英不用去管她,便自个儿地去各处走走看看。突然,她看见一扇门掩着,里边好像还有点什么动静,便上去推了一下。
“嘎——”门开了。
“哎呀!”屋里发出一声惊叫,把春英吓了一跳,她一看地上,天哪,春英从来也没见过的一幕被一览无余地摆在了她的眼前,虽然她并没有看清楚这一丝不挂的一男一女究竟是谁,但那情景着实有些吓人。春英像被摄去了灵魂似的,大叫一声,也顾不得再去关门,拔腿就往外跑,把玲玲吓得面如土色,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慌忙地跟着姑姑跑,一边痛哭不已。
史正仁慌忙从屋里探出个头来,用一副十分惊惶的面孔向外张望了一下。他的眼睛有些羞亮,老是睁不开,当他看清楚是自己的妹妹春英和女儿玲玲,而且还没有另外的人时,他一下子镇定了许多。
“你在哭个啥子?不准哭。”
史正仁慌忙穿了衣裳裤子,赶紧向哭喊着的春英跑去,正好经过玲玲的面前,于是,他趁势对玲玲大喝了一声,然后又去追春英去了。
春英猛地回头,见是自己的哥哥史正仁,她的愤恨、恼怒一齐涌上了心头,她觉得那受侮辱的好像就是她自己,她紧闭了闭嘴唇,从牙缝里迸出了几句话:
“原来是你,卑鄙!可——耻!”春英揩了揩眼泪,又说,“我现在才真正地认识你了,我要喊——!”
史正仁听妹妹说是要喊,他心里紧了,他知道不远处就有人在打谷子,要是春英一旦真的喊开了,那岂不糟糕。春英的喊字刚一出口,史正仁就用手紧紧地捂住了妹妹的嘴,他哀求说:“妹妹,我的好妹妹,请你别闹了!我……我是你的亲哥哥呀!”停了停,他又连忙地说,“妹妹,听哥给你说,千万要听话,别闹了。我可是对你很好的呀!你人了党,还有你读大学的事,我不是都打过保证吗?你就看在同胞兄妹的情意上,看在你自己的前途上,也看在父母的情分上,别喊了吧!”他边说边推搡着妹妹春英往家里走,玲玲本来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又看见是自己的爸爸和姑姑,所以也就不哭了。
春英本来是要大喊大叫的,不想被史正仁这么一捂二劝,反倒没了主意。况且,她那易动感情、易激动的棱角,近来已被阴郁、沉闷、烦恼给磨掉了不少。她身不由己地由史正仁推着向家里走去,不知道自己脚下走的还是不是路,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