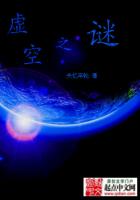初晴是东部大海之滨的一条白蛇。和一群小伙伴在白色沙滩上捉螃蟹长大。那时天蓝日丽,宁静和煦,是一大块快乐的童年时光,仿佛会永恒。
每逢退潮的时候,他们就从高高的山崖上飞快地游下来。
白得发光的海滩上和礁石下面很容易找到螃蟹。螃蟹很大,不仅吃着鲜美,枕着睡觉更是惬意好玩。
很难说那是什么年代。人们尚以笄束发,草屋早晚炊烟袅袅,大海上有小小的木舟,海边长着紫红色海草,紧接着海草的是一大片桑葚林。沿桑葚林往西山崖陡起,越来越高,摩天近十丈。山上松涛阵阵,虽然没有太多奇花异草,但也风景葳蕤,山体里渗出甘冽清爽的空山水,在崖下的石缝间形成一带淡水小溪,喝一口仿佛能永生。
白蛇自孵化出来,便以为世界就是这片蓝色、白色、绿色、紫红色、褚褐色构成的乐园,整个世界就是海浪、阳光、螃蟹、各种海虫和遥远的出海捕鱼的人类。
岂料,这天就在她和小伙伴在沙滩上追逐美味时,从海草后面忽然钻出一群男孩,至少五六人,快乐而嚣张,手持粗大木棒奔来,对着它们就是一顿乱打。一条棍子带着令人胆寒的风啸就要落到她的头顶时,被一个男孩架住了。
这条白蛇太漂亮了,打死了可惜,放了它吧!
只是差一点,她就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命丧乱棍之下。
这是初晴第一次身处人类中间。欢乐戛然而止。稚嫩而残暴的人类,轻易判定了他们的生死。每每回想,初晴都会觉得就在棍子罩顶的那一刻,自己已经被打死了。
她慌乱地爬回家,最高处的山崖,那里有一个隐蔽的洞穴,她美丽的母亲住在那里。
她的母亲,据说有几百岁了,又长又大,浑身洁白闪耀。当地偶尔有人见到她的身影,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她形容成传说中的『龙』。在收成不好的年景,会有组织地送很多食物摆到崖顶,焚香「上贡」,希望得到龙的护佑。
她的母亲,绝少出去走动。洞穴常进来山鼠野兔,洞穴附近生长着许多蘑菇药草,还有送到崖顶的丰盛的贡食,足够维持新陈代谢。她从不走远,甚至厌恶自己的洁白照亮了洞穴。一些年岁大的蛇嘲笑她的忧郁,但从不能触发她。
初晴浑身颤抖,慢慢游进蛇母冰凉的身体,紧紧偎在她的腹部。
他们都死了。她说。
噢,你越来越孤单了。巨大的蛇母只淡淡叹息了一声,好像惯见这残暴的事件。她细长的眼睛眯着,伸着长长的信子,看着遥远的往事。不要走近他们,那些人类看上去弱小,但他们会使用工具,会团结起来对付你,让你毫无尊严地死去。血腥的事发生得太多了,你要隐藏自己,才能活着,在我身边,不要走远。
从此初晴只在洞穴和附近活动,至多晚上去沙滩上捉捉螃蟹。那群男孩偶尔到山上,寻找『那条白色的小蛇』,猜测她到了哪里,长到多大,这群男孩变成老人时,偶尔经过这里,还会记着她,他们说她肯定死了,被打死,或是老死了。
她们一直活着。在越来越简陋越来越孤凉的洞穴里经历了数不清的岁月,关于龙的传说早已死亡,而蛇母更长更重了,仍像一个巨大的白色谜团。山洞就是她的牢笼,她自囚于此,从不想另谋高就。她越来越不愿意说话,但每天会不自觉地叹息几百次,在叹息声中,她的记忆越来越微弱,意识越来越模糊,有时忽然会凶恶起来,充满警备地问初晴是什么人,甚至时不时就会冲初晴张开大口,转瞬,清醒过来,又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悲伤和抱歉。
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生命对她,一直以来都是个负担。
冬眠是这条活了大概十几个世纪的白蛇所盼望的,褪皮的季节则令她厌倦。
她尤其厌恶女儿褪皮的样子,每一次褪皮都是她的「受难日」。出去!出去!记着收好你的皮!这让初晴每褪一次皮就恨一次自己。在一次次褪皮中,初晴感觉到自己也长成了一条大蛇,难以估量地大。她时常噙满泪水,充满愧疚。
褪掉的蛇皮像数不清的枯叶覆盖了洞穴的地面。
外面大多时候安静得出奇,偶尔又战火频仍。上山的人变化很大,发式,衣服,工具,变化越来越大。有一天,外面充满了争吵,一群人押解着一个捆绑着的胖乡绅,高高兴兴,推推搡搡地拥到沙滩上,几百人围观那个被绑缚的胖乡绅,他看上去不怎么害怕,倒显得有几分无辜,闭着眼睛,仿佛已经死了。一个年轻人忽然拿枪朝他脑袋开了一枪。那个肥胖的乡绅在荡漾的枪声中,脑浆溅了出来,倒了下去,附近的海浪舔噬着他的血,变成了红色。人群欢呼:打土豪,分田地!
长大,就是离别;吃人,也是离别。越来越昏聩的蛇母闭着眼睛,伸出长长的信子舔舔初晴的头。我们不能抗拒成长,但要记着,不能吃人。——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件,是几百年来唯一能让初晴清晰记住的事件。枪声响起,脑浆崩裂,海浪变成红色,人们欢叫,她的母亲平静地告诫她,不能吃人。她目睹了这个事件,但和母亲一样,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仿佛从这件事之后,饥饿像瘟疫一样传染上了这片与世隔绝的山崖。沙滩上仍然有螃蟹,山上仍然有山鼠,但所有的食物都没有以前那样多了。她时常感受到饥饿。她的母亲开始辗转反侧,巨大的沉重的身躯在身旁不时躁动。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在悄悄逼近。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上山来,一开始采蘑菇,找山药,摘桑葚,后来揭树皮,挖野菜。从山崖望下去,沙滩上拥满了人,搭鱼网,翻石礁,寻找一切可以吃的海物。
山鼠,野兔,黄鼠狼,连同蘑菇和药草很快绝迹了。
不能吃人。蛇母在黑暗中呻吟。可她的头不时昂起,她老花的眼睛仿佛又被什么点燃了,她的尾巴开始频繁地摆动。她游走到洞**又退回来,走过去又退回来,如此反复数日,终于出了洞穴。这位自我囚禁、与欲望抗争了成百上千年的巨大蛇母,像一个冰冷无情的不真实的传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甩下初晴,朝山崖下的灯火炊烟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