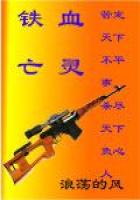当晚,程家做了一桌好菜,啤酒管够,盛情招待了恶棍们。
睡觉前,我再次被程家父子推到房里,房门外面挂上锁,插翅难飞。程学文醉眼朦胧,不但脱光了我的衣服,还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用棍子狠狠抽打我,边打边骂:“日妈的格老子,老子叫你娼!叫你跑!跑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到天上老子也能抓下来!”
我抱着头,扑伏在地,拱着屁股,让他打屁股和背,不反抗,也不还嘴。此前,狗日的还只是脱光我的衣服打。今晚,他竟然连自己的衣服都脱光了。可见,他不是喝多了,就是变态,或者恨我入骨。之前我都不反抗,此刻更不能反抗了。不然,变态的程狗子越打越重,越打越过瘾,倒霉的是我。程学文打累了,如法炮制,把我丢到床上,再次将我掐脖子强奸。
夜深了,程学文呼噜声不断,睡如死猪,正是报仇的好时机。
我悄悄起床,打开衣柜,准备拿我的切菜刀子,手刃程狗子。可是,当我摸到我那件破冬衣时,惊呆了,刀子不翼而飞。我不死心,继续在衣柜里找。令我失望的是,不但我那堆破衣服里没有刀子,整个衣柜找遍了,也不曾找到我暗自藏下的雪恨之工具。我明白,刀子被程家发现了,我的报仇雪恨之希望犹如肥皂泡,瞬间无影无踪。上次是最好的时机,可惜我手软。深夜里,万簌俱寂,村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我失落到极点,暗自掉泪。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后,程家父子三人商量怎么看守我。
程哲明说:“事情到了这个样子,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村里人可能不会帮我们看守了,这一个大活人放在家里,迟早是要跑的,你俩兄弟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呢?”
程学文说:“日妈的格老子,娼婆子疯了,昨天还说要杀死我,杀死我女娃呢!”
程哲明说:“她可能真有杀女之心,防不胜防,啷个办呢?要不,放她走算了!”
程学文说:“不行,这啷个行呢?我还没生儿子呢!我不能断子绝孙!”
一阵沉默,三人都没说话。忽然,程家的狗跳了起来,“汪汪”地叫着。程学龙看着被铁链锁住的大黑狗,叫着,跳着,却始终在门边打转,猛一拍大腿,说:“有了!”
程学文怀疑地看着程学龙,问:“你有啥子办法嘛?”
程学龙笑了,指着狗说:“狗啷个跑不了嘛!”
程哲明说:“狗日的,你要把燕娃子像狗一样链住,这是犯法的!”
程学龙冷笑一声说:“十二岁买来不犯法!没打结婚证强行日不犯法!屡次抓人不犯法!这些都犯了大法咯,再犯一次又啷个呢?链了三个月不就怀上了,怀上就不链了!”
程学文一拍巴掌,傻呵呵地说:“好办法,好办法,坐牢我坐,老子豁出去了!”
程哲明无奈地说:“既然豁出去了,那就链上吧。”
我正在房间里坐着,想着该做什么呢?跑是跑不掉的,干农活更不愿意,这日子该怎么过哟!女儿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似乎想亲近我。我懒得理这个强奸出来的孽种!
忽然,程家父子三人气势凶凶闯进房间,程学龙手上拿着一根链狗的铁链,程学文拿着一把电钻,他们要干什么?只见程学文站在椅子上,手拿电钻,在墙上装了一个大大的爆炸螺钉,又把铁链固定在螺钉上。我正惊奇地看着他们,不知他们要做什么,程学文和程学龙突然紧抓我的双手,程哲明把固定在墙上的狗链子的另一头,硬套在我的右手腕上,还用一把小铁锁住。“不——不——我是人——我不是狗!放开我——”我神经质般大叫。
程哲明拍拍我的头,说:“燕娃子,你天天想跑,我们哪有那么多精力看守你嘛!我们程家劳民伤财,你总不能看着程家人财两空吧!只要你怀上了,我们就给你自由,只要你帮程家生了儿子,我们就放你走,我说话算话。燕娃子,暂时委屈你了!”
程学文指着我说:“日妈的格老子,宁愿跑掉给野男人搞,也不给老子搞,捡了你妈的本本的娼婆子!跑啊——你现在跑啊——生了儿子老子也不放你走,狗日的!”
程学龙嘻嘻笑着说:“一个狗链子算什么,我这就去定做一根脚链子,把你这个娼婆子的脚也链住,我看你有能耐跑不?狗日的,好日子不过,自己作贱自己,活该哟!”
程哲明推着程学文和程学龙,说:“走走走,出去,干活去!”
父子三人出了房间,程哲明顺手拉上了房门,并且锁上,大概是不想让村里人看笑话。
我万万没想到,程家为了生儿子,为了防止我逃跑,竟然像链狗一样链住我。房间只剩下我,孤独,耻辱,愤恨,塞满了我的脑子。我的肚子里仿佛充满了火药,像要爆炸似的,逼着我狂叫,砸东西。我本就沙哑的嗓子,在狂叫了一个小时左右,彻底叫不出声音了,吞口水都痛。由于疯狂砸东西,我更是累得没有一丝力气,颓废地坐在地上,披头散发,真像一只狗,一只无家可归任人欺凌的流浪狗。流浪狗是自由的,我连流浪狗都不如。
这时,我的头又痛了,再次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发现,我的头痛病发作频率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痛。也许,我还来不及为程家生儿子,就已经头痛至死,一命呜呼。一想到死,我朝房间四看,想找个方法结束我悲惨的一生。房间里没有任何铁器和绳子。看来,程家早就为了防止我自杀而清理了一切可以自杀的工具。被链住的我,只有撞墙才能死。撞墙,血肉模糊,死得多难看啊!如果撞一下就死了,那也痛快。可程家的砖墙是土巴砖,如果撞一次没撞死,还得撞,那多痛啊!我承认,我不是个强者,也不是个刚烈的女子。如果我是个刚烈的女子,也不至于落到如今像狗一样链住,也不至于想死都死不了。
中午,程家人松开链子叫我吃饭,我再一次没想到,父子三人又在我双脚上锁上一条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是程学龙上午特地骑摩托车到双虎镇订做的。因为有了脚链子,我再怎么样跑,也跑不了。所以,有时候,程家人会把狗链子松开,我能在屋里走路,负责做饭喂猪。而脚链子,只有晚上睡觉前,程学文才会解开,以便于他“播种”。我就这样被程家人像看守管制解放前的共产党人一样,用狗链子链锁了三个多月,直到程家人确定我怀上了孽种。
程学文性功能并不好,估计是之前长期打光棍天天**造成的。再加上他在福建打工期间,不洁身自好,一有空就找年老色衰的站街女发泄,现在有用才怪。自从程家人用铁链锁住我的自由后,头两天程学文还能勉强行房,第三天再怎么弄也像个死蛇,站不起来。在福建期间,我就发现,每每没用的时候,程学文就喝泡了各种药材的白酒,还真能刺激他的**。现在,为了生儿子,为了传宗接代,程学文天天要行房,也就天天睡觉前喝白酒。他从开始喝二两酒,到后来喝八两酒,半个月之后再怎么喝酒,也不中用了。我暗自高兴,心想,程狗子他没用了,我就不会怀上了,老天有眼啊。也就是说,我不会再次有孕育生产之苦,也不会多一个孽种。虽然我讨厌强奸出来的孽种,但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内心深处来说,我还是爱娃娃的。可是,这种爱,被恨淹没了,只能潜藏在脑子中某个角落。
当程学文一连几个晚上想行房而不中用时,我就知道,他可能阳萎了。这是大伯卖我到程家几年来,我最高兴的事。不知是报复,还是希翼程家早日解除铁链,我故意多次对老太婆说,你家程狗子阳萎了,不中用了,你们锁我一辈子也没用,都生不出儿子,程狗子断子绝孙咯,哈哈哈......每当我说这些话时,老太婆就会狠狠瞪我一眼,骂道,死娼子!
吴龙村有一个前清末年出生的老爷爷,一百挂零了,据说读了不少书,不但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还能看风水,村里人叫他老佛爷。老佛爷不怎么说话,每天在村里转悠,念着村里人听不懂的经语,最受全村男女老少尊敬。由于多年来我不安心在程家过日子,我也就没注意到这个老佛爷。自从我被程家锁上狗链后,每天在村里走上几圈的老佛爷引起了我的注意。村里人都说他是活神仙,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很好奇。每当看见他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影子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就有一种跑上去的冲动,想找他聊聊,哪怕是说一句话也好。
程学文因房事过度不中用后没几天,这个机会来了。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坐在大门前晒太阳,程家没一个人。这时,平常从不经过程家大门口的老佛爷出现了。我之所以知道他走到这里,是因为听到他的之乎者也的喃喃读经声。我站了起来,走向正踱着方步的老佛爷。由于铁链拖地,我的走路有“哗哗”的铁链声,但老佛爷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踱着方步,挺胸抬头,就要走过程家大门口。
“老佛爷,请您帮帮我,程家凭什么像链狗一样锁住我!?”
老佛爷停住了,但没回头,朗声说:“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说毕,他又踱着方步,健步继续绕着村子走去。
我呆呆地看着老佛爷,他的身后传来我听不懂的天话: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