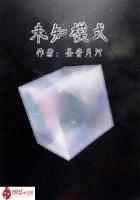流水飞逝,水盆已满,滴答滴答从屋梁下落。
落入水桶……
吕不非拱拱手,“天色不早了,无殇姑娘,就先在这里歇息吧,我就在对面安寝,如若有事可敲门叫我,小生一定随叫随到,恭候差遣。”
腰身向下弯曲,如弧形的拱桥挂满飞扬的彩绸。
夜已深,村落里的大狗,黑狗,看家狗,不再对着乌压压的天空汪汪乱叫,它们累了……回到窝里,开始睡觉,外面轰隆的雷声已经见怪不怪,大雨中的落水狗回到被风散大半的窝棚,主人已沉沉睡去。
圈儿里的猪,呼哧呼哧地在木槽里左拱右拱。
要想猪长得肥壮,就要多吃,尤其是夜里的加餐,每逢亥时,就是猪们雷打不动的进食日,主人会早早准备放入槽中,祈祷天公作美,冬日里的雷雨交加是少见的,年纪小的,惊骇地挤成一团儿,躲在安全的角落。
屋里,没有乱七八糟的牲畜。
“放心吧,这水桶,我会起来换的。”
无殇从木椅上跳下,扶起对方,爽快地道。
对待客气的人,她还是很有礼貌的,打打杀杀是粗人做的事,如果用脑袋可以解决问题,那便辛苦一下嘴巴,犒劳劳累多时的双脚,初初变成人,真有一点儿不适应。
脚踩在冰凉的地上。
干燥的地面,湿漉漉地流着眼泪,黑暗与阴影交错。
她的声音沙沙哑哑,不比木椅吱呀的色调,呲呲地直扎人心。
“本来,姑娘应当住小生那间屋,没有漏雨,只是男女有别……又没有别的屋子,只好委屈将就了,小生万分过意不去。”说罢,又要一拱手。
态度谦恭,极具迷惑。
他的声音,温温润润,像汩汩流动的泉水,没有寒冽至极的冷,只有沁人心脾的暖。
无殇低头一笑,“救命之恩,不敢忘怀,你放心,我一定会给您回报,一个您永远想不到的大回报。”
她学着少年的样子,双手合抱,左手在外右手在内以示真诚与尊敬,至于真假与对方一致,如果他是真的,无殇愿意敞开心扉再多一个朋友,与他肝胆相照,如果是假的,她也不是银枪蜡头。
他知道,滴答。
她知道,呼呼——
二人的影子交叠起来,左摇右晃。
“无殇姑娘,万万不可,圣人云,君子重义轻其利,吾等身为圣人门生,助人于危急,乐意之至也。”吕不非似乎有些急,上前一步,抬袖道,“每个人皆可心怀善念,如果为求回报而做善事,那人一定会良心不安,尤其在深夜。”
吕不非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只映着烛光儿,一只隐在黑暗。
以直挺的鼻根,为界之限。
仿佛世界切割两半,气氛一时凝滞,风挟着沙雨砰砰地敲击着大门,二人砰砰的心跳相呼应和。
吕不非的眉毛,是清峻的眉峰,有高度,有角度,叠叠重影间,似乎化成一把剑,带着锐不可当的剑气,直冲她的眉心。
这是无声的警告,隐晦的提示,在没有月色的夜晚,在雷电撕裂乌云的夜半,杀人放火,做坏事的人,总有一天会不安,良心在夜里隐隐作痛,鼓胀成球的衣袖间,隐隐有浩大的气息与天上的雷电相接。
如果,两个是成年人,在屋里对峙。
有铮铮金鼓之声。
两张略显稚嫩的面庞,一个有隐隐的喉结,一个胸部挂着小小的荷包。
穿着相似的绿意长衫,一高一矮,一仰一俯,铮铮金鼓萦绕在长发、衣袖间……着实好笑。
片刻。
无殇环顾四周,咳咳两声,挑起三分邪气的眉毛,笑道,“难怪你这么穷,都是因为太好心,太正直了。”
“无殇姑娘,请慎言。”
眉毛皱起,语气正色,只是紧张对峙的气氛一下子被笑声打散,如瓦片碎裂无法复原。
一股气,在吕不非的胸膛涌动,出不去。
“请叫我无殇。”
无殇挥袖打断。
一炷香飘过。
“好吧,无殇,你听我说。”吕不非叹口气。
“我知道,君子需敏于行而讷于言,无人时尚且慎独,面对姑娘时更需好好表现,”无殇再次笑着打断,上下打量吕不非,从头到脚,只觉风流往下流,从脚到头,风流往上走,“不过,你不要表现,只要站在那里就能吸引无数蝴蝶。”
呼气……呼气……
“无殇,咱们不说了,早早睡。”
嘎吱一声,木门合上,吕不非再次匆匆逃开,在黑暗里踉跄,直奔卧房,顾不及待收的药碗与油灯。
数盏茶的功夫,吕不非抱着被子,在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睛看对面的窗户,间或闪过一道白光,游走诡秘,寻不见规律。
永安城的冬天,极少这般,有一张夏日说变就变的脸,空气里湿漉漉,各种味道在雨中发酵,吕不非呼吸有些沉,以往只有打闷雷不落雨的季节才会感到胸口压抑,窗外瓢泼的大雨也舒缓不了他现在激动的心情。
大雨哗哗地下着。
危险,神秘……兴奋,忧心……
精神匹敌的对手,难以揣测的心思。
心大的秀才,失眠了,他隐隐有一种预感,这个来历奇怪,举止奇怪,外貌奇怪的危险女分子,会让他的人生翻天覆地。
他的平静生活,按班就部的日子,整个如死水的十六年生命,都会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彻底扭转。
她的邪气与野性,不是整日背之乎者也的自己可以想象,空有一副温和的皮囊,却做不来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吕不非抿起唇角。
“我的警告,她会在意么。”
“如果一切难以挽回,又该如何?”
“汪——”梦里的狗身子一抽,不禁叫出声来。
书房内。
无殇和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同样睡不着。
木桌上的烛灯,已经熄灭,喝了药,无殇感到脑袋昏沉,竟觉得药居然真有了疗效,不禁也笑了笑。
“真是一个嘴硬的家伙儿。”
“翻来覆去睡不着,是不是吓坏了……我可没有故意哦。”
沙哑的低语,像断续摩擦的二胡,在夜里铮铮,私私。
她的听觉很好,黑夜没有光更是针落可闻,捂也住耳朵不想听,各种声音仍踏着雨水而来,挡也挡不住,两道木门的距离,割不断声音的频率,空气与雨声的震颤,在风沙里摇曳。
“吼——”
你是妖怪,是天理不容,不容。
“我才不怕呢。”
她弯起嘴角,像一朵妖艳又青涩的罂粟,雨滴从房梁落下,准确落入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