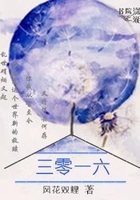本以为旗袍退回便可相安无事,谁知道杜晓莉仍旧是不依不饶,连着几日有意无意的在菱歌面前谈起于文祥,说他如何本分经营,如何孝敬父母,如何温顺有礼,菱歌每回只是笑笑,并不说些什么。
这一日从剧院出来已是晚上十点钟的光景,如意夫人追到门口塞给了菱歌一个锦袋,让她带回家给她母亲,那袋子包得紧实,看不出里头是什么,只知道沉得很。回到家里原以为父母都歇息去了,不想竟然还在客厅里喝茶,见她回来纷纷笑脸相迎,倒让她生出一种不祥之感。往常即便是向她要钱,也绝没有这样的笑容。她把锦袋交给魏太太,魏云忠赶忙抢了过来,正要打开,魏太太忙拦住了他,极用力的瞪了他一眼,他只好作罢。魏太太转而笑盈盈的对菱歌说,“周妈煮了些雪梨红枣羹,就在厨房里,你赶紧去吃些,难为了你这孩子,为了这个家都熬瘦了。”魏云忠也附和道,“就是就是,爸那份还没吃,你一并用了吧。”菱歌被这突如其来的怜爱惹得一身鸡皮,忙道了谢,往厨房走去。
那雪梨羹放多了糖,甜得叫人喉咙生疼,菱歌只草草吃了一碗,便上楼歇息。才换了睡衣就听见周妈来喊,说是有她的电话。极少有人打电话来家里找她,又是这样晚,忙不迭答应着开门出去,一只脚不小心撞在门槛上,疼得呲牙。
原是杜晓莉,也不知在哪里打的电话,只听得见电话那头高高低低的音乐声。杜晓莉听见菱歌的声音,柔声说道,“明天中午十二点文光在秦湘阁定了位子吃饭,你一定要来。”菱歌笑她胡闹,这样一件小事也要这样晚打电话来说,转念一想,她定是另有目的,于是问道,“你是不是也约了于文祥先生?”电话那头杜晓莉发出一声窘迫的笑,“你这妮子怎就这样聪明,我告诉你,我可是跟文祥哥打了包票,说你一定会来,若你不来,当真是不给我面子,我是绝对下不来台的。”说着话,那语气渐渐转为可怜,“你就跟人家见过那两次面,便如此决绝的说不可能,当真是太武断了,我认识你三年,你从没这样过。好菱歌,你就和他接触看看,实在不喜欢,我难道还绑着你嫁过去不成?就给他一次机会嘛。”菱歌听她话已至此,怎好再推托,于是就答应了下来,电话那头杜晓莉自然是喜出望外,末了还不忘嘱咐她准时到。
第二日一早周妈买菜回来,就大呼小叫的在家里炸开了锅,嚷着说卫国军驻守在南溏与渌洲交界的北大营夜遭突袭,此刻已是硝烟四起,炮火连天,只是战场离市中心远,他们没有察觉罢了,可此时也是全城戒严,局面紧张。
原是那渌洲统制梁德泰无端反动,连夜率着麾下兵将发起突袭,北大营猝不及防,死伤众多。周妈绘声绘色的描述着,脖间青筋暴起,额上碎发纷飞,仿佛刚从前线下来似的。
菱歌才起床,听得这样的消息,倒也不像父母亲那样惊慌失措,前些年也经历过兵荒马乱,到底也挨过来了,不过是日子难过些或者更难过些罢了。她母亲吓得没命,甚至将枕头套里藏着的几张私房钱掏了出来,吩咐周妈赶紧上街多买些米和干粮回来预备着。
到了十一点钟,并没有听得什么炮火声响,菱歌便照旧换了衣服出门。外头确是比往常要萧条些,许多商户上了门板,直接贴着告示宣布今日歇业。路上也随处可见警察巡逻,好几条街设了路卡,来往行人车辆都要接受检查。倒是那秦湘阁照常营业,一楼的大堂里也坐了不少的客人。杜晓莉跟她说了是在二楼的小包房,因而菱歌进了门直接往二楼去。刚踏上楼梯,忽闻身后传来杜晓莉的声音,唤着她的名字,菱歌转过头去,见她一个人行色匆匆的朝她跑来,脸上的神色十分惊慌,菱歌心中不由一沉,还未及问她缘由,便听她颤巍巍的声音说道,“文祥哥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