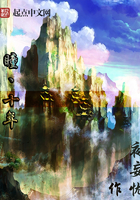热水中泡开了一些夏日里晒成的茉莉干花,淡淡的花香氤氲在水雾之中更多了几分清新。
隔了这么多年,她还是最爱这阵花香。
菱歌坐在小竹凳上低着头,付长东站在她身侧用水瓢舀起热水缓缓冲湿了她的长发,动作仔细而轻柔,也不慌不忙,倒像是从前做惯了这样的事情,菱歌忍不住打趣道,“你竟有几分熟手的感觉。”付长东轻笑道,“小时候替我母亲洗过几次,有些经验,你们女子的长发最容易打结,要慢慢洗才好。”菱歌心头一阵暖意融融,一缕热水顺着她的脖子流进衣领里,付长东连忙用毛巾替她拭去了,茉莉花的香气隐隐约约,木盆中的热水蒸腾着白茫茫的雾气,让这一切显得格外的不真实,像是一个幻境。
五年来他的体贴与关怀就像是这一盆温热的水,不浓不烈,恰到好处,让她饱受风霜的一颗心渐次的温暖起来,而他们的这个小家却也如同此时晕开的这一片雾气,常让菱歌有一种不真实的虚空感,总害怕风一吹便会散去。
“我有件事情没有跟你说呢。”付长东替她篦开缕缕青丝,低声说道,“前日有几个青年学生找我替他们做一批小旗子,要在抗战游行上用的,我并没有收他们的钱,你可别怪我自作主张。”菱歌略略有些吃惊,“这是好事,我怎会怪你?”付长东舒了一口气道,“年下要用钱的事情多得很,我还想着给你父母寄一笔家用,本来是应该多想法子赚些钱的,可那些学生本就拮据,且又是为国为民的事情,我便想着咱们也尽一份绵力吧。”菱歌不由得称赞了他一句,又说道,“我这些时日又收了几个学琵琶的学生,过几日他们就会把学费交过来,年下的用度你不必太担心。”
五年来,付长东除了制伞之外,还一直兼着做些纸艺工作,昭城常年温润,雨季绵长,加之他手艺精湛,油伞的销路一直不错,纸艺的活计也挣得一些零碎,日子虽然清苦,可总不至于捉襟见肘的地步,虽然年下要用钱的地方确实不少,可菱歌心中忧虑之事却不在于此,今日杜晓莉提起回南溏一事才是她心中的梗结所在。
那日他带着她登上那辆逃离奉阳的火车,便想着此生再也没有归途了,可自从有了平儿,她心中却不止一次的想过要回南溏去。五年了,父母与平儿一次面都没有见过,平儿更是不知道他的故土是何地方,她们虽然在昭城安家落户,却终究摆脱不了那种流亡的心情。
踌躇了良久,菱歌终于轻声的唤了付长东的名字,极力用云淡风轻的语气说道,“今日晓莉提议咱们回南溏过年,你怎么想?”许是篦子太密,许是湿了水的长发发涩,付长东手上一用力,那发篦卡在了青丝之中,被他手心一扯,疼得菱歌“哎呀”了一声。
他回过神来忙将篦子从头发上取了下来,几缕断发缠绕在竹木上面,仿佛几条极细的蛇,直缠到到他手上来。
她五年前嫁给他,是他合理合法的妻子,婚书就压在衣柜的最底下,牛皮纸上端端正正的小楷写着联姻的誓词和他们的生辰姓名,落款处有他们打下的红手印。可她早已对他坦诚一切,在此之前她曾是别人的结发妻子,只是没有凭证,因而他自然知道南溏于他们二人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在。
他不过是太爱她,太珍惜这一切的安定与美好,所以才会这样害怕而失态。
菱歌背对着他,看不清他脸上茫然自失的表情,可她从他的沉默里可以相见,因而抬起手握着了他的手心,劝慰道,“他如今早已不在南溏。”付长东回过神来“哦”了一句,却只是埋头重新替她梳理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并没有说些什么,菱歌知道他许是心烦意乱了,倒有些后悔自己不该提起这个话题来,故而也只是静静的由着他用毛巾帮她擦干着头发,半晌都没有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