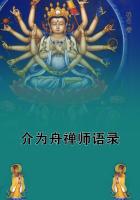钟彦兮顿了顿,出了门。即使是繁华的都城,在子时,也没有了车水马龙的热闹,路上偶尔有马车呼啸而过,她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放在桃色里子的斗篷里,她慢慢地走着,长靴在洁白的雪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墙角蹲着一个圆球,衣服一层又一层,套在身上。他扯起裤脚擦了擦鞋,冷嘲热讽:“名门闺秀,啊,真正的小姐。”
“兮姐姐。”身后一个清脆的孩童声音叫住她。
钟彦兮立在原地等她,他跑过来,可爱稚嫩的脸上满是天真的笑容,她有些恍惚的望着年幼的他,脑海中那不可触碰的记忆,又一次像是冬天的风暴一般凶猛的扑面而来。她紧紧的攥着伞把,咬着牙,等着那阵剖心的疼痛碾压而过,甚至都忘了和她的母亲紫隐元君蓝羽打声招呼。
“兮儿,你也走这条路啊?”蓝羽柔笑的很是温和,“我家就住前面。”
钟彦兮点点头,刚想转身走,可脚下忽然一歪,她向前跌去,蓝羽慌忙伸手拉住她,还好她反应及时一只手扶着蓝羽站住了,一只手停在空中,伞落在一边,雪安静地落到她黑亮的长发上,一片一片的,凉凉的,没有一点味道,和记忆中的味道,一点点重合。
新鲜血液的气味在雪夜散开,蓝羽用手挡住血液殷红了手绢的右手,生怕被孩子看到。蓝羽法力高强,也只有这个时候的她最脆弱无礼。
“谢谢。”钟彦兮扯动嘴角,毫无痕迹地将透明药粉撒到她手上。
“兮儿,只有你没有变。”蓝羽的柔声晕开了夜晚的墨黑。
墙角的打鼾声,像嗡嗡响的锯子,传过来,绕过去,整条街上的房子,哆哆嗦嗦,摇摇晃晃,颤颤巍巍。
“啊,剑。”一丝微光吸引了男孩的注意。
圆球悠悠醒转,男孩垂涎他的那把剑,但是他转了个身,压在身下:“不能碰,不能摸,只能看。”翻转间,他的肩上露出一条深深的、令人害怕的伤痕。
男孩哭闹着要摸摸他的鱼形剑,他咆哮着:“剑太快了,不是小鬼玩的。”然后粗鲁地剔着牙。
钟彦兮看着留在雪地上的那串脚印,大脚小脚并行,温馨美好,男孩眼神回头对着她微微一笑,露出一抹皎洁。他和小时候的他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他已经不再,他——彩光以君被镌刻在墓碑之上。没有魂魄的人的墓碑是立不住的,可是蓝羽每年用鲜血去浇灌那方土地,那方土地才允许墓碑才得立在那里。
钟彦兮沿着长堤看去,一派清清冷冷的景象:
银装素裹,白柳横坡,小桥通曲,天女散花。
石中冰清玉洁,篱落暗香,树头琼花层叠,疏林玉枝。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
钟彦兮正自看堤边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猛然从身后窜出一辆马车挡住去路,扬起一片雪珠儿,帘子一掀,闪出一个男子,他,望着她,带着她熟悉的笑容。
他还是这样的一股清流,品味奇特,满脸满脖子脂粉,涂得厚厚一层,看不见肤色,惨白惨白,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钟彦兮猛然见了将身子往后一退,她抬眼望着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样貌一点也没变,一如既往的俊朗,一如既往的优雅,一如既往的温柔斯文,一如既往的谦谦君子,可气质全改,一双柳叶眼里有别人看不懂的诡异微笑。
“是兮儿呀。”他轻轻叫着她的名字,这个名字许久没人叫过来。
他总是这样温柔得叫她,这种温柔像一张迎面张开的网,有一种令人想逃跑的冲动。
初见时,他说:兮儿呀,做我的娘子好吗?
拜堂时,他说:兮儿呀,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你也给不了我。
钟彦兮把伞上的雪抖了抖,黯然又有些平常的看他一眼,,是惹不起的人。多久,没见到他了,时间久的自己都记不清了。曾经那么近的人,现在却隔得那么远。
他抿了抿嘴,轻轻地看着钟彦兮笑:“兮儿呀,好久不见呀?”
她看着他温润如玉的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轻蔑,她点头道:“好久不见。”
陈宙伸手,挑起她的下巴,残忍地一笑:“兮儿。你本性不改呀。”
她挑挑眉,抿抿嘴,正言道:“没办法。”
他低头问:“他也见点世面了吧?”
他摊摊手,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一副受不了她的样子继续说:“还没厌倦你这副模样么?”
钟彦兮看着她戏谑的眼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苦笑了一声,转身要走,却被她快步走过来一把拉住。
他面带怒容,瞪着钟彦兮:“不想听吗?我只是说了实话,不是吗?呵呵……”
“陈宙。”钟彦兮叫出了他的全名,皱着眉头盯着她,“我想不想听,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呵呵,是啊,与我有什么关系?一直是我,是我自寻烦恼是吗?”他恶狠狠抓住她的胳膊,直直的瞪着她,脸上的温和早已不在,阴翳的眼里满满的都是被背叛的怒火,他慢慢地吐出每一个字,“那么,是谁惹我了,是谁,三年前,在我的婚礼上,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现在,我只想知道,三年前,我的‘祝福’生效了没?”
“你和他,不会在一起吧?”
钟彦兮叹了一口气,平静地抬眼,看着她:“陈宙,我们的订婚本来就是一场闹剧,你不情我也不愿,现在我和谁在一起,更不需要你置喙。”
他阴沉着脸,思索:“是你做得好事吧?”
钟彦兮一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诡异笑道:“用氛氲凝切断血的气息,是你的老把戏了。”
钟彦兮笑道:“何必明知故问。”
他苍白着一张脸,嗅了嗅留在空气里的一丝血味,就要追去。
钟彦兮“桃花如晦”出手,点点飞红雨,如泣如诉,如织似愁,片片如刀似剑,袭向陈宙。
陈宙拿衣袖挡脸,鬓间的几丝头发被削断,落到肩上。
“你自己整日风流快活,却让未婚夫去做和尚吗?”
“你这样无血不成宴的人想的倒是不坏。”
“你这样的人以情为食,贪得无厌,可有人收了你?”
“等你做了和尚再说吧。”
陈宙“苍茫云海阵”现世,风渐起,云渐涌,黑云升远岫,摇曳入雪地,云海一望无涯,钟彦兮内心震恐:“没想到他的功法已经登峰造极。”
“藕香墨污”臭味一出,钟彦兮第一次这么盼望见到这招,不,是闻到这招,果然陈宙遮着脸面,仓促闪躲。
“他这一张脸宝贝成这样了?”
“你若是在他脸上弄上一个墨点,流霜剑我就给你。”
“说的就跟自己的似的。”
“别这么说嘛。”
说完,她不在看他,收了伞,径直上了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马车。车夫抽了马一鞭子,马车缓缓的行驶,她安静地窝在马车里,冰冷的手感受的炉火的温热,但是,她知道他还站在黑云之上,风雪已经包裹了天地,也把他冰封在那里。
墙角那团圆球,把书窝了窝,折了个书角作记号,揣到怀里,鼾声再起,嗡嗡响,陈宙哆哆嗦嗦,摇摇晃晃,颤颤巍巍,仓促出逃。
钟彦兮将头靠在车上,面带倦容,真想不到,还会遇到他,忽然觉得,前尘往事,好像已经间隔了几个轮回。
钟彦兮看着车夫换成了李逸姜,道:“怎么是你?”
李逸姜道:“景公子不放心,让我来接你。”
钟彦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李逸姜道:“朗先生亲自去了。”
钟彦兮闭上眼,神思倦怠,天寒地冻的日子,动物多数都冬眠了,她也想冬眠了。
迷迷糊糊间钟彦兮握住把手,抚摸着上边的雕刻,头像山岩,鼻子若山峰,额头圆润,怎么有些突兀,疑惑间,睁开眼,哪里是龙,在她手里的分明是一条毒蛇,她立马蹦了起来,哇哇大叫:“停车,停车,车上有蛇。”
车夫停下车来,道:“哪里有蛇?”
钟彦兮跳下车来,心有余悸,指了指车把手:“谁干的?”
“你不是喜欢龙吗,上次那个龙丢失以后,我就让人有雕了一个,只是这个龙有点粗糙。”
“什么粗糙,那分明是一条蛇,一条蛇。”
“好好,我给卸下来,真不懂你们这种人。”车夫可能觉得干站着,与她一起,在大雪天气里,有些冷,便想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