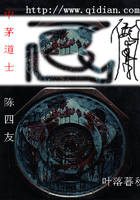在路边干坐着也不是个事,不管我对之前的事情有多少回忆,又有多少我防不胜防的,我现在的目的地是坐火车回老家,最好能一次性解决。
可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我每天活着,就是在不断渡劫的。每个劫就是我面对的每个问题,面对它们时,我应该知道问题是什么,这问题怎么来的,而最终我要想明白该怎么办。可是面对这几十年来的各种际遇,我却想不明白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换个角度,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自己描述这个问题。
街边的出租车很多,经过我的时候都稍微减速,可是很快就一脚油门蹿远了。我掏出手机打开相机,对着自己一看,有些怪异,镜头里的我开始变得连自己都不敢认。四方脸的棱角更加分明了,就像是减肥过度一样,可这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两个眼窝已经深深陷了进去,显得眼珠子变得很大,我嘴里自嘲了一句,着他大爷的和那聊斋里被狐仙缠上的书生没什么两样了。我把手里的烟头一扔,顺手招呼刚刚蹿出去的车,那车车头一颤,停了下来。
直至上车,我都在浑浑噩噩中,随着人群到了车厢里找到了自己的铺位,一屁股坐下。我该从那个角度来理解问题呢,从勇子摔坏开始,还是从小毛被高压电击成了一块焦炭开始,又或者该从大亮毫无伤痕死在了路边的沟里开始。脑子里乱麻一团,兜里的手机响了好几遍,我都没有发现,路过的乘务员提醒我,我才接通了电话。
还是二平子。这小子声音低沉,和我说,勇子的命是救回来了,不过可能以后得永远躺着了。我说什么意思,二平子说,他是背部着地的,脊柱断了。我说那医院是干什么吃的,二平子说,人家医生说,他们已经尽力了。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句话啊,多少狗血的现代剧里医生说的就是这么一句。哼,勇子算是没戏了,想白五混吃混喝一辈子,什么积蓄都没有,拿什么来赔偿,就算是慰问一下也指望不大。我摸摸兜里,兜里没多少钱,可是这次回去怎么着也得给勇子留点。
我的情绪非常坏,顺手把手机往小桌上一扔,结果手机顺着桌子上的塑料袋滑了下去,眼看就要掉到地上。对面伸出来的一只筋骨爆出的手接住了手机,我一愣,对方微笑着递给了我。我细看此人,居然是个大爷,其貌不扬,却明显非同一般,我几乎想到了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可是这毕竟是在现实之中,哪有那么多高手啊。我点头表示感谢之后,和大爷聊了起来。
显然我布满抑郁的面容吸引了大爷的注意,大爷和我的谈话开始后,大爷有意无意都劝解我几句。我也不好反驳只能点头称是,心说您也不知道我到底遇到了什么,就算是您说的对吧,可是未必对我有什么用。接下来大爷说的一句话,叫我觉得对面的可能真得不是一般人。大爷说二心者,必有百般见识。可二心者,内心未必舒缓,甚至恰恰相反。他用手敲敲桌子:小伙子,二心者,此时非汝若谁?或许是他以为我没反应过来,换了个容易理解的说法:小伙子,心不在焉,你到底遇到了什么。
我不是一个喜欢和任何人分享内心的,可是此刻我忧郁了一下,还是和大爷说了。我再次回忆了小毛的离开,勇子的出事,也再次回忆了大亮的蹊跷之死。
当年,大亮和小毛的家境算是村里比较好的,早早就搬到了县城。我们来回见面也就少了,小毛走了之后,大亮虽然在外地读中专,也还是请了假坐几个小时车回来给小毛送行。好好的五个好兄弟,少了一个,谁心里也不是滋味,一顿本来就偷偷摸摸的聚会成了几个半大小子沉默加沉默的呆坐。大亮第二天就返回了学校,直到暑假出事,好几个月都没有回来。
暑假的时候,大亮和我都放了假,所以在信里商定能聚一聚。没有合适的公交车坐,他爸也没空因为小孩子的聚会开车送他,于是大亮只能自己蹬着山地车往村里走。将近二十里的路,一路还是上坡,可是把顶着大太阳赶路的大亮给累坏了。眼瞅着八里沟的桥就要到了,大亮计划着到桥上去歇一歇,最好能到河里稍微洗个脸啥的。
大亮刚刚爬上桥头,对面的拐歪处树林里就出现了一量轿车,卷起一阵尘土冲着大亮过来了。大亮也没犹豫,手里一用劲,车把一歪就往边上靠。八里沟桥上的栏杆是石头雕刻出来的,可是有些年月了,粗壮不说,上头还有花纹,大亮计划着右脚一踩,停下来等着车过了再说。随着右脚一接触栏杆,栏杆却像是纸糊成的一样,软绵绵得把大亮闪进了河里。
司机看到对面出事,慌忙停了下来,准备救人。可是到桥边一看,八里沟桥下的水在河道清淤的时候被挖深了,足足有三米多,水里哪还有大亮的影子,不会水的司机只好开车到了最近的八里沟村里求救。几十号人从快中午的时候,捞到了下午太阳落山,才从河道里捞出了一个长条条的泥蛋蛋。大亮被河底没有清理干净的淤泥活生生裹成了一个泥疙瘩。
人们用河水冲洗了大亮的身子时,围观的老老少少中有人就摇头叹息上了,人已经僵硬了,哪里还有得救。可怜的是,大亮的父母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和他们阴阳两隔,最后还是乡上派出所发出了协查通报才知道的。大亮的身体没有任何损伤,法医鉴定为窒息死亡,但是听说法医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一个快要成年的小伙子,身强体壮能死于窒息。
不管解释得了解释不了,都没有意义,大亮也走了。我等到的是大亮父母送回来要埋在祖坟里的大亮尸体。在我们村里,这种二十都没有活到的人,都算是夭折,就连在村里举行殡葬仪式的资格都没有,而且没有人愿意参加一个夭折之人的葬礼,上次小毛也是因为这个,他的父母才把小毛带回城里火化的。大亮的棺材在席子搭成的棚子里放了三天,从官庄过来的那个师傅,按照大亮父母的嘱咐,给择了时日张罗着埋葬了大亮,从此,大亮成了我和二平子、勇子常常能从村里这边看到的,位于那边梁上的一个土堆。
这不是个故事,老大爷说得对。这是个事故,当年大亮死后,白五那个半吊子跳大神的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说的更绝,在村里那棵大槐树下,白五指着我们三个,说他算过了,我们几个的八字有问题。就因为这句话,我爹当年差点把白五给废了,而白五也因为我爹说的那句,再说有问题,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白五倒是不再说八字的问题了,可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在路上瞅机会问我们几个,是不是最近干过什么事。因为家里嘱咐过,我们走道儿都躲着白五走,更不要说和他搭话了。他碰不上我们,只好作罢。我们三个瞒着家人一起商议过这事,始终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小时候干过的那件事有关系。
老大爷到站了,收拾了行李,和我说了再见走了。就在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扭头和我说:小伙子,凡事有个定数,我觉得你该再回去一趟,回哪里你懂的。我愣住了,我没跟大爷说什么事,更没有说我们当年到过哪里,他却像是根本就知道似的。我起身要追上问问大爷的,头部却传来一阵剧痛。
我睡着了,剧痛来自头部和墙壁的亲密接触。耳边的火车车轮还在轰隆隆往前疾驰,根本没有停下,从窗户里看过去,附近丝毫没有车站的影子。我起身来到列车员房间门外,询问得知,车都从来没听过。我表示不相信,看看时刻表,才怏怏回到铺位上。从枕头下边掏出手机,手里的感觉出现了一丝异样,手机的边缘有些碎了的迹象。我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我的手机磕碰过。回到铺位上躺下却再也睡不着了,我看着对面。把手耷拉下来。手机轻轻磕着地板,我突然想起来,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被任何人接着,而且确实跌到了地上,摔坏的地方正是与此有关,可是,谁捡起了手机?
我摩挲着手机,手心里都是汗。难道是因为我一直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应该回去一趟,不仅是回到老家去,而且能再回到那里一趟,还有二平子,勇子都应该回去。我们的遭遇,没有别的解释。我记得有人说过,如果所有的可能被排除的话,最不可能的就是躲藏在背后的可能。我一直不认为小毛和大亮的遭遇不是意外,可是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猜想这么些年,好几次二平子在电话里的吞吞吐吐,也应该和他对此事的看法有关,他也想到了什么,大概和我一样,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万一看明白这个问题之后的种种。天亮了,车经过了一个小小的车站,我透过车窗看到了仍然在坚守岗位的老工人,和他照面的一刹那,我猛然发现,这人我在哪里见过。